开播一天就遭遇“停播”的电视剧《白鹿原》从昨日起回归了。这可不是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在播出过程中的第一次“波折”,实际上,从拿到改编权到播出,人们足足等待了17年。
早在2000年,陈忠实就已经将电视剧改编权进行了授权,但是直到2010年,电视剧版的《白鹿原》才通过审批,2012年得以立项,2016年初完成拍摄,2017年4月17日,播出后一集变遭遇停播。
《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重要作品,它每一次走向荧幕、舞台的路却又都历时甚久,磨难颇多。这份磨难,既来自原著本身内容的复杂性,也来自50万字改编为数万字剧本的艰巨性。
小说《白鹿原》:出版后被批评重复揭伤疤
从《白鹿原》完稿的那一刻,陈忠实就隐隐有些担忧,他在写给编辑何启治的信中特意留下一些叮嘱,他说希望能让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并没有出现陈忠实担忧的波折,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书一出版,陈忠实收获的来自读者和文学界的反响,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高度赞扬之外当然也有批评声,对此陈忠实和何启治都曾说,尚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因为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争论。

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陈忠实在他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文中写到,“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陈忠实在若干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对《白鹿原》最大的误读是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白嘉轩和鹿三的亲密让很多人认为这是模糊了阶级关系,但陈忠实认为,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没有改变。“过去文学作品里写阶级关系,都是地主既想让长工干活,还不想给长工工钱,不给长工饭吃……地主需要勤劳的互相信赖的长工,地主再愚蠢也不会为了省下一碗饭,让长工干不好活。不能为了显示地主的坏,连基本常识都不管了。”
另外就是对白灵被活埋的情节,这种对于极左革命历史的描写是否真实可信、能不能涉及也是各界围绕《白鹿原》探讨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样的定论让《白鹿原》的影视化、戏剧化过程变得困难重重。对于历史倾向性的误读,更是成为《白鹿原》不能搬上舞台、搬上大荧幕的理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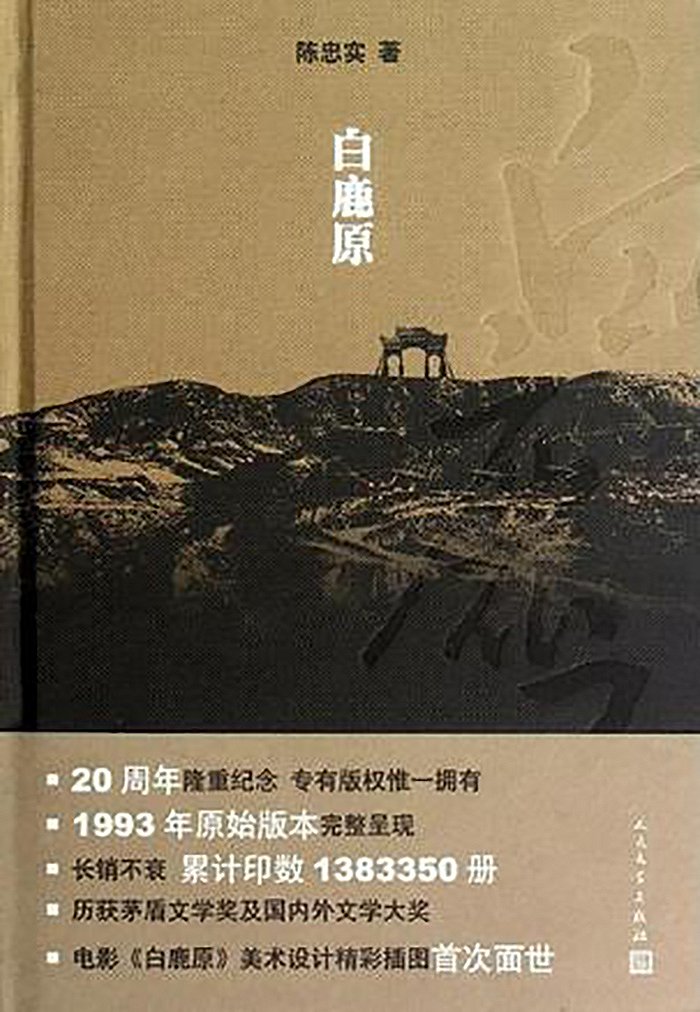
电影《白鹿原》:一路坎坷 一路前行
1993年,在《白鹿原》出版一个多月后,当时远在美国的导演吴天明就看到了这本小说,而且联系上陈忠实,获得了翻拍电影的委托书。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改编潜力的不止吴天明一人,谢晋也随后联系了陈忠实,可晚了一步。
但曾经一纸对《白鹿原》“不许拍电影,不许拍电视剧”的禁令,让吴天明手中的委托书很快过了期限。
时光荏苒,来到了2002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建国发话,要把陕西建设成影视大省,并且提到了《白鹿原》。很快,西安电影制片厂立项成功,并委任芦苇为编剧。到2009年王全安版电影开始拍摄前,芦苇在导演人选上先后举荐过王全安、陈凯歌、张艺谋、吴天明。
200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已经成立了《白鹿原》摄制组,王全安任导演。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没到位,《白鹿原》项目卖给北京一家名叫紫金长天的公司,制片人的理念与剧组矛盾很大,随后王全安退出,剧组也宣告解散。
又过了5年,到了2009年,王全安团队再次获得改编权,电影《白鹿原》重新筹拍。
2012年9月15日,电影《白鹿原》上映,公映版时长156分钟,送到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版本为188分钟,另有一版内部放映为220分钟。陈忠实给电影打了95分的高分,但也曾在采访中表达过一丝遗憾:“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革命者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
比起陈忠实这个“外行人”的夸赞,电影圈子里的各路人士对这版电影的批评之声却着实不少,第一个发出负面声音的便是编剧芦苇。芦苇在电影上映后就声明,自己历经五载、七易其稿的剧本被王全安“调包”,将《白鹿原》拍成了“田小娥传”。而观众较多不满的一点是,电影对革命者形象白灵和朱先生的删节。
尽管电影《白鹿原》已经完成,但对这部巨著的影视化辩论从未停休。从立项到公映,突破的是“不许拍”的困难,从公映到争论不休,探讨的是如何拍好的难点。
芦苇曾在采访中表示,原著时间跨度大,人物繁多,影视化改编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去选取、梳理人物与情节,再处理为电影画面。陈忠实也曾提过,不论任何形式的改编,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时空限制,舞台和荧幕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也许只能等电视剧了,那个不受时空限制,装不下再续一集嘛。”
因此,何处删、何处留,在改编者需要辨别的地方,也是观众评判和谈论的关注点。《白鹿原》原著围绕白、鹿两家的争斗,展现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口,人们所经历的矛盾与选择。在芦苇看来,这正是《白鹿原》的价值所在,他曾表明:“这个小说就是讲新旧两代人、新旧两种价值观撕裂的过程和痛苦,以及它里面的关怀。我的剧本是牢牢的抓住这点走的。”
改编《白鹿原》时,引起芦苇关注的另一点便是书中新旧道德的关系,这也是观众评价电影时争论的方面。芦苇看来,《白鹿原》中展现了新旧道德的矛盾与冲突,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让传统的儒家旧道德崩溃,但旧道德中也存在合理的东西,诞生的新道德同时也遇到新问题。原著中对旧道德的冲击、对新道德的建立,仍发生在当今社会的进程中,《白鹿原》显现的现实意义使改编难度上升,也让观众的期待与要求变得更高。
芦苇认为,改编版的《白鹿原》还应该展现关中文化的乡土魅力,他表示,现有的电影、歌舞剧、话剧等,在关中乡土魅力上都有一定缺失。正因如此,由芦苇担任编剧的新版电影《白鹿原》剧组目前正在西安选景,预计于2017年底开机。

戏剧《白鹿原》:与小说的逻辑截然不同
在电影《白鹿原》被搁置的2006年,话剧版《白鹿原》抢先以视觉形象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当年,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收获了许多好评,2016年,孟冰编剧、胡宗琪导演的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上演,被称为“陈忠实最满意的戏剧版本”。
比起电影、电视剧版《白鹿原》,话剧版《白鹿原》的筹备进程相对不那么坎坷。孟冰是两版话剧的编剧,对《白鹿原》走向戏剧舞台的改编过程很有感悟。当年北京人艺和陈忠实签了3年的作品改编权合约,林兆华找到孟冰的时候,已经是合约期限上的第三年了。两年间请过几位编剧改编,林兆华都不大满意。时任总政话剧团团长的孟冰,并没一口应下这个重任,待到重读几遍小说后,心中有了大致的想法,方才同意。
孟冰接下改编任务的时候,社会上正有一股名著改编热,很多编剧提到了“对原著的超越”的问题。面对《白鹿原》,孟冰至今仍认为,话剧改编的局限性和原著的高度,都让他没有能力去超越原著。“能在舞台上运用戏剧的形式,诠释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还原人物的基本形态,观众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成就和作品对社会、人性的刻画,就已经十分艰难了,谈何超越。”在接受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时,他说道。
孟冰表示,比起原创剧本,改编剧本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戏剧环境与文学环境的不同,改编不是直译,更不是复制粘贴。“戏剧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带有规定性、限制性、甚至强制性的,其中有来自社会公德的约束,例如要考虑看戏着装不能太随便,剧场也不能吃东西。同时剧场环境要求观众得随着剧情一气呵成地走,不能回看也不能快进。即使观众有情绪性的反应,比如哭或者笑,戏不会停。”而文学的个人阅读更加随意化,随时可以中断,可以重复阅读某一章,可以前后跳跃。孟冰认为,这种戏剧环境对观众的制约最终体现为对戏剧内容和创作方式的制约。“你的作品适应这样的一群人的接受,适应在这样的环境中呈现。”
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李龙吟也曾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戏剧逻辑和文学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戏剧逻辑,即冲突,才是改编文学作品的前提。《白鹿原》原著中不乏各种矛盾与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并非一一适用于戏剧舞台,因此就要寻找小说里符合戏剧逻辑的部分,并且用戏剧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
孟冰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剧本创作阶段下了大量的功夫,将原著拆散后一个情节一个情节地梳理,再提炼一张人物关系图贴在墙上,随后用这张图梳理人物命运的发展与历史事件的发展关系,之后再反复多次提炼必需的主要情节。“你必须把自己化进去,如果是站在外部从筐里往外挑挑拣拣,是必然有要缺失的。只有把自己放进筐里,再拿出来的东西,才是连根错节地带着你自己的东西,还带着原著的汤汤水水、枝枝蔓蔓,能水灵灵地、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白鹿原》是逼着我在文学样式和戏剧样式之间转化,用戏剧的方式进行再创造。”
孟冰的剧本最终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著中的白、鹿两家的主要人物,乃至像白孝文媳妇这样一个原著中没有具体交代姓名的人物都留在了舞台上。孟冰称取舍上的主要标准是“保持小说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主要故事线索”,每个人物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台词多少,而是体现在对整个格局的作用上。

尽管孟冰试图“忠于原著”,但仍不免删减原著中很大篇幅,他表示“书里描写政治斗争的过程都很复杂,这些内容大部分都省略了。”时空限制带来的戏剧容量问题让孟冰向林兆华提出过,能不能写成上下部,分两个晚上演出,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戏剧环境和观众接受度,最终放弃了这个设想。最终孟冰的剧本以白、鹿两家的争斗纠缠为主线,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场,以“仁义白鹿村”牌匾倾覆、老年白嘉轩伏地痛哭作结。
孟冰表示,《白鹿原》的戏剧呈现不单取决于剧本的水准,也取决于戏剧演员的表演和灯光、音响、道具等工作人员,取决于整个剧组对舞台的规矩、熟练程度等。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给孟冰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群众演员的艺术水准,当时孟冰根据导演胡宗琪的想法,将村民设置为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形象,集体出现推动剧情的起承转合。孟冰印象中,群众演员比主角还累,要换好几套衣服,每个动作的节奏、起伏度都能整齐划一,没有半点松懈,彰显出陕西人艺的艺术素养。
尽管话剧版《白鹿原》比起电影版收获了更多的称赞与夸奖,孟冰认为《白鹿原》的改编过程中依旧有着遗憾。他说,对白鹿原的评价,从小说到电影,争论没有停止过,但并不是有益于对作品理解的争论,而是“不能这样”和“不能那样”的争论。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往往造成主题先行、意念先行,作品容易缺乏艺术家的真实感受,缺乏社会真实体验的感受。“在改编《白鹿原》的时候,都是小说原著里的内容,有些台词却得被删掉。这反映出一种没有自信,对自己文化的认同的不自信,对自己艺术家的创作的不自信,对自己艺术院团的演出的不自信,对观众的接受度、理解度的不自信。”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