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书法创作事业发展,2023年12月23日上午,在四川大学社科处和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指导关怀下,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创作委员会工作会议暨书法创作研究论坛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圆满举办。会议由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创作委员会主任彭再生主持。论坛主题设置为“展览时代情境下的书法问题与创作路径”,旨在从当前书法发展的客观环境与现状出发,对相关现象及问题展开剖析与讨论。与会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现了应有的学术态度,这对于推动书法观念的百家争鸣、书法创作的百花齐放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发言题目:《高校书法在展览时代的立场》
发言摘要:书法展览是当下书法发展的重要表现,甚至有人说,当下已经进入了“展览时代”。首届书法展览于79年在辽宁举行,此时全国书协还未成立,由各省商议举办。评委包括:杨仁恺、启功、胡问遂、胡公石、李立。参展作品由各省推荐,整体展览倾向传统。中国书协成立以后,举办了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各次展览。除中书协80年代主办的展览以外,各地也热情地举办大中型展览,以河南举行的“国际书展”“国际临摹作品书展”“墨海弄潮进京展”最具影响力。随后,又出现影响力较大的“中青展”,这些展览总体倾向创新。九十年代后期,举办了有争议的“流行书风展”。为了纠正粗俗问题,中书协强调展览要重视传统、重视经典。展风改变后,又出现过度装饰、强调传统、缺乏创造等问题,这种“展览体”也受到批评。近十年来,网络发达、自媒体兴起,基本上左右了国内书法批评。如对丑书的批评,延伸到对民间书法的否定,甚至对清代碑学的否定等!
高校书法专业兴起,在书坛风云中应怎样对待呢?高校书法既不能混同社会团体,更不能轻易附和网络舆论。应该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和立场,做到旁观者清。我以为,对全国展览既要重视传统又要提倡创新,不能顾此失彼。对待书坛出现的各种艺术思潮,不要轻易地肯定和否定。如面对“现代书法”,要去追究其出现的原因,认清与其他艺术思潮的关系、它出现的社会基础和艺术价值以及它能走多远等。又如针对民间书法的否定,明确这是对文艺发展常识的缺失。中国传统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等都要“采风”,都要向民间学习,为什么书法不能向民间书法学习?另外,学习民间书法,不等于成为民间书法,还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出新的问题,只重视经典或只学习民间书法都是片面的。总之,高校书法应以理性、思辨、学术的立场站在舆论的制高点,力求引领书坛。并把这个理念贯穿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认知,不让青年学生被社会现象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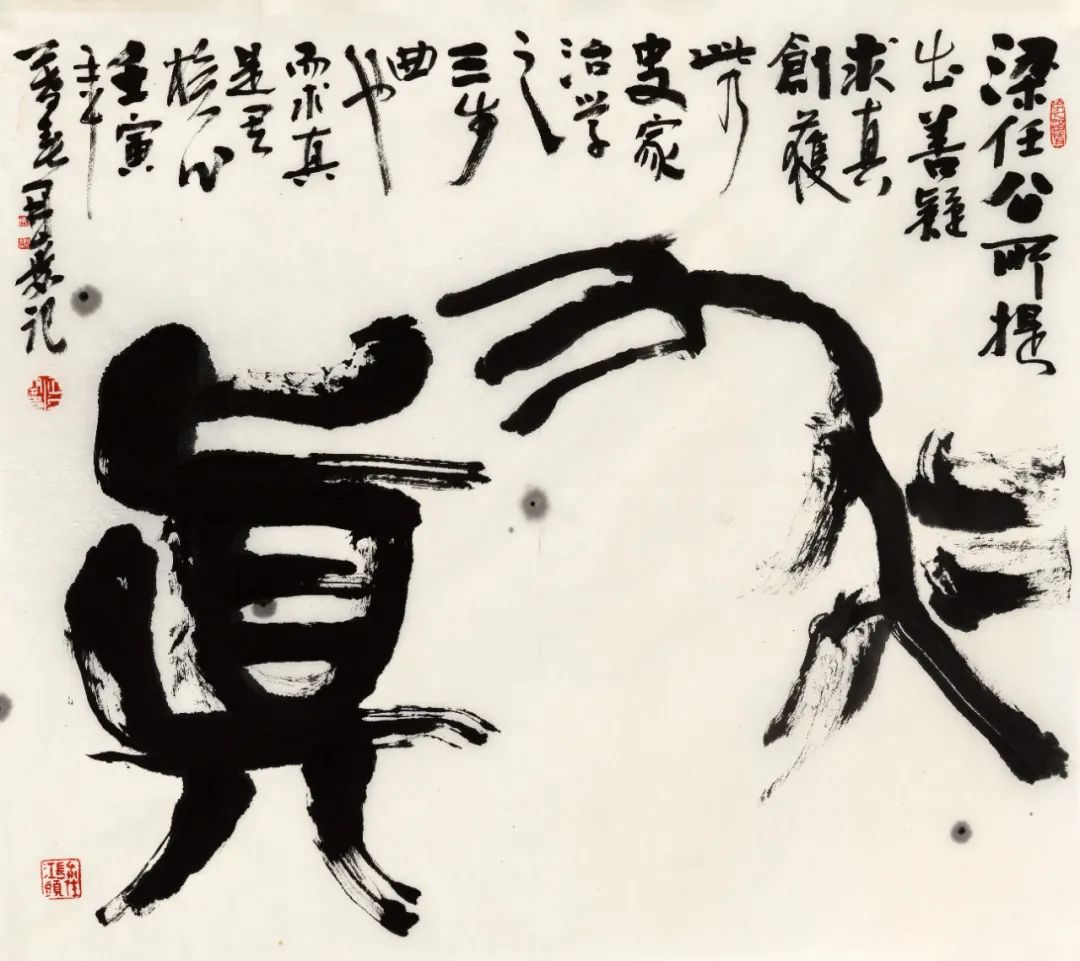

发言题目:《对展览时代下高校书法的思考》
发言摘要:关注当代书法,就要关注当下展览。中书协主办的全国展已有40余年的时间了。历十二届以来,其审美和取舍是值得分析关注的。从数年前的“取法随意、书写宽泛、形式较为简单”,进入到了如今的“取法鲜明、笔墨讲究、形式精致、审读精细”而一展难入的阶段。川大书法研究所以此为论坛主题,围绕当今书法创作的诸多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是具有积极意义和前瞻性的。
展览时代背景下,高校及全国书坛的创作当如何跟进?我认为可从“宏、识、精、专”四个方面来加以思考。
一、宏。宽敞的展厅展场需要大幅及宏篇巨制出现。由于幅式大,对作者的笔墨技艺能力和对创作要求大大提高了。比如以前在用笔上,中锋圆而能转,保持一定的技术能力,就基本能够可以了。但现在大幅作品的用笔要求,不但圆而能转,而且需有较大幅度的铺毫和提按,对用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那种厚重、畅达、灵动的笔墨,才能够把大作品的“面子撑起来”。这仅是一个用笔的问题。
二、识。就是聚焦在如何识帖取法上。在海量的历代优秀碑帖中,如何选帖、临帖、转换?案头功力的积累、综合性能力在作品中如何呈现?都是摆在作者面前的问题。需要什么呢?需要“根植经典、解析艺理、关照当代、书写性情”,尤其是如何能做到“精耕细作”。这会因作者不同的专注度而效果差异较大。
三、精。就是讲求形式雅致和笔墨精到。这是大的审美方向。以前的泛个性化、泛书写性的方式,进入到只有取法经典与个性溶汇和统一,才能在海量投稿中脱颖而出。还有就是字法与文本文字的精准性问题。近些年来,国展评审过程中加强了对文字、字法的审读。专业人员组成的审读班子,把很多字法和文本有误的作品挡在了门外。每次国展在最后审读关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作品止步于这一环节。“书卷气,精到样,雅逸相”是投稿作品的基本底色。现在全国高校书法专业生共计近万人,经高校培育出来的学子在国展入展中占据一大片天地。
四、专。高校书法在与当代书法创作的交汇上,呈现出有专业乏专攻的问题。唐孙过庭《书谱》中一个重要的论述就是笔墨的“心精手熟”。院校环境容易产生一种院校意识。长此以往而形成重论轻艺,重文薄技的现象。“锦绣文章旨奥理,黉门学子仰高才”,愿高校书法教育既重文又崇技,培养学生参与展览的意识,使其在分析、研习、探究当代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得到成长,不负韶华,担当起时代重任。


发言题目:《当代书法的困境与希望》
发言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便顺理成章,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书法,自然得到了从国家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当代也自然成了书法学习和创作的最好时代。作为书法人,我们理应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回报社会,但现实的情形却并不如人意。
先看看展览,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届展、兰亭展实际上已办成了新人展、习作展,究其原因当然是组织者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八九十年代的全国展有冲劲,有新意,但对传统的理解不足也是事实。近十余年的全国展则过于强调传统,把传统狭义地定义为经典中的几家,这明显有失偏颇了。造成的结果是学像一帖一家就能入全国展,而那些有想法有新意但可能并不成熟的作品则被淘汰了。要改变这种现状组织者在观念上一定要有改变,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励创新,鼓励写出新意、写出自我方能使全国展真正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高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展。
再来看创作,与全国展相反,当代活跃于书坛前沿的书家则更多地在放飞自我,在形式上求新求变,追求视觉的张力和展厅的冲击力,篇幅越写越大,花样越来越多。但线条则多是苍白空洞,经不起推敲。就如孙过庭所说“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实际上就是在用笔、结构、章法三要素中过于注重章法,而忽视了结构和用笔,而用笔和结构才是书法的基础和根本,只有把基础打牢实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还是希望当代书家静下心来,放平心态、敬畏传统、夯实基础,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书法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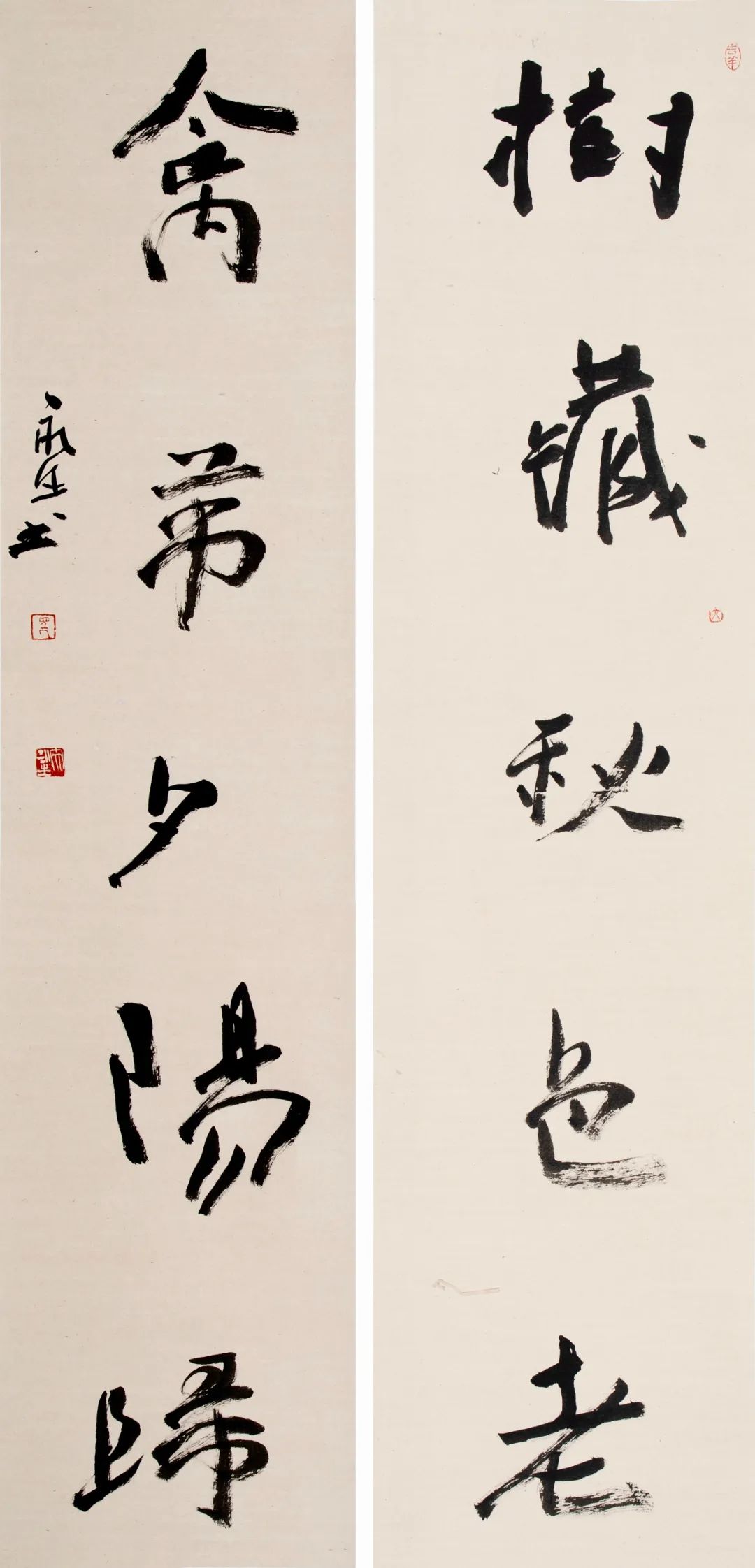

发言题目:《展览时代个性书风问题刍议》
发言摘要:经过四十年来的发展,当代书法已进入一个展览时代。毋庸置疑,展览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通过书法展览,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优秀人才和书法家。大家交流书法、欣赏书法的方式得以改变,主要渠道是在展览馆观看各种书法展览,数以百计、千计的作品济济一堂,悬挂在一起,成为当今书法展示的主要平台。书法作品的展厅化依然是今后的必然走向。
尽管现在的书法展览热潮不断,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每天都有展览开幕。仔细想想,这些年来展览中又有多少作品被人记住,亦或被人津津乐道,大都是过眼云烟,展览结束了,作品什么样也就忘了。究其原因很多,形式的僵化,观念的保守,意识的滞后等是重要原因,还有就是同质化严重,有个性、有特色、有震感力的作品太少。关于当前展览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技法,轻情感。古人作品为什么耐人寻味,艺术感染力强,是因为古人的创作都发自内心,抒发情感,为自己而写,无功力色彩。现在的书法作品,大都是为展览而写,创作就是为了参展,功利色彩明显,为创作而创作。许多作品技法不错,但缺乏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
二、重形式,轻内涵。现在所谓的“展览体”,其实就是形式雷同,同质化严重;线条油滑、单薄,内涵不够。作品内涵反映作者内在素质和综合修养,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的体现,是“字如其人”的个人情感表达。
三、重经典,轻民间。即取法单一,对传统认识的不够深入和全面。书法传统包括两大系统:名家作品与民间书法。名家作品是公认的经典,我们学书法,首先要学经典,学共性,学法式。但一旦掌握了这些法式、共性后,如何创作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这个时候,就应该拓宽传统视野,广收博取,一手进入名家书法、一手进入民间书法。民间书法有许多也是经典作品。如《龙门二十品》《好大王》《爨宝子》等。民间书法作品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更具鲜活力,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
我们的作品如何在展览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最终还是靠作品独特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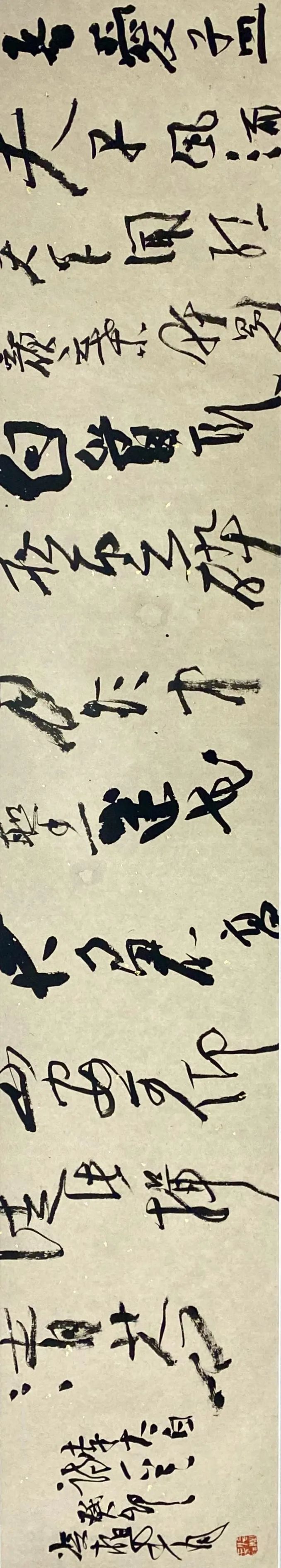

发言题目:《展览仍是促进书法发展的有效手段》
发言摘要: 当下的书法展览很多,仅仅四川区域内的书法展每天基本都有,展览可以说是极大地推动了书法作者创作的积极性,但统观当下的展览,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展览重数量、轻质量,搞热闹成为个别展览的显著标签。二是部分展览的策划性偏弱,展览没有对作品主题、内容、展览氛围等进行有效的思考,随意性大。三是展赛的书体通道很狭窄,黄庭坚草书、魏碑楷书、小行草等充斥展览,书体有些单一,比如颜真卿、褚遂良、吴昌硕风格的作品很难参展,很多优秀经典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四是展览裹挟下的书法,明显具有表演性:夸张变形、抓眼球。油滑简单、缺乏文气的作品还较为普遍。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精神气节的丧失,追时风、走捷径等功利思想扰乱了作者的创作心智,这显然违背了艺术的初衷。我们当下的书法人对展览应该抱有检验自身实力但又不深陷其中而苦恼的心态,自然生发的就是自我的,自我的才是最好的。当然,瑕不掩瑜,当代展览在促进书法繁荣、普及民众书法审美、传播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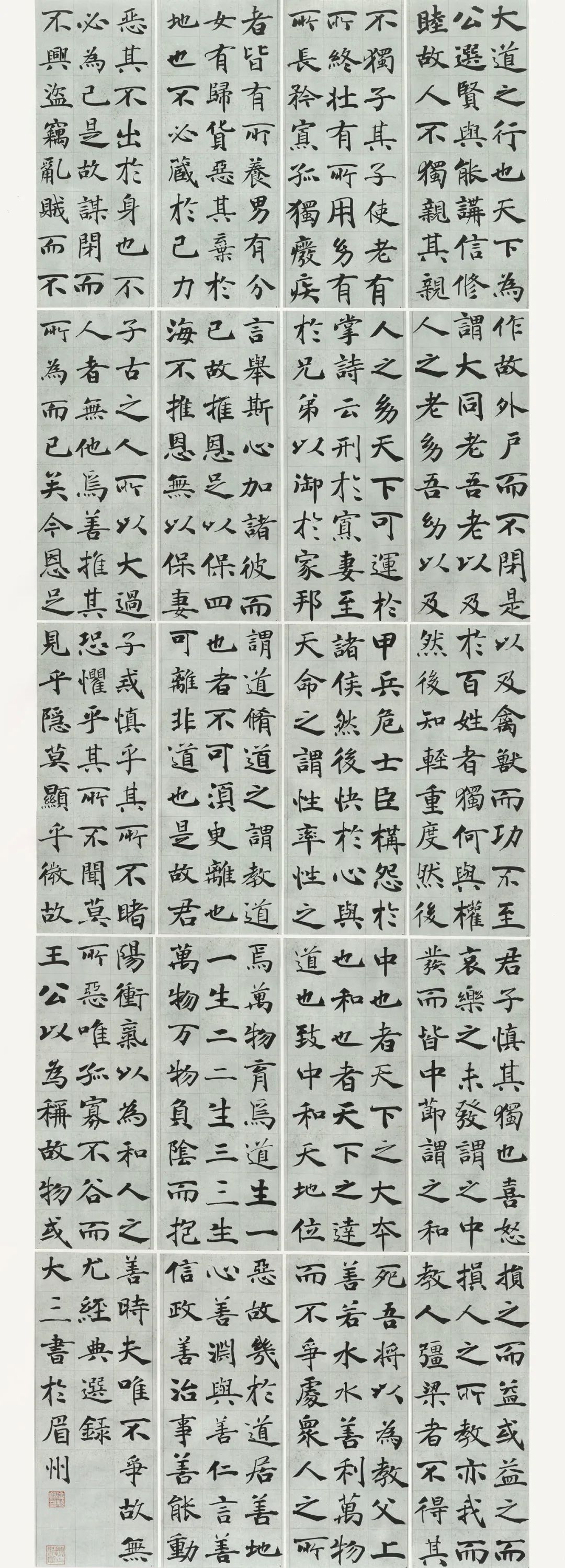

魏爱臣,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四川省青联常委,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书法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书画院书法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发言题目:《略谈当前书法发展的三个方向》
发言摘要:当前书法的良性发展,我认为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重视开放性。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体现在国粹上,书法文化是重要代表。从全国展来看,千人一面已经遭到书法界的共同认识。我们应该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以开放性的眼光与思维看待书法在当前的发展与形势。比如,关注地域书法、推动书法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借鉴当代艺术,等等。
二是立足文化性。当前书法展览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尚技、炫技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从根本说是对书法的文化性认识不够,重技轻文、重表面轻内涵,而忽略了文化才是书法的根基和来源。熊秉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们要克服短期功利性,从长远的、深层的视角来看待书法与书法学习。我们倡导向经典学习,并不仅仅是向经典的技法学习,更重要的是向经典的文化学习。
三是彰显学术性。全国书展的同质化与单一化,同样也是缺乏学术性的一种体现。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发现,中国书法的取法资源越来越广泛。简牍、砖瓦陶文等民间书法以其独特的魅力而为具备慧眼的书家所青睐。兼容并包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历史性与学术性的眼光,我们要善于鼓励不同书家从不同经典中汲取营养、各取所需,进而推动书法的多元化与创造性。同时,对于展览,我们需要以更高的学术定位进行策划和组织,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学术引领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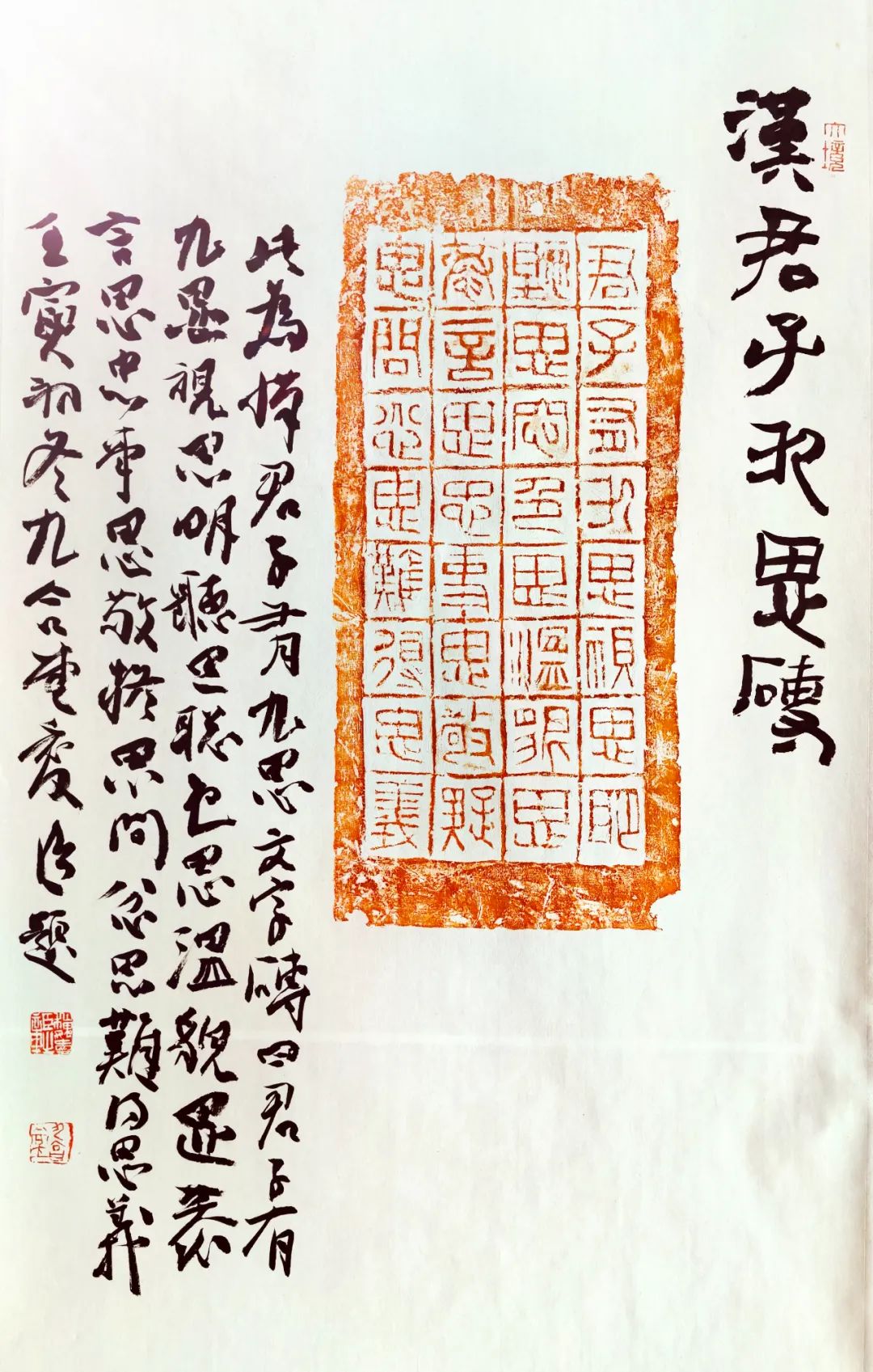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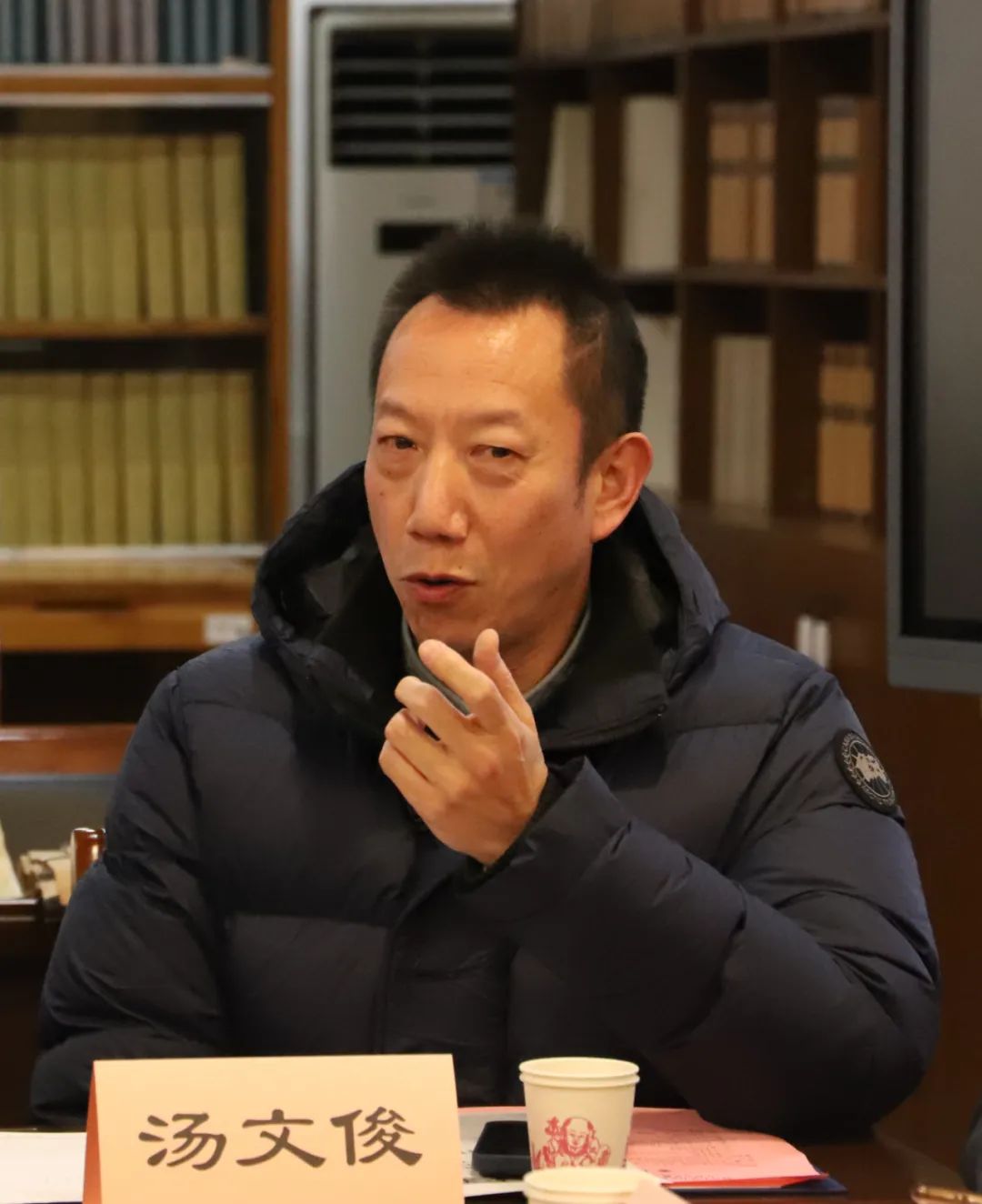
发言题目:《关于当前书法展览的几点看法》
发言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代书法的热潮至今依然持续高涨。在这一股热潮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书法人才,使书法渐渐从文人雅士在书斋里独自把玩的小视野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大视野。展览成为主流形式,同时助推了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机构从只展西方绘画和其他类型的美术作品,到书法占据一席之地的局面,书法也因此而受到更多关注。
传统中的经典书法作品多以尺牍手札为载体,信手拈来,但技法却非常高超,令后人为几个点画、几根线条痴迷并因此穷尽一生,甘愿抽筋折骨、九死不悔。遗憾的是很多人一路走下来,路径不当,可能根本入不了书法的门径。
当代的展览热潮亦是有这样的一面,充满矛盾和困惑,甚至是迷茫。一方面急于参展,在患得患失中等待结果,另一方面,明知自己的技法处于低水准却硬着头皮上,最终不尽人意,于是在自怨自艾中渐渐毁掉了自己。从具体的学习实践来看,这就是路径选择的失误,没有深入经典和累积经验。要得书法中的“味”和“质”谈何容易,究其根源,“技”的欠缺首当其冲。在这个以展厅形式为舞台的大环境中,很多作者在把古人经典作品由小拓而为大的时候,缺少对点画、线条、墨色、章法的驾驭能力,再加上对书写工具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经验的不足,难以支撑起作品的深度,尤其是大作品,致使作品空洞无味,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融入展厅的空间效果和氛围营造,作品和展厅的协调性脱离,视觉上缺乏美感,精品难出亦是意料之中的事。
当下书坛亟待加强的就是减少浮躁,应引导书家深入经典,回望传统,立足当代,提高作者的综合素养,把创作从高原而登上高峰。


发言题目:《书家字用现象应成为书法创作研究的重要内容》
发言摘要:字用即文字的使用,是文字记录语言的体现。文字学上的字用分析,即是考察一个历史时期文字的具体使用情况与表现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字书写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如字形讹混、误书错字、重文合书、美化装饰,都是文字学字用分析要关注的范围。黄德宽先生在《古汉字发展论》中指出,书写现象是字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开展汉字发展研究应该关注文本的书写问题。五种字体发展成熟以后,中国书法传承的文本主要是书法家书写的墨迹或墨迹刻本,也包括大量不知名的书写者留下的文本。这些文本因书写者个人的知识背景、审美趣味、书写习惯、书写方式的不同,会对书写文本产生影响。被历史所承认的历代书家之书迹,其字用现象应首先成为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曾提出字书与篆迹宜相参为用的看法。《说文》等字书对历代篆文书写字法的规范性一直起到关键作用,历代名家篆迹的篆法,既能反映书家个人的字用特点,也能反映其与历代字书之联系。早在汉代,许慎就在《说文》中征引李斯秦刻石中的“也”“攸”“及”等字。徐铉校定《说文》,也曾列出“几”“凡”“以”等十三字出自李斯、李阳冰石刻而异于《说文》的形体。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亦将《说文》小篆的“长”“言”“羽”等八字与李斯、李阳冰篆文作辨析,说明历代文字学家颇注意书家字用的研究。
举例来说,我在考证李阳冰篆迹中,得出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不全是李阳冰刊定《说文》的新看法,又从李阳冰篆碑中的篆法反证其刊定《说文》的面貌,还联系唐代篆文去证明《说文》大徐本、《汗简》、林罕、梦英等字书与篆迹对李阳冰的继承,即是对书家字用现象研究的尝试。书法创作研究不能止于仅写写字,不能止于仅作风格描述,不能止于美学层面的形体结构分析。唐代的字样学,很好地促进了文本书写的规范性。明清出土北朝碑刻日多,又有顾炎武、钱大昕、赵之谦等考辨俗字,这些都是字用研究的传统。只不过今日书界多以这些研究为文字学范畴而不加重视,实在是一大误解。搞书法创作的人,能稍作一下书家字用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书法创作,且能更深入地剖析书家之艺术风格,而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拓宽书法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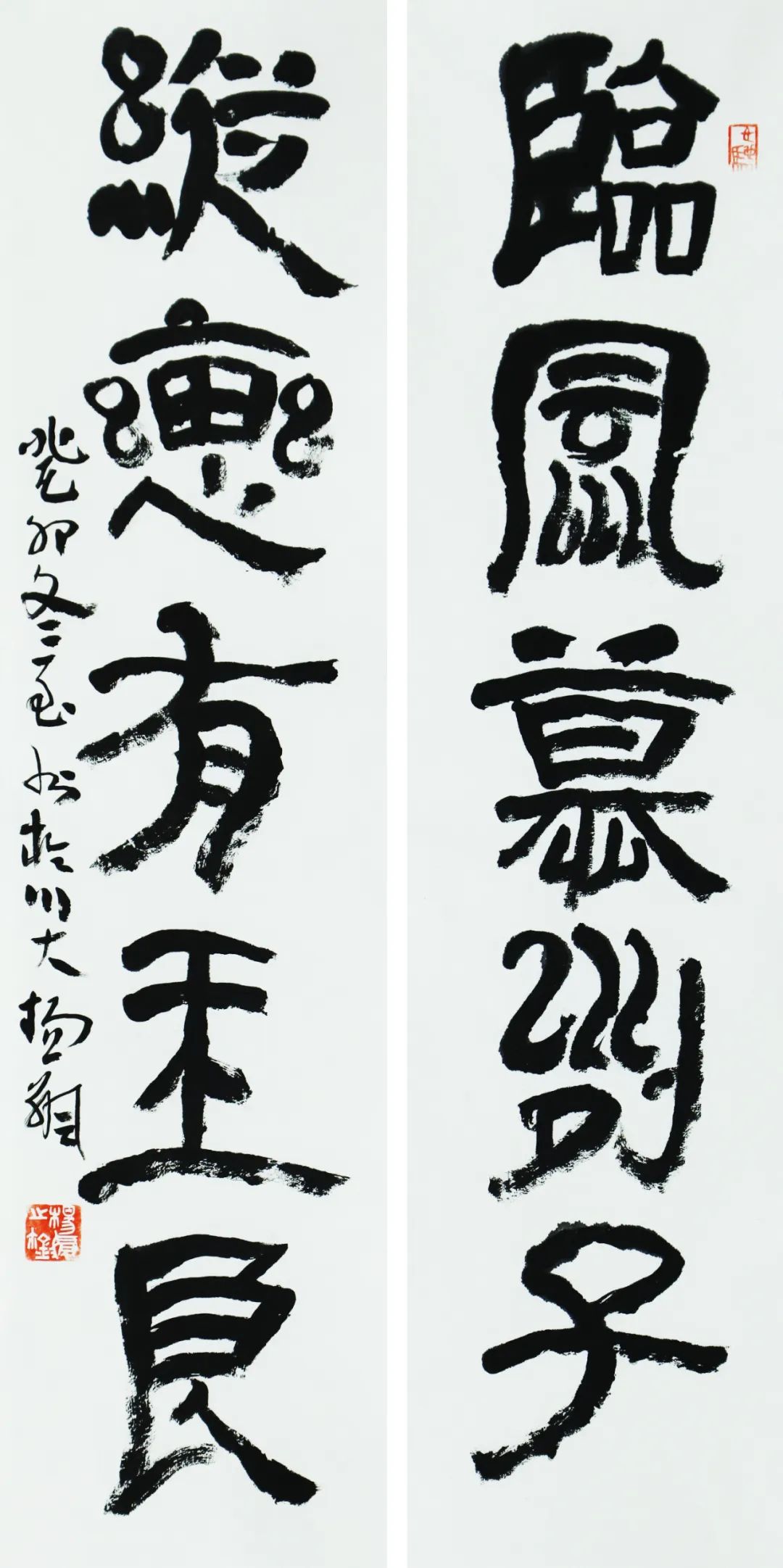

发言题目:《学书历程与隶书创作体会》
发言摘要:我主要谈一下个人学书的历程与体会。我的学书经历刚开始是立足篆书,比如本科阶段主要是吴让之《宋武帝与臧涛敕》以及邓石如等清代篆书,对它们的学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我现在还保留有清代篆书情结。后面又写过一段时间隶书,再后来慢慢把精力主要放在草书上。有一年在杭州,张羽翔老师来杭授课,那时正是“广西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当时写《书谱》,主要是放大书写,八尺屏尺幅。张羽翔老师看了我的书写,非常赞赏和鼓励。我坚持这种写法写了三年左右。来川大报考研究生时,我把写的那种大字二王草书给侯开嘉先生看,侯先生认为非常好。后来,随着学习深入和认识提高,我意识到,要想在行草书上真正格调高古,线条质量过硬,需要向篆隶书学习。
就隶书学习来说,我觉得汉碑是基础。在汉碑基础上,我非常喜欢金农隶书。所以,近三年来,我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金农隶书上。从笔墨语言到形式感,金农隶书都是一个高度,难以企及。其中,金农《临华山碑》既有碑版的庙堂之气,又有简牍的笔墨意味,二者兼具、天真烂漫,为我所最为青睐。预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将金农的这种隶书作为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由此生发的问题是,金农隶书在展览时代,应该如何解读?金农隶书如何既能适应展厅效应,又能兼具日常书写?这是我现阶段着力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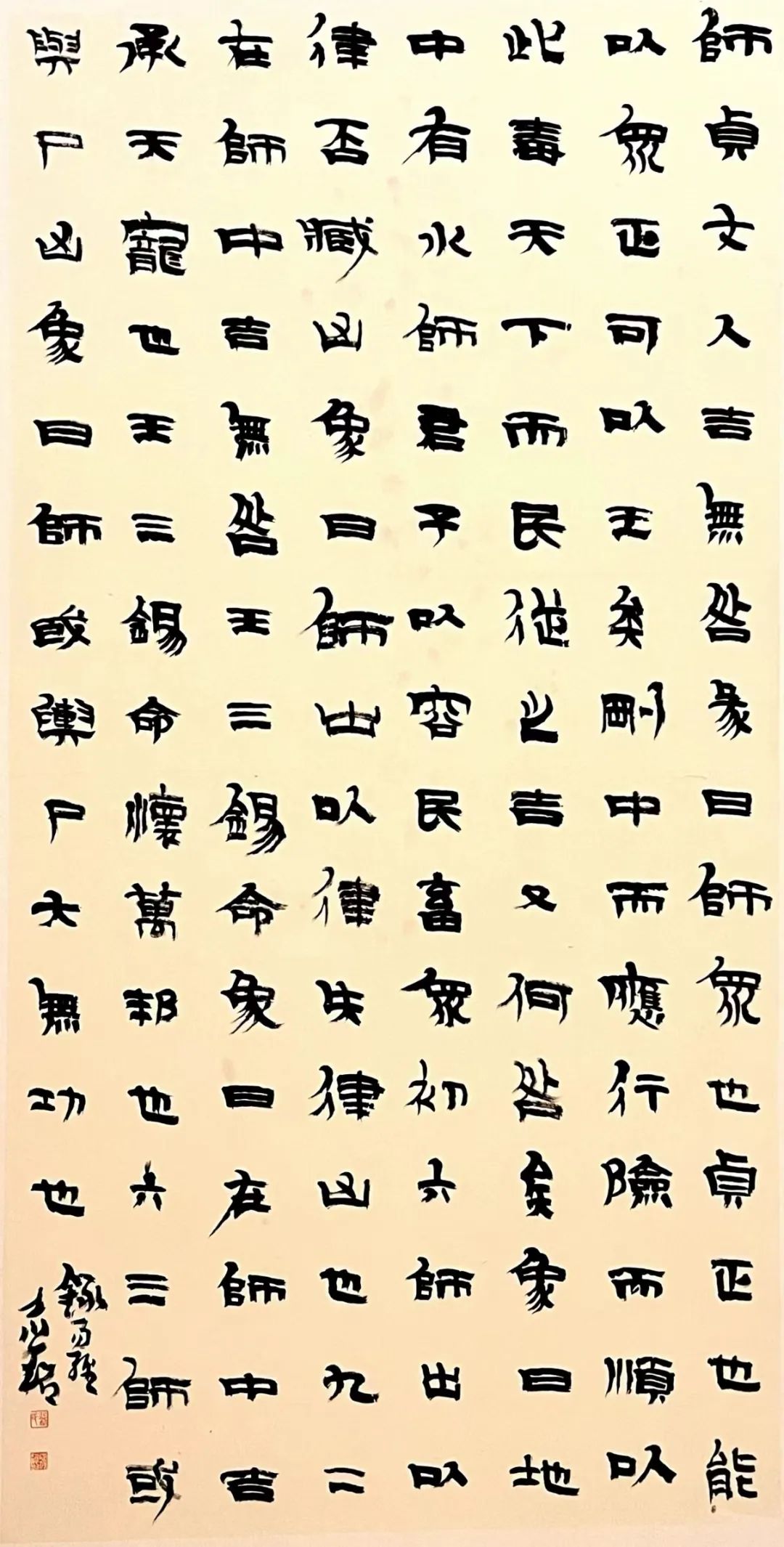
来源:推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