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仅有12万的达尼丁是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也是奥塔哥地区的首府。尽管没有奥克兰的人口规模和惠灵顿的政治地位,但它在新西兰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150多年前,这里的金矿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外来者,他们抱着致富的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
中国移民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先是为了躲避战乱不远万里逃到大洋洲,一部分人最终在新西兰落脚。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奔波,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生活,陆续而来的华人移民也加入其中,让这座小城热闹起来。
艰难生活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经历着内忧外患,反抗、战争、贫穷和饥饿冲击着普通人的生活。当时,广东大部分地区像是人间地狱,家族中的男性不得不向外寻找生存办法。成功漂洋过海的一小撮人在美国加州找到了机会,紧接着澳洲的维多利亚地区也发现了大金山。据统计,当时有约4万6千名中国人在澳洲本迪戈地区淘金,一部分从墨尔本来到了奥塔哥。
“我的祖先们都交过100英镑的人头税。”Glenys Shum对界面新闻说。她的祖辈是最早一批到新西兰的中国人,如今66岁的Glenys已是家中的第四代。
刚到新西兰时,华裔并不受欢迎。确切的说,早期的中国移民遭受着恶劣不平等的待遇,人头税(Poll Tax)就是其中一种。美国加州在1852年制定了反华人头税,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效仿起来。1881年新西兰政府制定了具体标准,每个进入新西兰的中国人需交纳10英镑,这一金额在1896年涨到每人100英镑。

歧视性的税收并不能阻止华人的外逃。Glenys常常从长辈那儿听到当年的故事,比如有人为了离开村子,靠游泳逃了出来。

尽管Glenys没有亲历逃亡的过程,但艰难的日子还是持续了很久。因为备受歧视,中国人无法在当地找到体面的工作,他们只能凭借攒下的钱开一个杂货铺,做做小生意养活一家人。上学时,常会有小伙伴称Glenys为“ching chong china man”。在Glenys看来,这是新移民未曾经历的黑历史。
Glenys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年轻时开起了一个杂货铺,以维持大家庭的所有开销,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等到她父母结婚时,Glenys的母亲不得不自己另开一家店以维持小家庭的生活。Glenys和兄弟姐妹从小就学着帮母亲洗菜、算账、照看生意。“那时候我们没有算盘或者计算器,所有东西都得记在脑袋里。”
重男轻女也成了家庭不得已的生存策略。“母亲告诉我,在她小时候,男孩在家中最受宠,一有吃的外婆一定会先给哥哥和弟弟,而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只能吃剩菜剩饭,有时只有清汤寡水,里面飘着几片绿叶菜,没有营养。”
入伍的父亲当上了空军,成为一家人的转折点。Glenys依稀记得是一位苏格兰裔的长官提拔了父亲,除了表现优秀,他也非常欣赏华裔对家庭的照顾。Glenys的父亲就这么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空军,退役后社会地位也不同了。Glenys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父亲托银行业的朋友找到的。“虽然开始的日子非常艰难,但与我同龄的朋友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

大家族在新西兰生活了100多年,Glenys的家庭里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传统。Glenys不仅照看父母,还照顾着家中的长辈。有客人来时,她总会做云吞招待他们。在当地华人组织里,她还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
现在的新西兰已经大不相同,没有人会指着Glenys的鼻子调侃她是中国佬,而Glenys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我不指望女儿以后会养老,我顾好自己就行了。”
1934年,时任海关部长宣布豁免“人头税”。2002年,在中国新年的庆祝宴会上,新西兰总理Helen Clark代表新西兰政府就过去的种族主义道歉,获得了不少华裔选民的支持。
“在达尼丁,很多律师和医生都是华人,他们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中国人也渐渐证明了自己了,他们非常努力。”Glenys说。
用力融入
与Glenys家族为了躲避战争而飘洋过海的动机不同,Teresa Chan的父母将她送出国则是为了更好的教育。
1980年代,香港的大学数量没有现在多,能被学生们列为“理想院校”的也只有港大这一所。还在念高中的Teresa虽然成绩不错,但想要考上港大的好专业却不容易。去澳洲成了父母给Teresa规划的解决方案。
在上大学前的一年,Teresa申请到澳洲一所女校继续高中学习。尽管,姐姐和弟弟也一起到澳大利亚求学,生活上能相互陪伴,但如何融入成了Teresa的困扰。“可能是因为我并不酷吧,女校里的小团体又多,我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进去。”
那时澳洲的华人数量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当地人对亚洲族裔的歧视还很严重。“常常有人在墙上写‘亚洲人滚出’这样的字眼。人们不会在意你是华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只会说你们是亚洲来的。”Teresa回忆到。
进入大学后,融入的主题仍然没有停止。除了审计,Teresa还选修了法律专业的课程,这给她自己增加了学业上的负担。“学法律就像是学一种新的语言,对非母语学生太有挑战了。我必须要在上课之前把所有内容先读一遍,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老师课上讲的是什么。”因为家庭状况并不好,Teresa还得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以补贴生活费。
几乎没有娱乐时间,这直接导致Teresa在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热衷聚会。“我的伴侣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还喜欢开趴体。‘你有什么问题吗?’他常常调侃我。”当然,Teresa并不认为自己在弥补当年的某种缺憾。“我很享受我的大学时光,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但回想起5年在澳洲的日子,我一直在很努力的融入周围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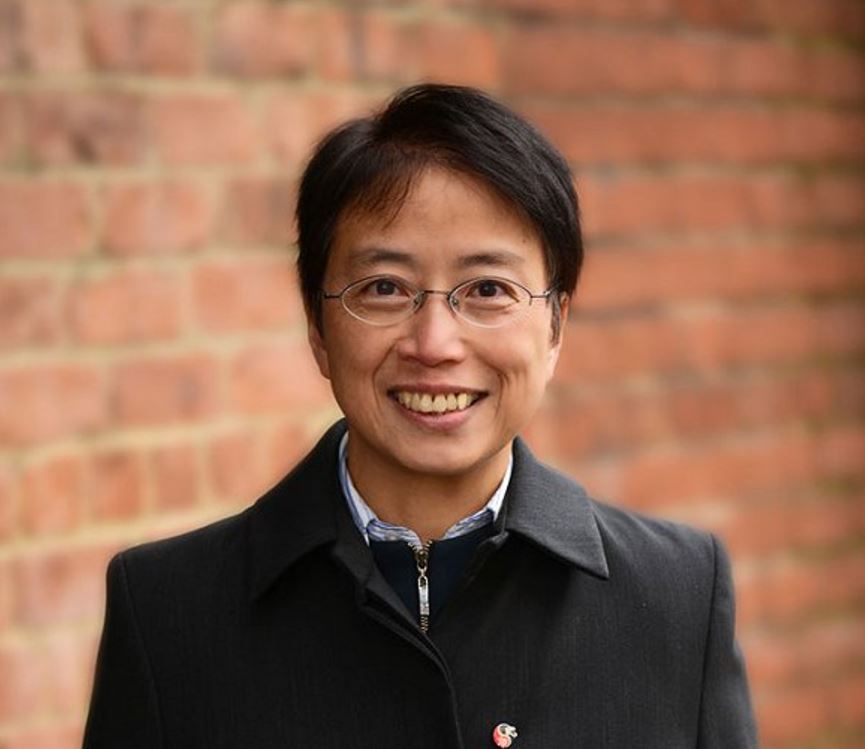
Teresa毕业后,一份在惠灵顿的工作机会将她留在新西兰,这一呆就是25年。“我在这儿感觉到和澳洲不太一样的氛围,在惠灵顿遇见的人会很愿意了解你,他们知道你不仅仅是亚洲人,也不仅仅是华裔。”两年后,Teresa跟随伴侣来到达尼丁。因为城市规模很小,Teresa的律所业务又需要和很多人有来往,她感受到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在达尼丁,人们一旦接受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接受,不仅肯定你的为人,还会想着如何照顾你。”
融入已经不再是Teresa的困扰,相反她成为一个施助者。她的律所常常帮助新移民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她还是“上海达尼丁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达尼丁和上海在1994年结成友好城市关系,联合会常常举办文化活动,将新老华人移民圈在了一起。
新移民
2009年,刚结婚的穆晓雁跟随丈夫从云南来到新西兰。与前几代的华人移民不同,她对居住地的选择更为自由。丈夫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在中国和日本工作过,结婚时,他们有三种选择。最终来到新西兰,是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更适合照顾子女和家庭。
刚开始的几年,穆晓雁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焦虑。在国内,生完孩子的女性总想着怎么能衔接好事业。出国前,她是一位职业白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来到新环境后,我之前在国内的教育和工作经验都和这边不接轨,生完孩子之后老想着怎么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呢?”那段日子,穆晓雁看到招聘信息都会去面试,做过几份与兴趣不符的工作。这种焦虑直到丈夫工作稳定后才消失,她渐渐接受了在家照顾孩子的状态。
全职主妇的经历反倒给她制造了融入新环境的机会。“我常常带孩子去参加一些Play Group,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而在一旁照看的家长也会彼此交流。”

在穆晓雁看来,达尼丁的小城氛围将人与人拉得更近。“等你呆到一定年份,你会发现认识的每一个新朋友都和过去的人脉有着某种联系,大家要么认识,要么眼熟。”也是因为朋友介绍,穆晓雁在Teresa律所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彻底摆脱了职业焦虑。作为律所的法务助理,她需要重新学习法律相关的业务,Teresa对中国事物的关注也让穆晓雁过去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从融入新环境的个人体验上来看,穆晓雁要比她的老板Teresa幸运很多。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顺风顺水了,比如给孩子找幼儿园就是一桩麻烦事。
她给孩子换过两次幼儿园,直到第三次时才满意。“刚开始很盲目,朋友家的小孩上什么幼儿园,我们也就跟着去了。而后才发现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是一个态度,背地里却不太一样。”
穆晓雁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幼儿园。如果用国内家长的眼光来评判,这所幼儿园状况堪忧。2015年达尼丁经历过一场大雨,幼儿园的旧址已经损毁,他们利用周边的教堂作为临时教学楼,陈列也并不华丽。
“我更看重的是老师们怎么教孩子。”穆晓雁认为,这所学校的老师鼓励少数族裔的孩子分享他们的特色文化。“比如学数数时,老师会鼓励孩子用中文来数一遍,其它小朋友都很好奇。这反倒是培养了孩子的自信和自豪感。”这种文化包容也让穆晓雁对孩子能放手,去追求职业上的成就。
“Chinese”
尽管新西兰的政客常常会以移民问题博取眼球,不乏有排外观点,但实际的文化融合氛围要好得多。作为新移民,穆晓雁也加入了达尼丁的华人组织,尽管他们常常一起聚会、看孩子舞龙狮,但在她观察中,二、三代移民对“Chinese”的理解却与新移民不大相同。
“他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对‘Chinese’的概念很抽象。他们会在家中置办一些有中国元素的物件,孩子也经常穿传统的中国服饰,看得出他们很想保留血液里传承下来的文化。”穆晓雁对界面新闻说。
这在Glenys和Teresa的父辈那儿也表现得很明显。早期中国移民进入新西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很多华人移民后裔们都想回中国寻根问祖。Glenys的父亲曾经回广东的故乡,看望依旧在世的亲戚,她的姐姐还在退休后担起了整理家族史的任务。“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知道家族是如何传承下来的。”Glenys说。
但不是每个人都幸运地找到故乡。战争后,许多村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模样。然而,尴尬还不止于此。
真正回家后,许多移民才发现他们对“故乡”的执念太过美好。“我父亲曾在2000年之后回香港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想象中高兴。在此之前,他并有意识到自己在澳洲的生活其实比在香港的要好。在澳洲,他能在花园里种喜欢的花花草草,然而回到香港,人们大多只能住在狭窄的小单间里。”
尽管上一辈人的“寻根”情结未必有善终,但这辈人对国内的关注却在增加。新西兰社会鼓励青年们在年轻时出国多看看,Glenys的女儿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后,女儿去过英国和新加坡,现在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工作。“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三个月前她告诉我,我可能快要当外祖母了。”Glenys说完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去年春节时,中国驻基督城领事馆从云南请来一支杂技团到新西兰来表演,从那之后,穆晓雁就心心念念想做些什么。“他们来的时候我挺自豪的。云南的文化艺术一直是很有民族特色,如果能将其中一些搬到达尼丁来该多好!”
Teresa也想要让达尼丁和中国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今年四月,第一届“2017中国电影节”在达尼丁开幕,当地政府、新西兰驻沪领馆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等组织都参与其中。作为达尼丁华人组织负责人,Teresa也是参与者。在此之前,她担心以京剧影片做开幕会超出达尼丁观众的接受范围,但听到满意的评价后,她放宽了心。
“第一次吃芝士时,我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种食物。接受新文化也是如此,但一旦接纳了它,你就慢慢学会欣赏了。”
(实习生周雅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