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段时间我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大热的丧猫表情包,一脸生无可恋的猫脸上还重重写着一个“丧”字。
谁知,几百年不主动找我聊天、有事都靠我妈传话的老爸特意发来语音,让我把头像换掉,他说:“丧字不吉利。”

我一方面讶异于这个头像竟然惊动了向来对我不闻不问的老爸,也忽然想到了在“丧文化”大行其道之前,单用“丧”字是中国人的忌讳,它所代表的“丧事”“丧期”“丧乐”等,无不跟死亡有关。
不知何时起这些概念在我脑海里已经很弱化了,即便每天说很多遍“好丧”,都跟它的原意扯不上一毛钱关系。但这些语义变化我无从跟父辈说起,与其跟父亲争执倒不如火速换掉头像来得简单省事。
我的父辈是生长在红旗下,啜饮无数心灵鸡汤,试图将鸡汤宝典传给下一代的人。从上学起学业上遇到什么挫折,回到家里获得的都是“你再努力努力,我们相信你”,以前这句话的疗效有如打鸡血,听完后当天写物理卷子都会有种错觉,虽然我依旧一道也不会写,但我开始感觉它们一点儿也不难。
再后来,我发现这种努力其实是没有尽头的。
父辈的思维常常是“不错,这次 考得很好,下次争取查漏补缺,考得更好”。虽说很多人长大后回顾上学的岁月,会怀念那时候趴在书桌单纯地上解题时光,感慨能够套用公式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题目,答案都是明确而肯定的。

即便如此,那时我就看到了人身上的局限,有人善文,有人重理,倘若颠倒,学得费力不说,效果也是事倍功半,这也让我开始怀疑从小被灌输的——努力就能成功。
后来这句话被修缮为“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成功”,一再被诟病后,演变成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
2、
恰逢台湾金曲奖揭幕,草东没有派对成为本届金曲奖的黑马之一。
这个来自台湾的小众乐队去年才开始进军大陆,今年就横扫“最佳乐团奖”。在投票环节,草东一举收割了19张支持票,而评审票总共就只有 20张。
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草东角逐这项大奖的对手几乎是在乐坛有着不可撼动地位的五月天,双方票数悬殊,结果可谓爆冷了。

草东仅有的一张专辑《丑奴儿》中收录了代表作《大风吹》,这首歌拿下当晚的“年度歌曲奖”。
哭啊,喊啊
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
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
孩子交点朋友吧
——《大风吹》
纪德在《如果种子不死》中说,“人当童年,心灵应该完全透明,充满情爱,纯洁无暇。可是,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心灵却阴暗、丑恶、忧郁。”
原来人性的虚荣与虚伪,是自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都说孩童最童真,其实他们比
成年人更明白尊卑贵贱与三六九等。
草东唱的是常人所不敢唱的“Loser之歌”,因而在越来越敢说真话的年轻人中大受欢迎。
我想要说的
前人们都说过了
我想要做的
前人们都做过了
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
——《烂泥》
这是一群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嘶吼的时候有热血和渴望,但更多的是深陷泥淖、自顾不暇的慌张,改变现状就和改变世界一样希望渺茫。
朋友分享过一首小诗:“惟尝到人生的苦味的人,对于人生乃真没趣。没有尝到的人,总很有兴的前进:他总觉他以为有味的东西在他前面。”
3、
中国的应届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这些年轻人每年六七月鱼贯涌入市场,就业竞争加大自不用说,应届生的起薪更是连年下降。
看过一篇报道大致说,高度普及的本科教育使得很多基层的服务业从业者都是本科文凭,在一定意义上拉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对于国家而言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势必是好的;
但于这些亲身经历者来说,一个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发挥一技之长,专业学识不受重视,在偌大的公司犹如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尊严早已跌落尘泥,生存也举步维艰。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办公室的白领们自以为自己的表现优于父母。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而已。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哼哧哼哧做PPT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醍醐灌顶。

我们都自以为能逃出平庸的牢笼,实则不过是牢笼换了个形式,我们就沾沾自喜,以为鲤鱼跳了龙门。
界限依然存在,白领们收拾得体大方,拎着小包走进市中心林立的一幢幢大楼里,打开电脑对着屏幕一天到晚写写改改,做不完还要接受着主动或被动的加班;
这和当年在棉絮飞扬的车间机械地踩着缝纫机的女工相比,除了多了外表上的精致,工作上所拥有的丰富度和话语权并无增加几何。
而面对这些可悲之处,却又束手无策,只能日常在朋友圈调侃一句“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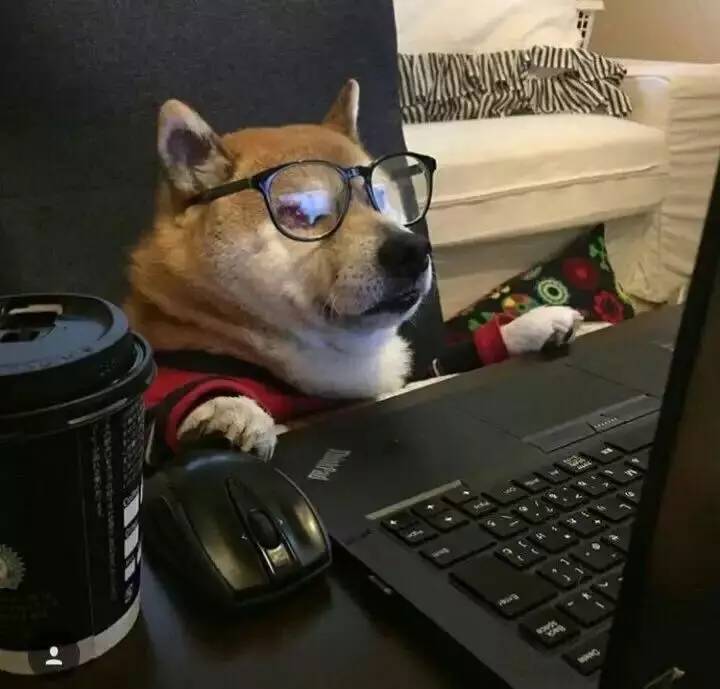
换个角度来看,近两年这些流行用语也都在隐隐折射出,年轻一代已疲于应付这泥沙俱下的现世生活。
无论是年少时多心高气傲的少年,多有灵性的孩子,长大后被迫与世界赛跑,大部分时间都是浸在“苦味”里,苦得逾久,知觉越是麻木,最后,我们就这样变成一个个平庸的中年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