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
作者:(美)马立博(Robert B.Marks)
译者:夏继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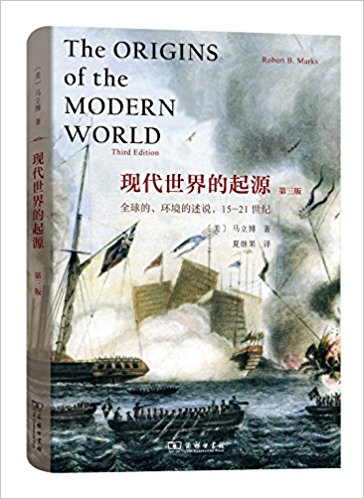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南加利福尼亚惠蒂尔学院历史学和环境研究教授马立博(Robert B.Marks)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环境史的整合研究,关注人与环境在历史上的关系。他曾出版在美国和我国均广受好评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等作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是他的新作。这本书有别于探讨欧洲崛起、现代世界起源的其他作品,将亚洲尤其是对于地区有着极强影响的印度和中国放在15-18世纪全球经济的核心,指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远远超过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与中印两国的贸易联系,也因此成为欧洲国家发起大航海运动的重要动力。
书作者还试图在环境的语境下,重述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转变。书作者指出,以1800年为节点,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欧洲、新兴的美洲,原有的农业经济都已经发展到发达程度,对于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字,这种情况下无法再以原有方式继续提升。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使得人类找到了对于能源、资源和环境更为有效的利用方式,突破了之前的制约,从而让世界人口猛增到之前不可想象的数量。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这本书开篇首先讨论了1400-1800年全球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环境约束。1400年时,全球人口约3.8亿,1800年,增长到了9.5亿。在这四百年中,全球人口中的八成约为农民。这期间,全球气候经历了多轮剧烈变化,也造成歉收甚至灾难。可以认为,当时的旧有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包括资源、环境、人力等维度的,在没有实现大的技术突破之前,将无法实现超越。同样,这期间亚欧大陆上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明也使得所在地区的生态承载水平到了一个紧张的程度。
早在13、14世纪,随着蒙古西征所拓展的亚欧大陆商路就已建立,而中国-东南亚,波斯湾地区,地中海地区的海洋贸易同样兴盛,出现了多中心的贸易繁荣。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生在现代社会之前的贸易全球化,只能成为农耕经济、游牧经济的补充。在旧的生物体制和技术背景下,经济发展促使贸易和人口增长,每当触发环境承载时,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瘟疫、剧烈战争。
这本书单辟一章讨论了15世纪及之后几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在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受到的影响。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明初一段时期的开明政治,也是当时经济体制的开放性体现。书作者认为,在永乐皇帝去世后,明朝政府内部的政争,打断了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可能,也给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留下了权力真空。在奥斯曼帝国无力东进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才得以跻身其中,后者期望通过殖民冒险来打通去往中国和印度的商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欧洲等其他地区。书作者指出,中国和印度,在当时的许多产业都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更有能力生产出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手工业制品,特别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印度的棉纺织品。印度棉布到了18世纪,仍然在品质上远远超过英国工厂的同类产品,价格还要低廉得多;即便掌握了殖民权力的英国当局通过歧视性的关税政策,限制印度棉布进入英国本土,也无法阻止这种强有力的竞品在世界市场上将英国产品排挤到边缘化的位置。
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与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世界体系开始不可避免的发生触碰,直到最后后者取得对于前者的优胜地位。在这个阶段,欧亚大陆上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迎来了最后的黄昏。先前欧洲殖民者登陆美洲,击溃了盛极一时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并带来了致命的病毒,造成美洲土著人口锐减,也使得美洲许多地区高水平发展的农地彻底变成了荒地,重新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书作者指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量开采贵重金属,白银因此大量流入亚欧大陆,这在很大程度上再造了明代和清代中国的经济;还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摆脱了之前的城邦国家林立的状态,这也增强了国家实力,让重商主义政策推行变得可能。而从美洲流出的许多农作物,也起到了养活更多人口的作用。为了确保美洲开发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者用诱拐在内的各种方式,将大量非洲奴隶贩卖到美洲。
工业革命打破了旧经济及其依赖的旧生物体制。英国因此才得以生产出比印度棉布更便宜的棉纺织品,在那之后,英国才开始推崇自由贸易,并试图用武力来对付拒绝接受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国家,如中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如此显著,以至于英国等国家的发展水平,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大大超越了过去的世界一流国家中国和印度。书作者指出,清代中国在1800年前后已经实现了农业的很高生产率,政府也积极利用市场进行农产品调度和销售,棉纺、蚕丝、甘蔗等产业的生产也实现了专门化,并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来避免出现饥荒。但清代中国未能有意识的发展突破旧生物体制的技术,因而发展水平无法突破生态极限。书作者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将丘陵、山地、沙地等边缘地区开发殆尽。当然,工业化进程对于环境、资源的消耗,深度上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旧经济。
书作者指出,1750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制造品的大约33%,印度和欧洲各占23%;但经过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印度相比欧美世界的发展水平迅速下跌,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下降到了7%,而印度只有2%。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原有的旧经济体系被打破,中印两国在半殖民化、殖民化背景下丧失了经济主权,成为欧美世界工业品甚至毒品的倾销地。另一方面,中印两国这期间人口增长迅猛,使得国家发展的负担更为沉重。
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与旧经济解体,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后者的环境代价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低,而前者虽然造成了工业污染,但如果从全球总的背景来看,初期的工业化对于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和后果却没有那么明显。工业污染成为全球性的命题,是到了20世纪,当欧美世界之外的全球其他地区也进入了工业化进程,而美国制造业在机械时代、流水线时代的生产效能得以暴增,才使得工业污染的绝对总量达到了一个令地球不堪重负的地步。
二战后,消费主义、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更快发展,也使得环境和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任何形式的‘经济’都来源于大自然的转化。采矿业、制造业以及农业都是把大自然所赋予的一部分资源改变成人类可以使用或消耗的物质的过程。”全球生态的危机在20世纪后期逐渐显露,与之同时,因为大航海时代以来造成的全球各地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很低,民众还没有实现基本的温饱,这让解决发展问题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