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杀的日本无赖派文学开创者太宰治(1909-1948)
日本文学有两个著名的无赖,一个叫太宰治,一个叫西村贤太。他们都热衷写“私小说”——就是印成书的Blog。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讲述的是一个乡下富家子弟大庭叶藏的堕落,辍学、酗酒、嫖娼、染毒,尝试自杀,最终不知下落。这是“日本文学无赖派”的开山之作。在太宰治自杀63年后,东京人西村贤太推出了《苦役列车》,描写的是一个无力抵抗下坠命运的屌丝贯多,由于父亲犯了强奸罪,年幼的他不得不跟着母亲远走他乡。高中失学后,他不得不当装卸工,从事只能维持最基本生存的重体力劳动,他渴望友情和爱,但缺乏建立它们所需的社交能力——当他企图和一同打工的大学生日下部当兄弟时,他的粗鄙最终令对方忍无可忍。他看清了现实:他和日下部这样的正常的同龄人活在两个世界,遭遇了深深的挫败。贯多后来拿起笔,疯狂写作,这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小说在贯多苦苦等待获奖电话中结束。“可是电话直到半夜也没有响。”但西村的电话响了,《苦役列车》获得了芥川奖,这几乎成为日本当代文学的一段佳话。
新闻报道:西村没有手机,获奖当天编辑给了他一只,为了不让他错过可能的喜讯——更为了让他的获奖更加戏剧化。他和朝吹真理子分享了2010年第144届芥川龙之介奖,当皮糙肉厚的他和白富美朝吹真理子一起站上领奖台时,估计评委都笑出声来。评委将票投给他时恐怕还带着些小邪恶:还是给他吧,他都这样摇尾乞怜了!西村和太宰治都盼望着芥川奖,太宰治的第三次自杀就是因为短篇《逆行》没有拿到芥川奖。
无论文学姿态有多另类,到了评委面前都要矮三分。芥川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文坛新人,西村拿到这个奖时已经43岁。
二
苦役列车 2011年芥川文学奖
太宰治被誉为战后日本文学三大巨擎(川端、三岛)之一,但高大上的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由纪夫很不屑与他为伍,认为太宰治不仅娘炮还喜欢玩自杀殉情的行为艺术。旅日文艺评论家李长声认为,太宰治写出了“皮袍下的小”,这正是他的强大之处。但面临战后重建的日本无暇欣赏负能量满满的太宰治,终于,在《人间失格》最后一章即将发表时,太宰治抱着文学女青年投河而死。这是太宰治第五次自杀。太宰治出生在日本本州岛最北端的青森县,虽家境富裕,却仍被三岛由纪夫嘲笑:“作品背后闪现的文坛意识以及乡下孩子负笈进京的野心似的东西是我最受不了的。”
西村贤太跟太宰治相反,西村1967年生于东京都,出身低微,太宰治的美酒和爱情他都没有享受过。他笔下的贯多也是如此,每天挣扎于要不要起床去上工,懒惰、自私又粗鄙,对人生这辆“苦役列车”充满无从发泄的怨恨。“他握着那根因晨勃而变得硬邦邦的'棍子',找到合适的角度,挺着腰,放出大量的尿液。”贯多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再往下你以为会是一本官能小说,你可能会失望,西村很克制,写出了一个卑微到尘土里的失学青年:货场里难以下咽的午餐、向房东下跪以求迟交房租,每天计算着兜里的钱够不够买酒、去下等风俗店解决性欲问题……《苦役列车》的成功在于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天生的loser。我在日本游玩期间,看到社区贴出的寻人启事,失踪人口大多数是10-15岁的少年,这是对即将进入的成人社会的恐惧吧,掉队的孩子默默地逃离了。痞子文学恐怕就来自这些从户籍上消失的年轻人。在高度工业化的、黑道也很规矩的日本社会,这些年轻人去哪里混呢?
三
文学中年西村贤太
日本大概没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整个社会给“异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很小,反抗社会主流价值观代价极大。中国人改朝换代看的多了,人生观的range相当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方法论。这方面日本社会似乎完全未开化,单一的价值观令日本国民活得很紧张,时时刻刻都要自省,寻找自己的位置,以求“不失礼”。
日本式的集体主义直接脱胎于原始部落的军事纪律,陈舜臣先生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中提到,当年倭寇扰华时摆出的蝴蝶阵,“战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挥扇,则伏兵四起。”没有高度服从,怎能在客场以寡敌众?陈先生写道:“扇子向右边挥,就不能往左边跳。违反的人不仅自己性命堪忧,而且也会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安危。”无赖和痞子们不听管束,不对自己负责,不在乎给别人制造麻烦,在日本这等于给自己判了社交上的死刑。
《人间失格》里的大庭叶藏玩颓废玩得很彻底,敏感脆弱又沉迷于享乐,让亲友逐一离他而去。《苦役列车》的贯多则更多是身不由己跌入深坑,幻想能够跳下这辆苦逼的列车,换乘新干线,他无力在黑暗的坑底去开创一个自己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村没有达到太宰治的精神高度,这让他有继续苟活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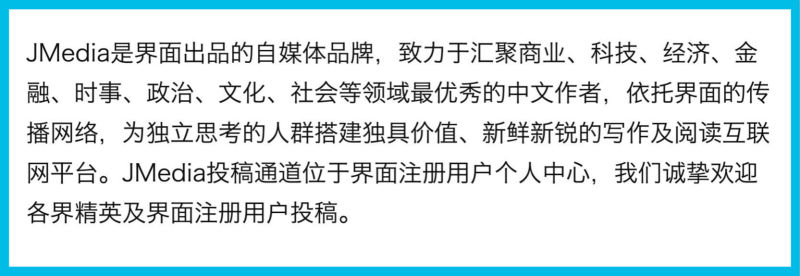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