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在美国度过。来到一个新的社区,这里有一个“华人传统俱乐部”(Chinese Heritage Club),每到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和中秋,都要举行盛大的聚会庆祝活动。这里不是“唐人街”、“中国城”,而算是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尚”社区之一,华人家庭及人口在这个社区中听说有近3%左右,已经是高于华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他们大都是已经退休的技术和专业人士,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教师、职员和商人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均是来美国已经数十载。
“庆祝中国春节晚会”在社区中心的大礼堂席开几十桌,自然也有不少“老美”前来来助兴。灯笼、红绸、对联、旗袍、唐装,大家见面拱手拜年,喜庆“羊羊”,好不热闹!唱中国歌、美国歌、跳中国舞、美国舞,名称为Time Wave的乐队也是华人和美国人共同组成,学中文的美国人和华人一起合唱中国歌曲,场面活泼动人。席间的节目全部由社区及俱乐部的成员自编自演自唱。浓浓的中国味、深深的乡愁情,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欢聚总是如此传统和温馨!
多年来到访过美国多个城市和多个社区,参加过各种华人社团或者朋友圈、中国使领馆、还有美国人办的庆祝中国春节的聚会活动,有如此档次和品味的联欢活动且还是自己一个社区的华人搞的,并不多见。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凝聚华人甚至喜欢中国文化的“老美”,这样的社区名副其实“和谐社会”,可喜可贺。
同桌的老大哥、老大姐都是来自台湾的“外省人”,听说我来自北京,顿时发现今儿个一桌是“老乡见老乡”,虽说没有“两眼泪汪汪”,也有一见如故之感。其中有一对姐妹的老大姐,告诉我说,她们家当年住在东城的南池子,现在还记得儿时北京的风沙,还记得骑自行车出门车胎陷进了有轨电车的轨道内那个着急和尴尬。如今白发苍苍,但乡音不改,还是一个“老北京人”。不过,说说就不免感伤和遗憾,老大姐说,“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在台湾我们又是‘外省人’,如今我们是无家可归,落叶也归不了根啊!”
春节是思乡的日子!怎么感慨都不过份。……
席终人散,回味无穷。会后当晚,新结识的朋友发来一个用powerpoint制作的《最后一代的内地人》,图文并茂,读后不免思绪万千,特把原文的繁体字忠实地抄录如下:
數年前,專欄作家信懷南在「世界周刊」的一篇文章《最後一代的內地人》,催生了一個新「族群」:「最後一代內地人」。
作者在文中處處流露著無處歸屬的感嘆與無可奈何的哀傷,「最後一代內地人」,是特殊歷史之下的產物。「最後一代內地人」這一新的族群,他們的人生軌跡是: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念大學、留美深造並在美生活數十年。假如您不是「感同身受」,那就抽幾分鐘時間認識一下這個「族群」吧! 最後一代的NDR,指的是我們這批1937到1950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長大,長住美國的「內地人」(Nei Di Ren)。
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50年後,當後世的中國人回頭研究這一段歷史,他們會發現我們這些「內地人」,是卡在東西文化的夾縫裡,遊走於外來與本土間,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對中華文化抱殘守缺,對西方文明汲汲經營,非常特別的一代。逐漸地我們這代都會隨風而逝。
我們那一代生於戰亂,早生的遇到抗日,晚生的遇到內戰,很多生在四川,所以名為「渝生」、「蓉生」、「嘉陵」的很普遍。
我們雖然生於戰亂,但卻因年齡太小而對逃難沒什麽印象。我們跟著父母到了台灣,變成「內地人」,那不是我們的選擇,但回頭來看,這可能是我們命運中的一個break。
如果我們沒去成台灣,我想我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活不到今天。就算活到今天,我們子女的一生絕對會完全不同。基本上,我們是虎口餘生非常幸運的一群。
我們的童年是在台灣過的:有的在北部的城市,有的在南部的田間。穿過木屐,打過赤腳,玩過官兵抓強盜,睡過榻榻米。雖然物質的享受很貧乏,但我們沒有餓過肚子。
我們這一代,很多是在眷村長大的,有人怪我們住在台灣那麽久還不會說台灣話,不夠本土。我們不會說台灣話不是我們的錯,那時候的政治大環境,在學校不准講,回家不會講,這筆帳沒理由算在我們頭上的。
我們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會讀書的一代。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留學,一路考下來,過五關、斬六將,個個身經百戰,久「烤」成精。大學畢業後,我們大多都選擇出國留學的這條路,學理工的特別多,有幾個理由:
1、受到當年楊振寧,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的鼓舞,家庭,學校,社會都鼓勵我們「理工報國」,在科技上光宗耀祖。
2、家長們大多對政治沒興趣,對法律,醫科不瞭解。大多不推崇這些科系。
3、留在美國找事容易。
但當年看起來很正確的選擇卻埋下了後半輩子在美國沒安全感的種子。
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美國非吾土,台灣憶舊逰。
在台灣,他們早些時候叫我們「內地人」,後來又叫我們「外省人」。
到了中國大陸,他們稱呼我們為「台灣人」,在美國我們是第一代移民。
中國人的子女,美國人的父母,我們的一生,不管住在那裡,始終還是過客而非歸人。
在政治認同上,我們對台灣早年「白色恐怖」沒好感,因而對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不能認同。
我們愛台灣也愛中國大陸,但我們不是新台灣人,而是身上有中華民族血液的美籍中國人。
大多也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持支援的態度,對90年代以後台灣的紛亂憂心忡忡。
40歲以前,我們多半是「有心腸」的自由主義者。
40歲以後,我們多半變成了把票投給美國民主黨但思想行爲追隨共和黨的「有頭腦」者。
我們這一代有一些人在「保釣運動」中熱情過,但大多數對政治運動選擇旁觀者的冷漠。
在我們的一生中,曾經目睹三個極爲荒唐的政治鬧劇:
毛澤東和其信徒搞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幾乎革掉了中國的命:
李登輝一個沒有誠信又搞黑金的政客,又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居然把自己的黨搞垮;
民進黨的陳水扁,滿嘴謊話,作盡了貪污腐敗和禍國殃民的事,竟然還賴在位子上想把台灣徹底弄垮爲止。
也難怪我們這代,大多數的人對政治人物不信任。
和我們這輩的女孩子們,年輕的時候多半穿過「蓬蓬裙」,跳過「吉路巴」,聽過「康妮弗蘭西斯」,迷過「詹姆斯•迪恩」。在計程車還沒出現的時候,約會路近靠走,路長坐三輪車。那時台北市新生南路路旁的大水溝還沒蓋上。我常想,現代的年輕人,把男女感情的境界看得太開放,太直接。
有回在台北和一家有名的文學雜誌的同仁吃春酒。談到男女感情的境界,我引的是元積「取次花叢懶迴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在座有一位有名的詩人兼帥哥不以為然。
他說:「對我來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玩笑。一般講起來,我們這代也是最後一代的「純情派」,是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
我們對上要生養死葬我們的父母,對下會把最好的給子女。當我們老了的時候,我們不會將負擔加諸在子女的身上,我們是最後一代的「三明治」。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孩對中國文化多一些瞭解和認同,但12年中文學校下來,能認得「王大中」、「李小明」就不錯了。我們可能是13億中國人中,中英文都還可以的一代。希望不是最後一代。
我們生的太晚,錯過了北伐、抗日、內戰、成大功、立大業轟轟烈烈的時代。
但我們也生得太早,台灣經濟起飛的成果沒我們的份。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保留了一些中國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美德。
我們不是中國人中最偉大的一代,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內地人」。
阅后,同为中华儿女,怎能不感慨伤愁。我当即给这些新认识的朋友们做了如下email回复:
看完《最后一代的内地人》,让我一个从北京来的新的“内地人”的思绪油然而生,颇有感慨。此作品充满了浓浓乡愁、丝丝悲哀,触景生情。炎黄子孙有太多的悲剧和灾难,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和遗憾。
历史诚然已为历史,过去的事情显然是无法改变,但未来却是可以创造的。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其固有 的resilience注定了中华民族是要复兴的,现在已经让人看到了曙光,尽管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且必定坎坷。
“外省人”、“内地人”、“台湾人”、“大陆人”,这里人,那里人,都是中国人,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的肤色和基因是不会改变的,血浓于水。有一点可以相信,台湾的命运和大陆的命运终将由13亿人民来决定,加上千千万万在海外的华人。想着这一点,大家的浪迹生涯或许就会“淡定”许多。
不知道这部伤感powerpoint作品的笔者是谁,如今何在。今天愿借其文中的繁体字“五言”诗续之简体字“五言”句:
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美國非吾土,台灣憶舊逰。
落叶归不根,不必图伤悲,中华已觉醒,未来更朝晖。
2015-02-23羊年写于瀚海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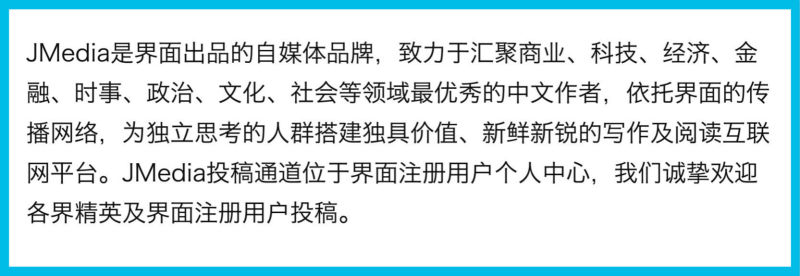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