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镜子总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后视镜、反光镜使得我们拓展视野
化妆镜、穿衣镜帮助我们审慎自我
当电影遇到镜子同样可以在
技术层面和叙事层面
发挥奇妙的作用

今天我们就一同去发掘
当电影和镜子相遇 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
▼
场面调度 元素并置
好电影的开头尤为重要,必须简洁而有效地交代清时代背景,介绍人物出场。
在《甜蜜蜜》中黎小军初次造访姑妈家,场景设置是典型的香港蜗居式住宅,局促且逼仄。
在镜头无法拉开的情况下,导演在黎小军面前立了一面镜子,通过镜面反射,将黎小军、姑妈和梳妆台周围的照片并置。

不仅清晰地交代出黎小军和姑妈的人物关系,又为后来揭示姑妈与照片中人的恋情埋下伏笔。
黎小军来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梳妆台前见证了一段悠长、刻骨的暗恋,正是对他后来与李翘难解难分的恋情进行了预告。


而这一切重要元素的并置,都要归功于这面镜子在这里起到的作用。
同时,利用镜面反射进行场面调度也是许多港片受制于狭小建筑空间而惯用的调度手法。

《甜蜜蜜》中另一处经典的镜面运用出现在李翘和黎小军在街头请邓丽君签名的戏上。
镜头模拟李翘的主观视点注视着车前的黎小军,衣服上的“邓丽君”三个字不断提示她这是二人之间隐秘的爱情符号。
这时镜头反打,对准了后视镜中李翘的脸。


影片发展到此刻我们不难看出黎小军依然对李翘抱有恋爱的幻想,而李翘才是这段感情中相对不稳定,始终回避问题的那一个。
利用镜面反光,陈可辛有意识地把两个人物都以正面展示给观众,一方面有效地传达了那一刻人物电光火石的激动内心,又在实景中点明了李翘对黎小军也依旧怀有情愫。
这一刻本来把感情掩藏起来的两个人,终于袒露心声,直面了彼此。

利用镜面反射把两个人物正面并置起到的效果,要远好于背影交叠所能携带的情感力量。
像这样利用镜面进行场面调度的做法,就是镜子这个元素在电影技术层面上的运用。
虚实交叠 内心一致
在镜面运用上《第三度嫌疑人》可以说是有创新之举的。
影片反复呈现了律师与犯人的会面,每次对话拍摄的方法都不一样,非常具有设计感。
其中有一个细节是,随着二人间相互认同感加深,审讯室的玻璃上开始逐步投射出犯人或者律师的虚影。
在昏暗的场景灯光下,透明玻璃也起到了和镜面相似的作用,能够在同一画面上同时呈现两个朝向不一样的人的面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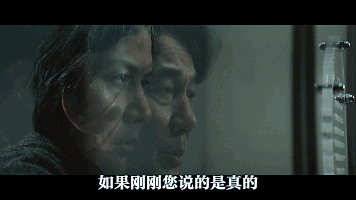
这一特征在最后一场审讯室的中戏到极致,犯人的面部虚影直接交叠在律师脸上。
此刻两人无论是对于父女关系的心结也好,对生死的看法也罢都在精神上已经达到了统一,因此画面中的两人面朝向同一个,好似朝一处使力。
但是仔细看,我们又能发现犯人的虚影总是更靠前,而实景中的律师始终在试图向虚影靠近,又凸显出两人一主一从的关系。
律师是受到了犯人精神信念的引导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同时犯人也已经欣然接受死刑的命运,他的虚影仿若一个幽灵留在了幽暗空间,而律师的实体带着对案件的反思渐渐隐去。
这个长达两分钟的固定镜头就是靠着玻璃,或者说镜子制造的虚影效果,用画面语言表达出了丰富的内涵。
自我审慎 关键转折
在另一些场景下,镜子作为道具可以为摄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点,镜子甚至可以不用真正地出场,而是用摄镜头模拟镜面,让主人公直视镜头来达到照镜子的效果。
在《我,花样女王》当中就有这样一组镜头,观众一步步见证Tonya在奥运赛前化妆的过程,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她几乎要被压力碾碎,又不得不强装振作的人物状态。

拍摄时演员其实是对着摄影机化妆,并看不到自己的面部,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
而通过“镜子”这个媒介,剧中人得以长时间地凝视自我,和真实的自我进行交流与相处,也在剧作上为后续人物发展的转折变化进行引导。

类似的处理还有像《丹麦女孩》中艾纳在镜子前专注地打量自己的身体,通过一番自我审慎,他终于确立了内心对于变成女子的渴望。
这场通过凝视镜中真实自我的戏,正是艾纳实现转变的关键。


这里的镜子起到了叙事层面上的递进作用,而《丹麦女孩》与《我,花样女王》在这一点上的区别仅在于后者不仅有叙事表达,还利用镜面提供了视点上的辅助,将技术和叙事两个层面结合在同一个镜头当中。
我们不能说哪部影片的镜头更高明,只要是恰当、符合当下需要的镜头都是优秀的创意。
区隔空间 虚实界限
镜子也是惊悚片中的常客,经典如《闪灵》初次介绍丹尼出场,便使用了一个他在镜前的画面。

面庞天真可爱的丹尼与镜子中的自己进行着异常诡异的对话,此时镜子内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虚拟的,超时空世界,是超越理性的存在。
而这面镜子则是虚幻和现实间边界的实体。
另一部经典之作《黑天鹅》当中也大量运用了镜子的元素,妮娜初次显示出精神分裂端倪就被表现为实体空间内的妮娜和镜中的虚影妮娜动作不一致。

此后妮娜常常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虚影发生变异,可以说是妮娜意识到了自我精神世界的紊乱,而镜子中现实的就是妮娜的精神世界。
来到更衣室的重场戏,这次妮娜直接与镜中的黑天鹅接触,而镜子是始终盘踞画面左右的固定元素,正是因为镜子的存在,打开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的通道。

也不是说用镜子来区隔虚实是惊悚片的专利。
在《戈雅》这部人物传记片当中,中年戈雅在病中走入自己的想象,从一个实景进入虚幻空间,最后再通过一面镜子过渡到老年戈雅的现实生活,意为表现老年戈雅回忆往昔峥嵘,思绪从记忆中翩飞回现实。

这样的双重过渡最终落在镜子这个媒介上,因为它具备了实现主人公自我审慎的能力。
所以说对于一个元素在叙事层面及技术层面上的运用往往不是单层的,而是叠加式的,是优秀的导演对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
镜子是重要的电影道具
它一面拓展了画面中物理空间的广度
一面又打开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