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活周刊记者 唐骋华
从人组成社会的那一刻起,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称之为社交。因此可以说,人自古以来就身处于一张无形的社交网络中。但这张网从未曾像今天这般巨大而繁密。因为,它不再是比喻意义上的网,而是笼罩了我们生活的互联网。
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已然成为了随身携带物。就是说,社交成了随时随地都能进行的事,且无分线上与线下。
一种新形态的社交就在这新风俗中迅速成型。它首先拉长了社交链,使我们的“社交最远点”近乎无穷。其次它延展了社交宽度,化传统的非社交为社交。最重要的是,由于网络的存在,传统的二维社交成了三维社交。这个春节,你感受到了新社交的魅力了吗?当全家人捧着手机抢红包的时候。

手心上的虚拟城市
香港或许是科幻片、谍战片最偏爱的取景点之一。港剧自不待言,我们也经常在好莱坞大片里看到中环魅影。另一个地方是纽约,外星人总是于此落脚。近些年,上海也日益受到青睐,陆家嘴、外滩等相继在《007》《变形金刚》《黑暗骑士》《第九区》露脸。
这三座城市的共同点是,充满了神秘感和未来感。这恰恰是科幻片、谍战片需要的布景。
那么,这布景由哪些元素构成呢?高耸的现代建筑、多面的玻璃幕墙、成片的住宅区、琳琅的商业符号,以及穿梭其间的车流人流。功能上,它们各有分工,空间上却不得不紧挨乃至于交错——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就是住宅区,而商业符号无远弗届地瓜分了城市的半空。
这是城市的特性决定的。巴里•谢尔顿等人在《香港造城记》中说,城市将“商业、工业、市场、学校和娱乐区域全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高密度的生活状态”。
高密度生活一方面造成拥挤,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硬币的反面,则是巨大的包容性和便利性。在城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和节奏过日子,想购买什么都很方便。你还能结识各色人等,无穷地延伸交际半径。
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比手机更契合城市性格的物件了。毋宁说,手机是高度浓缩的城市,一座攥在你我手心的虚拟城市。
网络是这座城市的街道。它有发达的线,带我们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线组成面,是人们的活动范围。由于虚拟的街道可无限延展,因此理论上,我们的活动范围也无限宽广。
虚拟街道上散布着APP,可以将它们理解成虚拟建筑。其本质则为替代品。具体说,网店替代了商铺,视频网站替代了电影院、MP3,公开课替代了学校,支付宝替代了银行柜台。微博是众声喧哗的广场,QQ群是或沉默或欢畅的老友记,微信则接近熟人社区。
总之,从实体经济到人际关系,凡是能虚拟化的尽皆虚拟化。而这些统统被集纳到一部手机里。
2010年7月我在《手持终端新大陆》中写道:“谁离开了手机,谁就离开了社会。但这玩意还能叫手机吗?或许可以这么问:手机能做什么?答:它什么都能做。”五年间,手持终端突飞猛进。这一天已悄然降临。

屏社交,泛社交
在实体城市,我们从一个点(家)移动到另一个点(公司),依靠双脚和交通工具。而在虚拟城市,拇指就是交通工具。拇指轻轻划动、敲击,我们就能从商铺瞬移至电影院。
于是有人提出了“屏社交”。屏,指电脑屏、手机屏及可穿戴设备的屏。概念提出者、专栏作家陶舜认为,通过屏,从购物到交流,人们的大部分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质言之,这实际上是拇指在各种屏上划来点去的过程。一切归于屏,一切又从屏出发。
为什么要强调社交呢?这是虚拟城市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实体城市,你也购物、吃饭、看电影,这主要是个人行为。充其量,你与有限的几位亲朋交流心得。而到虚拟城市,你给淘宝卖家评价、美食网站上晒图都将影响陌生人。理论上,你是在向所有人分享。
这意味着“社交”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你在屏上的任何言行,都可能被定义为社交。或许,称此为“泛社交”更妥帖。它有别于目的性较强的传统社交。
关键是网络。最初我们用猫(Modem)跻身虚拟世界。然而,56K的龟速加上昂贵费用,严重制约了社交时长和质量。那只能算泛社交初级阶段。宽带出现,泛社交进阶。宽带费是固定的,因此,上网时间越长单位成本越低。仔细观察,“网瘾”讨论得最热烈的2009年前后,正是宽带普及之际。据次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网瘾”青少年达2400万。
有线网络的短板在于,无法在移动时使用它。没了那根线,我们也就和泛社交隔离。
无线网络使社交摆脱了物理空间,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至此,真正意义上的泛社交产生了。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网购、抢票、秒杀,也随时能刷微博、微信,登录QQ群。新近受到瞩目的是微信红包。
从前,红包是少数人之间的游戏,且主要由长辈包给晚辈、老板包给员工。其暗含着的身份意识,限制了此类社交行为的延展。微信红包却一夜间改风易俗。同学、同事、同辈甚至陌生人都能互发红包。除夕夜,全家人一起摇手机抢红包则成为守岁新景观。据统计,从除夕到年初五,全国人民收发的微信红包高达32.7亿元。
微信红包正是典型泛社交。它也凸显了泛社交的特点——打破传统社交的藩篱,使社交跨越年龄、阶层、财富、性情等而融汇贯通,形成泛社交的“全民狂欢”征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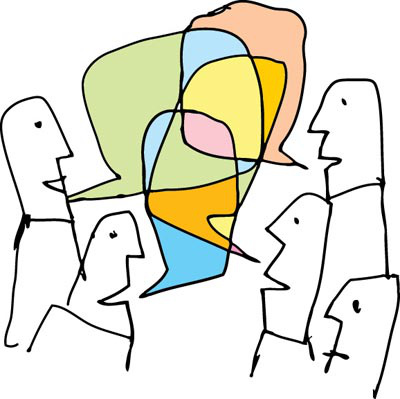
分享型人格,过剩型社交
一个典型泛社交狂热者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如同上班要打卡,他每天睡前和醒来必发早安与晚安。刷微博、刷朋友圈是工作,无论坐地铁抑或乘高铁。追剧、看电影、读书、吃到美味要及时地评分、发观感。连跑步,也有APP画好了路线图供你晒图。
对这幅图景,原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在新书《移动时代生存》中有更细致的描绘:“以前看到有趣的事,记在心里,见到朋友时讲述给大家听;现在看到有趣的事,立即拍下照片,发微信与朋友们一起分享。”由此形成了“分享型人格”。泛社交狂希望自己的一切都被人看到,他也要看别人的举动,并点评和点赞。
问题在于,我们真的那么需要分享吗?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社交半径合理,我们分配给每单位长度的精力就会多些,质量也相对能得到保障。泛社交使社交半径无限延长,并且,将几乎所有言行都社交化。但同时,社交品质被极度稀释。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今电子邮件飞快,微信比飞快还快,爱不断膨胀,浓度急剧下降。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已经迈入了社交过剩的时代——当生活各层面都充斥着社交的时候,它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与此相应,我们的社交能力在退化。
这似乎十分矛盾。明明泛社交化了,社交无处不在,社交能力怎么会退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泛社交前所未有地分散了人类的注意力,让任何有目的的行动都可能节外生枝。例如,打开电子地图原本是查询路线的,可每每,我们忍不住会“顺便”查看商户信息、团购活动。换言之,我们攫取直接信息的能力减弱了。
因此,过剩型社交导致了大量无效的社交行为。而无效社交正挤占时间。难道不是吗,24小时里我们将多少精力扔在了社交上?
实际上,多数人的分享并不具备分享的必然性。它真正的作用是,使人们处于“分享/被分享”的场域中,制造出一种“需要/被需要”的幻觉。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泛社交,那意思是,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人群的包围。即便只是想象中的人群。难怪“独处”成了一件需要练习的事。这就是这座虚拟城市之于现代人的作用。
本文刊载于《生活周刊》1564期,转载请联系,并注明“来自生活周刊,微信号lifeweekly1925”。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