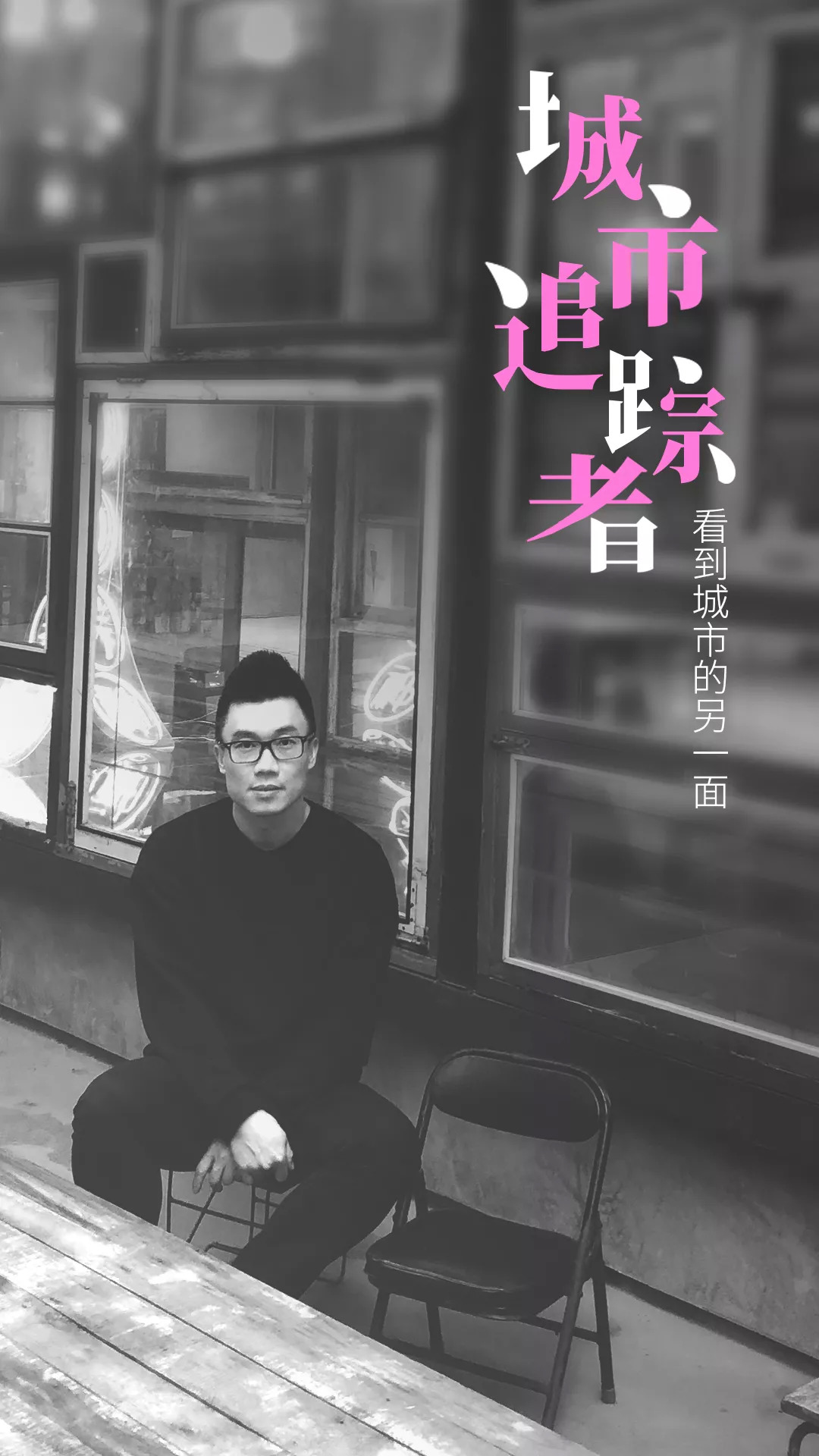
故 事
/
Vol. 446
城市追踪者何志森的故事。
何志森有一个“猥琐”的爱好,就是跟踪。
从人到动物,从物体到气味,有形到无形,无所不跟。
在上海的弄堂里,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80%的人打招呼时手里都拿着尿壶;
在广州的火车站,他跟踪小偷,试图透过小偷的眼里理解城市的空间;
在香港,他跟踪警察,试图理解警察眼里的城市地图是怎样的;
他跟踪卖冰糖葫芦的阿姨,为阿姨设计了三条躲避城管的逃跑路线;
他还在城中村和平民窟跟踪流浪汉、城管、盲人、小贩、站街女,甚至跑到湿地公园观察蜗牛,并为蜗牛设计逃生路线。
他呼吁设计师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需求,从而为阅读和理解城市和空间提供另一种可能,也为设计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
但是他极少去跟踪有钱的人,因为他觉得,有钱(权)限制了想象力。
——跟踪者说

何志森火了
在中国,极少有一个城市设计师会持续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何志森是第一个。
事件最初的起因,是在2018年3月,何志森受邀在演讲节目“一席”上做了一个题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的演讲,观点新奇有趣,行为离经叛道,不光在设计圈炸起一圈大浪,还触动了数十万网友兴奋的神经,视频短短时间内就突破了400万的播放量。
戳视频
▲何志森在一席的演讲视频
何志森火了。
“城市跟踪者”、“网红教师”、“侦探设计师”……各类标签接踵而至;
“伪情怀”、“反精英主义”、“作秀”……种种质疑裹挟而来;
在各种网络平台搜索“何志森”,都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他的报道,但何志森平时工作实在太忙,我的采访从2018年5月开始,前后五次不断推迟延后,直到11月底,才终于在广州扉美术馆见到了何志森。
何志森现在的主要身份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兼任教授,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扉美术馆策展人,同时在国内外不同学校上课,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墨尔本大学、台湾淡江大学……等等。同时,他也是一名城市设计师,通过Mapping工作坊的形式,参与了不少城市设计项目。
早在2003年,何志森就离开中国,到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念建筑。2014年博士毕业后,导师推荐他去美国一所长青藤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何志森有些心动,但当时他的第一个Mapping工作坊“城市侦探”(在华南理工大学)是他非常想做的,所以就放弃了那个职位。工作坊启动后,一直在国内外的不同城市持续进行,何志森也开始了他历时4年的“游牧式的教学实践”。

▲研究生毕业时候的何志森
他不光跟踪小偷,还跑去跟踪警察
每一个跟踪观察项目时间都不一样,短则一两日,长一点的需要两周或者一个月。
何志森说:“我希望能带着大家去认识真实的生活世界。”
▌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
何志森带着学生去到城中村、贫民窟、去到社区、去到街道、菜市场,观察真实生活里的人群行走的轨迹、生活的需求。在他看来,设计师只有真正地走出象牙塔,去理解生活,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现在大家每天都在加班、熬夜、做项目、不停画图,没有时间看电影,没有时间旅行,甚至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又如何知道美好的生活是怎样的?设计师本身的目的是在为老百姓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但如果每天都坐在电脑前面画图,加班熬夜,是设计不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品来的。
▌那哪一种才算是有创造力的建筑呢?
何志森说,就好比番禺紫泥堂的纤维板厂改造项目。设计时,建筑师把建筑的外缘部分设计成了很多展示日常生活和家庭交流的“小展厅”,让建筑的中心转移到了外缘,让建筑的外缘变成了一个上下左右邻居交流的场所,实践日常活动的舞台,一个相遇、工作和创造的中心,形成加厚的边界。让平凡的日常生活像美术馆的展品一样呈现出来,而不是一个只有单一可能性且封闭绝缘的盒子。
在另外一个蓝天商场项目里,也是利用了mapping的方法,通过对那里居民长时间的跟踪观察,记录他们每天是如何移动的,了解那里居民的实质需求,最终在商场设计时,在中间让出了一个公共通道,让居民既能够从那里穿过,同时又能经过商场,变成一条社区的街道。

所以何志森的所有看似无厘头的跟踪观察,正是基于这个最终目的。
通过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城市和空间,才能做出不一样的设计,如果仅以设计师本身的视角,或领导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做设计,那样的建筑只能是一个冰冷的外壳,与人的生活方式和周边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一次,何志森在火车站偶然发现一个小偷在偷手机,他没有制止,而是悄悄地跟在后面,观察小偷的路线,研究小偷在火车站是如何移动的,他把自己置换到小偷的角度,去思考小偷眼里看到的空间和行走的路线有何不同。后来何志森发现,小偷作案前会了解这个地方的摄像头的分布地点,保安的巡逻时间,而且小偷的逃跑路线也事先做过调研,一旦被发现了应该怎么跑,跑到哪里,都有一个非常周密和在地的调研和规划。
设计师设计了火车站这个扁平而巨大的空间,但是小偷却根据设计师提供的条件重新去规划了这个空间,设计了自己不同的行走和逃跑路线,这是设计师没有想到的。何志森说,这是平凡人的日常设计,这是另外一种再设计,它还会有第二次设计,第三次设计……
跟踪完小偷之后,何志森开始好奇:如果小偷的路线是这样,那警察的行走路线又是什么样呢?
在2018年10月份,何志森来到香港,一连几天跟踪了不同的警察。他发现警察走的一些路径,一般不是地图上多看到的两点一线。警察不会按照规划师提供的路径去走,而是会不断拐动甚至穿过私家住宅、商店和屋顶,在实际使用中,城市规划又因为场所的使用者发生了不断的更改和调整。对于何志森来说,没有一副地图是永恒不变的。



▲警察的巡逻路线图
特别有意思的是,就在跟踪警察的时候,何志森几次遇到了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年人,于是他放弃了既定计划,没有继续跟在警察后面,转而开始跟踪起了这个老头。他发现这个老头是想去一个社区公园,原本可以从A点直接走到B点,但是他非要走一个弯弯曲曲的路线,至少比直线路程远了两倍不止。经过仔细观察,何志森才发现,原来在老头走的这条路上,每隔不远就放置着一根凳子,所以老人家每隔四五分钟都要坐一下,休息五分钟,再继续往目的地走。如果走直线路程,就没有凳子可以坐,所以这个老人是在发现和利用街道已有的设施在重新规划他的日常行走路线。这一点,规划师是没有想到的。所以何志森经常提到:城市既是设计师设计的,又是生活在那里的人营造的,这就是平民的智慧。



▲老人行走路线图
这些都是城市设计师不知道的,他们以为我只要给你一个公园就够了,但其实很多人都在重新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发现。在何志森看来,设计师要去理解场地生活在那里的人,如果这个公园的设计师能够早一点知道这位老人的需求,也许他在设计公园时会在不同的街道不同的位置为去公园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小小的“加油站”,而不是只专注在红线范围以内。对于何志森来说,设计最重要的是要跳出那个甲方给定的框框,跳出盒子,去设计建筑与周边各种各样的关系。
他被称为建筑界的“周星驰”
何志森说自己用粉色,是因为粉色代表柔软,他希望设计师的内心也能越来越柔软,但同时他也说,这是因为自己特别离经叛道,大家不喜欢的,他就非要喜欢。
当然,不管是在各种电视节目上,还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何志森,永远都是一身黑色,他说:“我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人格很分裂。”
何志森喜欢思考和质疑,他喜欢不断地提出问题推翻自己,并且享受这种过程,
身边的朋友都说何志森的出现,总是让周边的人感觉很压抑,虽然他偶尔也会搞笑一下,但是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何志森认为自己非常沉闷,但在做着非常有趣的事情,大概只有这两个方向不断走向最极端,才能维持到平衡。
周星驰的电影总是很搞笑,但是本人却很压抑,大概正因为这种相似度,所以网友才会说何志森是建筑界的“周星驰”吧。

很多人说,何志森在为底层民众代言。
何志森说:“我一直觉得我是精英”。
他认为自己接受很好的教育,没有必要去否认或掩饰自己是精英这个事实。虽然现在何志森在做着一件跟很多精英背道而驰的事情,就是走到平凡人的生活中,带领学回归日常,做着很草根的事情,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何志森自己也有点恍惑:“我在思考,我到底是草根还是精英?”
正是这个精英,在媒体争相报道之后,一下掉入了舆论的中心,在学霸扎推的知乎上,何志森成为不少设计师狂喷的对象;
对这一切,何志森很冷静,他说:“质疑我的人太多了,但我不是一个喜欢辩解的人,让大家去评论好了,教书本来就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老师不可能马上见到自己的教学成果,教学就像是在播种子,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会开花,可能永远也不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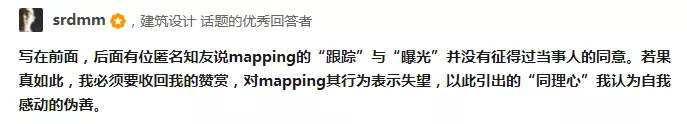
何志森被喷得最厉害一个观察项目,是他把病床给搬进了社区。这个举动遭到了居民的抵制、泼脏水。
@萨庄德:这个实验真是缺德,挑战人家的忍耐心;
@是橘:这个实验毫无意义,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不会坐吧,还在人家家门口摆,真的像诅咒一样;
@cynthia:搬病床放街道问你敢不敢坐,这和探测社区里住的病人的态度有什么联系,实验不严谨,丧失了它的意义;
对此,何志森回应说:“我只希望能激起一些涟漪和碰撞,引起人们的思考就够了。”
还有两个引起争议的观察项目,一个是他给广场上的小贩制定躲避城管的路线,另一个,是他帮助他母亲将社区花圃改造成了菜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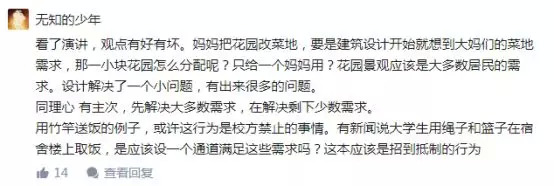
在何志森看来,他所做的这些观察,都是为了让设计师知道什么是“同理心”?
对于何志森来说,真正的同理心, 不是居高而下的怜悯,而是如果把命运对调的时候, 你的感受将会是如何? 其实花圃改造成菜园也是一样,何志森说这些都只是一个很小的引子,他只是想通过他生活中的小故事,告诉我们的设计师不要乱来,一定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使用者的日常需求,一定要以“他人”的视角去做设计,不能把设计变成一个自我感动的工作。
“我比较反感的,是很多人觉得老师一定要去做商业项目。上课不讲项目还能讲什么?你不觉得教书就是一种最在地的实践吗?如果你的理念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学生未来做的项目,这不就是老师最好的实践?”何志森说。

部分图片由何志森先生提供。
·········· END ··········
本期故事制作团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