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晶
编辑 | 罗立璇
设计 | 张鹏飞
“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一秒钟》作为电影艺术,可以促进我们思想和生活上的真正转变”,在柏林电影节的颁奖典礼台上,评审会主席朱莉娅·比诺什代表组委会缓缓读出给张艺谋的一封信,“这就是电影的能力。”
今年本应是中国电影人在柏林少有的兴高采烈的一年:除了《一秒钟》以外,王全安的《恐龙蛋》、王小帅《地久天长》入选主竞赛单元;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相梓的《再见,南屏晚钟》则入选全景单元。中国导演电影在四个单元共计12部作品入围,创下中国电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入围之最。这一年也被称为“柏林中国年”。
尽管由于某些因素失信于柏林,柏林依然慷慨地向中国电影人给予了足够热烈的认可:中国演员王景春和咏梅凭借《地久天长》包揽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相梓的《再见,南屏晚钟》则获得了泰迪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


脱胎于冷战时期的“西柏林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在东西德签订友好条约后,逐渐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的一座桥梁,扮演了更重要的文化角色。在那以后,柏林电影节一直要求自身对于本国以外的文化有着同样充沛的同理心和理解层次。这也是中国、罗马尼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的电影一直能够在柏林获得重视的重要原因。
找到自己的故事
回望过去,我们可以从柏林电影节中看到中国电影人如何一步一步找到自己想讲的故事。
从80年代开始,中国面孔就是柏林电影节的常客。第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影片是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燕归来》,讲述的是因“右派”身份划分导致一对恋人难成眷属的故事。
《血,总是热的》是第一部送到柏林电影节的罕见的“说人话”的电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是,“我们搞了三十年,不理想。万一再搞二十年还不理想,中国怎么办?没有退路了。”虽然当时的柏林电影节评委和观众依然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太重”,没有评奖,但在中国观众看来,弥足珍贵。
直到1988年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终于折服了。外国人从政治议题之外终于见到了另一个张扬而又野性的中国,绿油油的高粱地上“大”字躺下的九儿、跪在一旁黝黑又强壮的北方汉子余占鳌,生命原始的欲望与意志力打动了评委,最终让《红高粱》摘得金熊奖,成为首部荣获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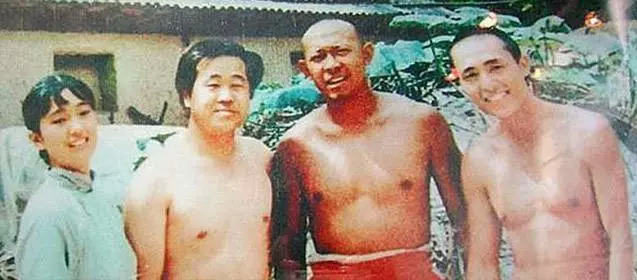
在这部作品中,张艺谋打破了外国人对于“中国农民”的习惯认知,让他们看到藏在那群无趣、庸常麻木的农民骨子深处的生命力。尽管他们依然受着愚昧的约束,但是在对性压抑和物质压抑的反抗中,他们冲破了禁锢。
当时巩俐还是中戏表演系二年级学生,姜文刚凭《芙蓉镇》崭露头角,张艺谋也是生平第一次做导演。1987年,张艺谋接到通知说《红高粱》将会被送选柏林电影节,然而那个时候电影声音和画面都还尚未合一,为了抓住去柏林电影节的机会,张艺谋在北京拼命加班,终于在12月26日赶出了第一个拷贝版本,12月27日是星期天,中影公司的同志加班办理报关手续,终于赶上了12月30日中国民航CA936航班,寄往西柏林。
但是当时收到成片的柏林电影节主席却十分生气,因为此前中方报选的单子上填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和王树忱的《选美记》,后来电影局决定选送这两部片子去戛纳电影节,临时决定改为推荐《红高粱》。
对于当时的柏林评选团来说,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高粱”是什么作物,因此对于《红高粱》这部影片并不抱多大希望。当时身在德国的爱国华侨李定一先生耐心地为评委会一字一句讲解,从片名到影片台词的含义都做了深入介绍,评委会才消除了对影片理解的隔阂,最终破例同意《红高粱》进入主竞赛单元。
《红高粱》后来被柏林的评委多次提及,在2010年柏林电影节60周年回顾展上,《红高粱》被再次播放。回顾展负责人、英国著名影评人和电影史专家戴维·汤姆森表示,让《红高粱》“回家看看”是因为“这是部非常棒的片子,当年它在柏林上演时效果好极了,就像忽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谈起《红高粱》重返柏林,张艺谋说:“我觉得像回家一样,电影让我们成了一家人。”
柏林对于姜文而言同样意义重大。虽然他当时已经凭借《芙蓉镇》名声大噪,但正是柏林电影节对《红高粱》的肯定让他开始走向国际。
1990年,姜文参演的另一部影片《本命年》同样也入选了柏林电影节。这部片子被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对中国影坛的最后一次大冲击,也是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

影片改编自小说《黑的雪》,但是拍摄当时并没有下雪,还是姜文想了个主意,提议改名为《本命年》,因为片中的主人公死在了自己的本命年里。巧合的是,片子在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那一年也是导演谢飞的本命年。
全片思索着一代人青春的生存与毁灭。姜文饰演的主人公李慧泉因为哥们义气打架入狱,出狱后一无所有,于是“下海”摆摊谋生活,为了追求爱情和义气,他最终倒在了血泊中,死于自己的本命年。在城市的灯光下,姜文摘掉眼镜眼泪滑落的镜头,让观众也陷入思考,到底是生活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生活,这一代人的孤独和迷茫,并没有随着主人公的生命戛然而止。
港台电影黄金时代
进入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港片在柏林电影节的评选中大放异彩。这一时代的港片形成的经典类型在柏林评选中都有体现,徐克的《黄飞鸿》、刘镇伟的《东成西就》、袁和平的《太极张三丰》都曾经入围过柏林的论坛单元。
在主竞赛单元中,评委们更加青睐的还是反映香港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许鞍华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在1995年的《女人四十》中,可以看出许鞍华对于当时香港生活的敏锐观察。

80年代以来,香港社会转型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产阶级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正在被中产阶级化的普通市民一时无法适应自己身份的更迭。电影将一位40岁的女人面临的生活琐事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中诠释了女性在人到中年时面临的压力。
在拍这部片子之前,许鞍华的两部片子《极道追踪》和《上海假期》双双遭遇票房惨败,尽管《上海假期》入选过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但许鞍华的电影生涯依然坠入了谷底。于是许鞍华远赴日本,蛰伏四年,后来就有了这部《女人四十》。此片一出包揽1995年台湾金马奖与1996年香港金像奖的多个奖项,主演萧芳芳也凭此片在继张曼玉后再夺柏林电影节影后。
柏林也是李安的伯乐。由于题材敏感,到处都筹措不到资金,李安在当时几乎付出了一切来拍摄《喜宴》,甚至把家中的锅碗瓢盆和餐桌都放到了片场。为了能够让《喜宴》获得国际声誉、在海外发行,《喜宴》的制片人徐立功和李安几乎天天都在餐馆和担任评委的张艺谋见面拉票。

最终,《喜宴》和《香魂女》两部影片票数相当,评委会决定同时授予两部影片最佳影片金熊奖。从此,李安在国际影坛一飞冲天,成为了华人导演的重要的国际声音。
更丰富的生活图景
从80年代华语电影对宏大叙事的逃离,到90年代展现改革背景下人们内心的迷茫与孤独,进入21世纪,华语电影更加关注社会分层背景下矛盾的撕裂与爆发。这一时期,以王小帅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作品开始受到国际电影评论的关注。
王小帅最早与柏林电影节结缘是从他的第一部独立作品《冬春的日子》开始。这部由王小帅自己筹钱,脱离电影发行体系的影片在1994年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上播放。在未入选之前,王小帅以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电影。

1989年王小帅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以后,他先后写了5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他发现再等待组织给他机会,他的电影就永远拍不成了。要像第五代导演那样用国家的资金拍片是非常渺茫的事情。要拍一部电影就成了王小帅和一批他这样的年轻导演们最为迫切的愿望。
王小帅不希望自己在等待中荒废了所学到的专业,找到了他原先在美院附中的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画家刘晓东、喻红夫妇,拍摄了全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的《冬春的日子》,后来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
这部电影展现了两位青年作家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的挣扎与突破,电影的演员是一对真实的恋人,他们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在多年的交往中程式化、单调的生活就是当时他们真实状态的反映。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席卷下,两人开始寻找生活的变量,但是最终,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却走向了疯狂。这部全片都是黑白色调的影片用接近冷峻的方式描述了这对青年画家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在遭遇生活创伤后的自我放逐。
2001年,王小帅凭借《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这部电影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两个底层青年的生命交织。一个是进城打工的农村男孩,因为单车被偷被打破了预想的规划,另一个则是贫寒的城里孩子,偷了家中的钱,买下了被偷的单车。

《十七岁的单车》由此用现实主义的所展现的青春,是残酷却又令人倍感真实的,在电影中单车所承载的已经不单单是车本身,它既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更代表着在梦想面前成长的隐痛。
这部电影在国内的放映并不顺利,一开始由于没有送审就参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导致被禁止在国内公映,2004年,该片重新送审后通过了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审查并允许公映,影片象征性地剪了8个镜头,名字改为《自行车》。
这也是广电总局电影局政策改革后首部解禁的地下电影。导演娄烨曾透露,该片被禁止公映原因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尽管作品在国内上映多次受挫,王小帅对于中国人的疼痛和迷茫的展现却打动了国外影评界。
在这次《地久天长》参评后,现场观众表示“这是一部令人心碎的长篇家庭杰作”,因为“审美、情感、故事都如此完整”。
两个家庭的三个孩子展现了中国30年社会大变迁的历史。故事不算复杂,却巧妙地将当年的计划生育、下海热、东北老工业基地、南方打工淘金等等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两个家庭的往事镶嵌进故事里,而这些历史事件,又反过来成为故事重要的推力。
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夫妻受到评委会一致好评。在颁奖礼后的官方晚宴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透露,最佳男女演员奖的评选几无悬念。评委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特意强调,“银幕上几乎没有另外一对夫妻,可以有如王景春与咏梅演绎得如此自然。”
另一位入围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导演王全安此前也曾在柏林电影节上多次获奖。他的首部参选作品《图雅的婚事》就斩获了第57届的金熊奖。出于对蒙古的特殊感情,王全安选择在距离自己母亲出生地300公里的地方拍摄了《图雅的婚事》。粗暴的工业开发导致草场严重沙漠化和政府强令当地蒙古牧民搬离牧区是拍摄《图雅的婚事》的最初动因,王全安想在牧区消失之前记录这一切。

图雅为了一家四口团聚,选择带着孩子和残疾的前夫为自己寻找丈夫,克制的情绪和自然平实的画面让柏林电影节的评委大为赏识。在57届柏林电影节评选现场,22部竞赛单元影片还没有播放完毕,组委会就已提前通知《图雅的婚事》主创人员留到闭幕式,电影节官方刊物《银幕》也对《图雅的婚事》打出了颁奖前的最高分2.33分。
此后王全安凭借另一部描述家庭伦理的影片《团圆》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曾说,自己一直在重复的东西就是生活的悖论。在《团圆》中展现出来的悖论则是家庭的团圆无法两全台湾老兵刘燕生与昔日爱人玉娥的聚首,却要以另一个大陆家庭的分离为代价。
一女二男的三角结构,在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中已有呈现,然而本片特殊的历史背景,却赋予故事一个可以承载政治隐喻和历史解读功能的舞台。王全安一面谨慎地避开了国共话语逻辑的正面交锋,一面在情节编排的细节处暗藏深意。片中有一场戏,家宴,三人畅谈对酒当歌,忆起国军败走台湾,台湾老兵眼中是“民国三十八年雷雨交加的一天”,大陆老兵纠正那是“1949年,艳阳高照”,而作为女性视角的玉娥只记得,去上海码头赴约,在万千离别人群中,遍寻不到自己的爱人。导演在历史真相与个体记忆面前,做了某种反讽和戏谑式的注脚。
在这部电影在柏林电影节的颁奖现场,曾经和王全安合作《图雅的婚事》的女演员余男作为评委团成员为王全安颁奖。余男在现场发言:“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分开,我们又会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从《红高粱》中野性又坚韧的中国农民,到《本命年》中迷茫痛苦的青年一代,再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结构中挣扎的中产与底层。中国电影人们在柏林电影节上相遇,也从柏林电影节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我们感谢柏林电影节,它拥有足够宽阔的舞台,不单止能容纳我们的欢愉、冲突与痛苦,也能让我们欣赏平静生活上偶尔溅起的层层涟漪。
来源:三声
原标题:柏林爱中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