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J.克拉曼(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著名宪法史学者专家)
法律在美国种族平等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很难界定。白纸黑字的法律与实际执行的法律时常毫无关联。
尽管法律禁止教奴隶读书写字,但还是有许多奴隶不是文盲。1850年代,黑人仍在继续进入一些州宪法禁止他们进入的州。种族通婚禁令也没能阻止跨种族夫妻的产生。

民权立法往往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1875年民权法案》在被最高法院取消前就已形同虚设,在它之后颁布的许多北方公共设施法令也不例外。
1875年,国会禁止在选择陪审员时带有种族歧视,但直到1910年,黑人也没能出现在南方陪审席上。尽管南方各州宪法规定,政府给黑人学校的拨款应当与同等白人学校的相同,但在1900年后,教育支出的种族差距已非常庞大,但这些歧视性行为几乎从未被告上法庭。
很多时候,立法不仅无力削弱白人至上主义,对它的存续也不是不可或缺的。北方各州并没有立法强制实行居住隔离,但北方黑人都普遍居住在隔离街区。
一战前,北方并没有种族歧视性的就业法律,但体面的工业工作几乎都不会录用黑人。绝大多数南方铁路公司都是在各州通过强制隔离法令前就开始对乘客进行种族隔离了。南方法规既没有要求黑人在公共人行道上给白人让路,也没有要求他们以尊称称呼白人,但若不这么做,他们就有可能遭遇危险。
吉姆·克劳法的制定往往是发挥象征作用,而非职能作用。1904年,肯塔基州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教育机构实行种族隔离,但当时该州只有一所学校是种族融合的,而且融合程度非常低。德克萨斯州出台法律禁止黑人参与党内初选,也只是为了镇压少数几个允许黑人参与初选的变节县。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法律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确立和瓦解都至关重要。1890年前后出台的选民登记规定剥夺了大量南方黑人及其支持者的选举权,便于白人对黑人选举权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没有法律强制,20世纪初时南方公用事业公司也不会在有轨电车上实施种族隔离。

《1964年民权法案》对废除南方学校及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至关重要,《1965年选举权法》彻底改变了南方腹地的黑人选民登记规定。
最高法院在推动种族平等上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很难界定。
19世纪时,最高法院一直是少数族裔的死敌。大法官们让一个北方州为保护自由黑人免遭奴隶捕手绑架的努力付之一炬,还废除了国会禁止在联邦领土上实行奴隶制的命令,否认自由黑人拥有任何“白人有义务尊重”的权利,释放了私刑绞死黑人及实施了种族屠杀的行凶者,废除了一项联邦公共施设法,维护了绝大多数由州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排华举措。
到20世纪,最高法院依然认定种族隔离及剥夺黑人选举权符合宪法规定,二战期间,它还支持了政府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后来,大法官们还废除了反歧视行动计划和旨在增加少数族裔政治代表的立法计划。但另一方面,从191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逐步废除了南方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规定,遏制对刑事案件黑人被告实施外表合法实为私刑的惩罚,并最终裁定居住、交通和公共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无效。
历史事实表明,最高法院几乎从未不加掩饰地维护过少数族裔的权利。大法官们主要反映主流民意,所以难以保护真正受压迫的群体。如果有人不这么认为很可能是受布朗案及其后续案件的影响。不过,那些判决也是受社会及政治影响,同时反映了社会及政治的变化。
布朗案法官们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称种族关系已经有了“惊人”且“持续的进步”。这些变化足以说服数位认为法律理由不足以宣判学校隔离无效的大法官们。
宪法权利若不落实,就没什么实际意义。即便最高法院做出了进步性种族判决,往往也没有实际效力。1917年的布坎南诉沃利案没能实现居民区的种族融合,布朗案在判决后的10年里对南方腹地几乎毫无效力。相比之下,其他判决的作用则要大得多。
1950年的斯维特诉佩因特案让南方腹地外的公立大学实现了种族融合,1944年的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则在南方城市掀起了黑人选民登记革命。究竟是哪个政治及社会条件影响了法院进步性种族判决的效力?
史密斯案之所以有比布朗案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因为,所有黑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投票权,但一些黑人比起种族融合学校更愿意就读经费相同但种族隔离的学校。
此外,二战的民主意识形态与投票权的直接相关性要大于与无种族隔离教育权利的关系。战后返回南方的黑人士兵常常直接拿着退伍文件去市政厅登记投票;而不会直接找到当地教育委员会,要求让自己孩子入读种族融合学校。
黑人在某些权利上的分歧确实比在其他权利上更大,但二战后他们对落实所有权利的斗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足了。斗志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源于更有保障的人身安全。
若坚持宪法权利很可能招来殴打或谋杀,那就不太值得了。即便普莱西案判决不同,也很难改变南方铁路的隔离现状,毕竟在一个私刑猖獗的地方行使无隔离旅行的权利,势必会给黑人带来生命危险。不过,到1950年,私刑绞死基本过时,战后黑人原告遭遇经济报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遭遇肢体暴力。
反对者的反抗强度也会影响最高法院进步性种族裁决的效力。1940年代时,绝大多数南方白人反对取消小学种族隔离的力度超过了反对黑人选举权的力度。二战带来的民主意识形态和黑人教育的进步让许多南方白人改变了观念,认为仅让白人参加政党初选是一件“残酷而可耻的事”。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南方白人仍在强烈抵制废除小学种族隔离,这涉及到取消年幼孩童间的种族隔离,而这些孩子有男有女,势必会让绝大多数白人联想到种族间通婚。
毫无疑问,公民权利采用公共执行会比私人执行更有效。司法部掌握的资源远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只有它能采用刑事执行手段;它也没有遭遇经济报复和肢体报复的风险。史密斯案之所以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司法部做出了有真正威慑力的威胁。
类似地,在《1964年民权法案》授权司法部长提起诉讼后,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速度就急剧加快了。公共执行还有其他私人原告无法使用的手段,比如威胁终止权利侵害者的公共拨款,以及任命联邦官员取代冥顽不灵的州官员。

可用的律师数量及其专业素质也会影响公民权利的执行。早期诉讼胜利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就是,南方鲜少有执业的黑人律师,即便有也往往没受过良好训练。绝大多数白人律师又怕引起公众反感而不愿接手民权案件。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资源有限;在1940年代以前,南方许多地区都没有该组织的分部;没有当地律师协助,它就无法插手。不过二战以后状况变了,白人律师更愿意接民权案件,南方也有了更多训练有素的黑人律师。
事实证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组织对公民权利的落实至关重要。如果只有在最高法院的胜利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要落实权利就必须有后续的诉讼。如果没有强大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支持,后续诉讼是很难维持的。
黑人个人鲜少能负担得起数千美元的上诉费用。黑人个人也欠缺起诉的积极性,毕竟诉讼一拖就是几年,会扰乱原告的生活,也会给他们招来毁灭性的经济报复,有时甚至是肢体暴力。
只有数十年来代表黑人争取权益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才能把握住诉讼的好处,同时分摊诉讼的风险和成本。若是二战期间该组织没有大规模扩张,黑人选民登记数量就不可能在史密斯案后大幅增加,各地也不会在布朗案后出现针对学校隔离的攻击。
不过,该组织对民权诉讼的实质性垄断也不尽然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南方白人提供了一个易于攻击的目标。1950年代中期,南方白人对该组织的猛烈攻击几乎使它在南方腹地的活动完全停摆,还阻碍了废除种族隔离诉讼的进行。
法律命令的相对明确也会影响公民权利的落实。
尽管绝大多数南方联邦法官都认为布朗案的判决大错特错,但职业责任感往往会阻止他们违抗该判决;他们承认州强制执行的学校隔离必须结束。然而,布朗第二案的判决非常模糊,也就毫无意义。它没有为南方法官提供政治掩护,这样一来,即便他们想要积极推动判决落实,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他们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人,绝大多数法官都选择了拖延和逃避。
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会自动落实。即便民权诉讼中原告赢了,若他们没有足够权力落实判决,这场胜利也就毫无意义。在南方黑人受压迫最重时,他们甚至连提起针对教育拨款中明显违宪的巨大种族差异的诉讼都做不到。直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南方种族条件改善,为民权组织支持民权案件打开缺口,最高法院才接到了针对披着合法外衣的私刑行为的起诉。而布朗案后的9年中,密西西比州连一起要求废除学校隔离的诉讼都没有。
诉讼需要律师、经济资源和一定的人身安全保障。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时候,最需要法院公正种族判决的人恰恰是最不可能得到这样判决的人,压迫重重的外界条件让他们根本无法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会产生间接后果,比如让某个问题凸显出来,激励胜诉方(或他们的对手)。毫无疑问,布朗案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学校隔离上,他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逃避,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一个立场。对于1954年的北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势必意味着反对种族隔离。但对那些想要保住自己工作的南方政治家来说,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捍卫种族隔离,谴责布朗案判决。
布朗案也给了黑人希望,让他们相信种族关系是有可能彻底改变的。在布朗案的激励下,南方黑人提起了要求废除学校隔离的诉讼,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投票权、学校平等、警察暴行和就业歧视问题上转移到了该案判决上。布朗案的议题设置 效果意义重大,因为南方白人对废除学校隔离的反对程度要远大于对黑人所寻求的其他改革。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是布朗案改变了美国白人在学校隔离问题上的立场。南方白人强烈谴责该判决。绝大多数北方白人虽然支持它,但也是因为他们本就认同该判决的观点,而非受到该判决影响才改变了立场。此外,在1950年代中期,他们的支持相当敷衍,非常冷淡。在1960年代早期之前,北方白人几乎都不支持采取激进手段落实布朗案判决。北方人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受民权运动的影响要远深于受布朗案的影响。
事实上,最高法院数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种族判决似乎是引起了政治反弹而非引导了民意对其判决结果的支持。1842年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似乎挑起了北方州对最高法院的反抗,反而制定了更多保护当地自由黑人免遭绑架的激进举措。
1857年德雷德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禁止联邦管制国内奴隶制之举实际是声称共和党违反宪法,此举引发了共和党人对最高法院的谴责和反对。布朗案激发了南方白人对种族变革的强烈抵制,并驱使极端主义政治家利用言论煽动暴力。
然而,就像布朗案一样,强烈抵制会引发强烈反制。布朗案所引发的暴力,尤其是针对和平抗议者,并有国家电视台转播的暴力,彻底改变了北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为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立法铺平了道路。
民权诉讼无论是否成功,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激励和组织功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为黑人讲解他们的宪法权利,并让他们对种族条件可以改变心存希望。该组织的许多分部就是围绕诉讼而建,也确实是卓有成效的集资工具。
法庭上,黑人律师成为了黑人观众的榜样,毕竟法庭是南方唯一允许种族间互动的地方,黑人律师也就成为了唯一可与白人在几乎平等的条件下同场竞技的人,而他们所展现的法庭辩论技巧否认了认为黑人不如白人的传统成见。
二战前,南方黑人生活在专制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下,基本无法使用诉讼以外的其他抗议形式,比如政治动员、经济抵制、街头示威和身体抵抗。当时,诉讼并没有与其他抗议策略竞争稀缺资源,它的优势就在于不需要大规模参与者也能取胜,而且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法庭上进行。
不过,正如早期民权领袖所了解的,单就诉讼而言,它对种族变革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1930年代查尔斯 休斯顿就曾警告称,“我们的仗……不能依靠法官来打”,他敦促“社会和公共因素必须得发动起来,最好是在正式开始诉讼前,再不济也得与诉讼同时进行”。
然而到1950年代,诉讼在最高法院取得的胜利是如此令人瞩目,布朗案带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声望是如此之高,即便当时已有条件开展直接抗议行动,也会被众人所忽略。1950年代时,诉讼开始与直接抗议行动竞争稀缺资源,而且似乎是占优势的一方,直到南方白人拒不执行布朗案判决,令其形同虚设,才暴露出诉讼本身对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是多么有限。
尽管诉讼在动员种族抗议和取得最高法庭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胜诉案件也确实带来了进步性的种族变革,但它并不具备直接抗议行动的所有功能。诉讼会使黑人更相信精英的黑人律师和白人法官而非他们自己,相比之下,静坐、自由乘车和街头示威更有利于培养出黑人自己的机构。此外,直接抗议行动更能制造冲突,更能煽动反对者暴力,而事实最终证明,这些对改变整个国家的种族观念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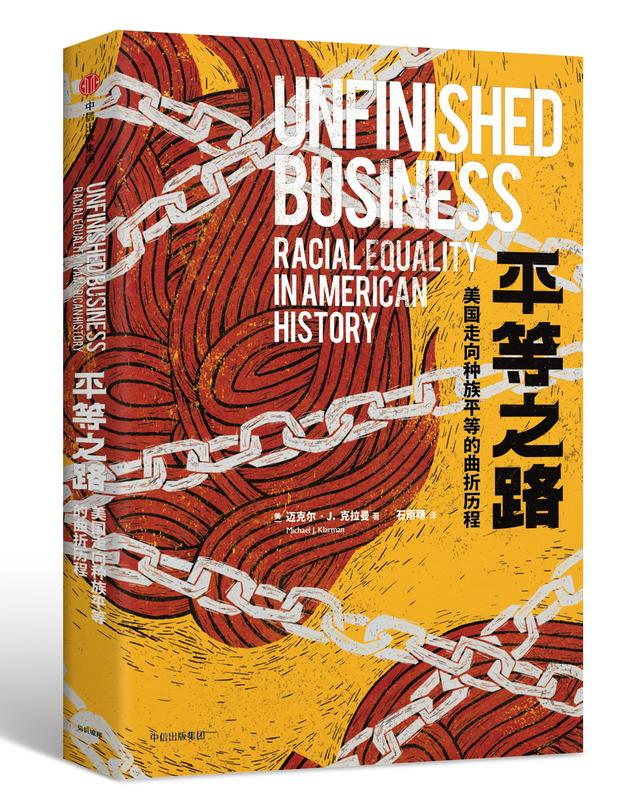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