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Trabzon纯粹是为了去附近的苏美拉修道院,至于城市本身,Ozgur回答简短:“很丑,仅此而已。”而事实是,苏美拉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反倒是城市本身——我两天后离开时几乎是依依不舍的。
几乎所有临海的城市我都不会太讨厌,若是加上依山而建,那简直不可能难看了。Trabzon就是如此,我攀上高处的Boztepe公园俯瞰全城时,觉得它有点像香港,却又没有冷冰冰的摩天大楼隔绝其中,你能清楚地看到城市的每条街道,过马路的人。那是个周日,家庭,情侣,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坐在山顶喝茶,野餐。一家人请我为他们拍下照片,又邀我加入他们。大人们语言不通,叫Aley的小女孩充当翻译。她总是不管大人们说了什么,自顾自跟我聊天发问,全部涉及个人隐私:“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能加FACEBOOK吗?”
短短两天,我不知接受了多少陌生人请的茶水。早餐问餐厅经理要一瓶水,他递给一瓶常温一瓶冰过的。我结账时,他摇摇头,朝我眨眨眼睛,跟我说再见。遇到土耳其航空飞上海的机长和空乘,他们付了我的午饭,说我来土耳其是客,若在中国遇到,我再请回他们就是。机长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问我想不想家,他们今晚就飞上海,可以带我回去,不用买机票。女空乘在一旁撺掇:“我们过几天再把你带回来,行不行?”
我说就冲这,我有天一定要买票去坐你们的航班。
苏美拉对我来说,不能说是“nothing”,但比起这些陌生人的善意,它的意义只有指甲盖儿这么大。
Merve是这些陌生人里唯一和我成为朋友的。
先是我的AIRBNB主人土耳其男孩Sencer带我认识了他的沙发客美国人Sam,Sam和我一见如故,领我去见了他的土耳其朋友Merve。我和Merve又一见如故,她请了假开着车带我去她最喜欢的森林野餐。

Merve26岁,英文超好,在首都安卡拉为政府翻译文件,也一直为土耳其的一个妇女权益NGO做义工,还一边学法语申请去法国读关于人权的硕士项目。她已做了两年的沙发主,常年收容没钱住旅馆的世界各地背包客,都是女孩。她上周刚刚送走两个身上只剩100美元的日本姑娘。
她特别喜欢阿塔图尔克,小森林就在他的故居附近,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自己开车来这里坐一会儿。不用说,她投了CHP。但她却说自己是穆斯林。
“这不矛盾吗?阿塔图尔克可是一个反宗教的世俗主义者。而且,你是我在土耳其遇到的唯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英文很好还信仰伊斯兰的年轻人。”我很惊讶。
“我投CHP,并不代表我认同他们所有的政见。我今年刚刚信的伊斯兰。”
“每个土耳其人的身份证上都写着我们的穆斯林身份,但我一直没有认同过。这是政治强加给我们的,你可以改其他信仰,但非常复杂。你要上法院,找警察,要填很多表格,不同的人问你一大堆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这种折磨的。于是我很早就想,我要去了解那些宗教,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我读了佛经,读了圣经,也读了古兰经。最后我被Rumi(13世纪波斯诗人,伊斯兰学者,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的诗打动了,为了读他的原著,我去学了阿拉伯语。然后我又去读了古兰经的原著,感受到伊斯兰与我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是的,我是穆斯林。”
Merve非常漂亮,化着淡妆,没有戴头巾,开着一辆大众的SUV,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女白领无异。她正在准备人生中第一次斋月,下周就要启程去苏菲派的圣城孔亚,还计划要跟她的义工组织一起去非洲服务,因为斋月的主题就是牺牲和奉献。她明天还要去接受一家反政府的报纸采访,我问她会不会担心,因为她是为政府工作的。
“大不了把我炒了,我本来就讨厌这个政府。之前只是讨厌,现在是极其厌恶。你知道他们偷偷给IS送武器,让他们杀库尔德人吧。他们收容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都是逊尼派,而什叶派穆斯林呢,他们就只能等着被IS屠杀。我是穆斯林,我对苏菲神秘主义感兴趣,但不属于任何派。古兰经上没有这些称呼,都是后来的人强加的。”
Merve把我送回市中心就要回办公室加班,“今晚得熬夜了。接了很多私活,我需要攒钱去上学。”
“你可以做AIRBNB的,我住的主人以前也是沙发主,后来发现可以挣钱以后就改出租了。完全不费力,挣钱也快。”
Merve笑了,“我也没那么需要钱。但那些来我家睡沙发的人,的确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回到市中心广场Meydan,一如既往的喧闹,这一大块平地是所有人聚集的地方:各种肤色,不同人种的人。Trabzon非常奇怪,有大量长相偏希腊金发碧眼的人,也有偏中亚长相的人,还有安纳托利亚中部传统土耳其人,和很多从沙特来的阿拉伯人,从格鲁吉亚来在这等伊朗签证的背包客,还有新增的叙利亚难民。
我坐在广场的餐厅等饭吃,一个叙利亚小姑娘走过来兜售纸巾。她其实不是兜售,只是抱着一大堆比她还大的纸巾站在你面前,什么话也不说。她来错了地方,这里没人需要纸巾,餐桌上堆着一大叠。她站了三桌,都没有卖出去。快走到我面前时,她看我一眼,我手上正拿着餐厅的纸巾呢。这回,她决定放弃,转身要走了。“嘿!”我叫住她,把一里拉递给她,又从她怀里拿了一包纸巾。
回去收拾行囊的路上,我想起书包里还有买来备着的面包,就掏出来送给了街边乞讨的小男孩。他双手合十,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语言。
这样就到了土东之旅的终点了,我最后一次跑去看黑海,夜里终于是黑色的了。这些一个月前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Van,Kars,Trabzon,现在对我意义非凡。我先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土东,现在我相信直觉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后来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当人人说着流利的英语问我会不会说英语时,我想念在土东连比划带猜的交流,想念骑着自行车冲到我面前问“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urkey”的小孩。我心疼Kars和凡城的贫穷,却不愿看到旅游业像改变卡帕一样改变土东。
Ozgur说,不会的,那些人害怕库尔德人和IS,他们不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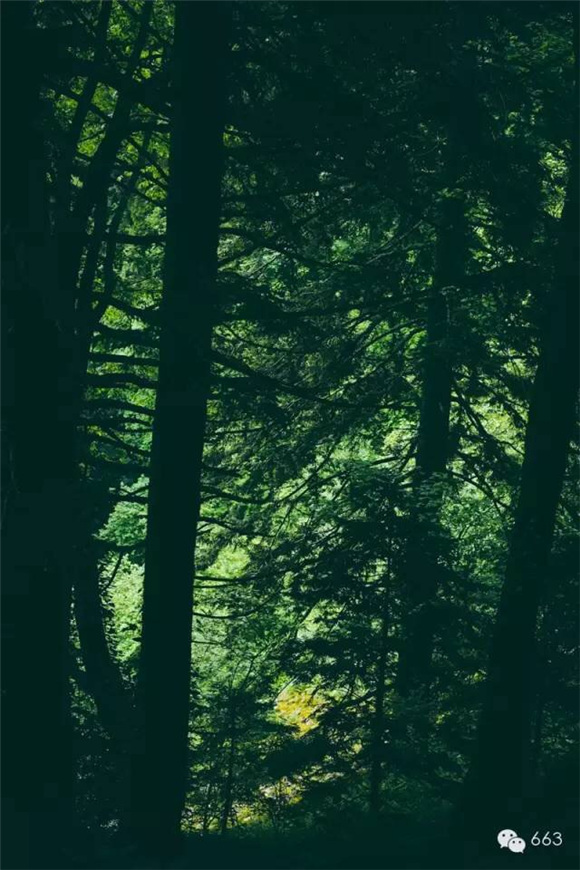








***
本文转载自663(yunke6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想要获取更多有意思的内容,请移步界面网站首页(http://www.jiemian.com/),并关注乐趣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歪楼】:esay1414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