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剧帮 俞露儿
好消息哪怕是小,但也总带有一股活力之风:在这届上海白玉兰奖上,首次对编剧类奖项进行了原创和改编的区分。
事实上,原创和改编的二分是国际惯例,剧集类的艾美奖就是如此,而此次白玉兰也漂亮地颁出了编剧类的两座奖,此番慷慨,既肯定了编剧改编创作的付出,也体现了对原创编剧的尊重——并蒂莲开,本身就是对影视的源头内容的肯定性加磅。
一、原创不只是情怀,而是要红尘落地
坦白说,原创的往事,包括现状,仍有不少尴尬姿势,其一就是原创编剧这个概念。
所谓原创,其实指的就是从故事源头构思,就来自于编剧本身,无非以可供拍摄(或搬演)的台本形式呈现而已。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以剧本形式完成的,但他本身就是个writer,甚至不会有人降维说莎士比亚是编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作家。

莎士比亚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改编成电影
举个例子,中央戏剧学院的写作教学课,是不会把原创写作和改编写作分开上的,因为默认从最源头就要有创造力的活水,从小品到短剧到完整剧本的写作,参差多态,但都是作者的原创故事,这是一种学术默认、也是训练默认。
一言蔽之,原创作者就是把一个完整承载着人物和母体人物的故事世界,从零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至于形式,小说、散文、戏剧剧本、影视剧本,只是奏鸣它的不同乐器尔尔。若说琴中有,何不指上听,无奈太多人关注指着月亮的那只手指,而忽略了月亮本身。
上述看来,白玉兰的一变二,其实是一种专业角度的正本清源,同时这一信号,对目前行业内的原创作者来说,是信心利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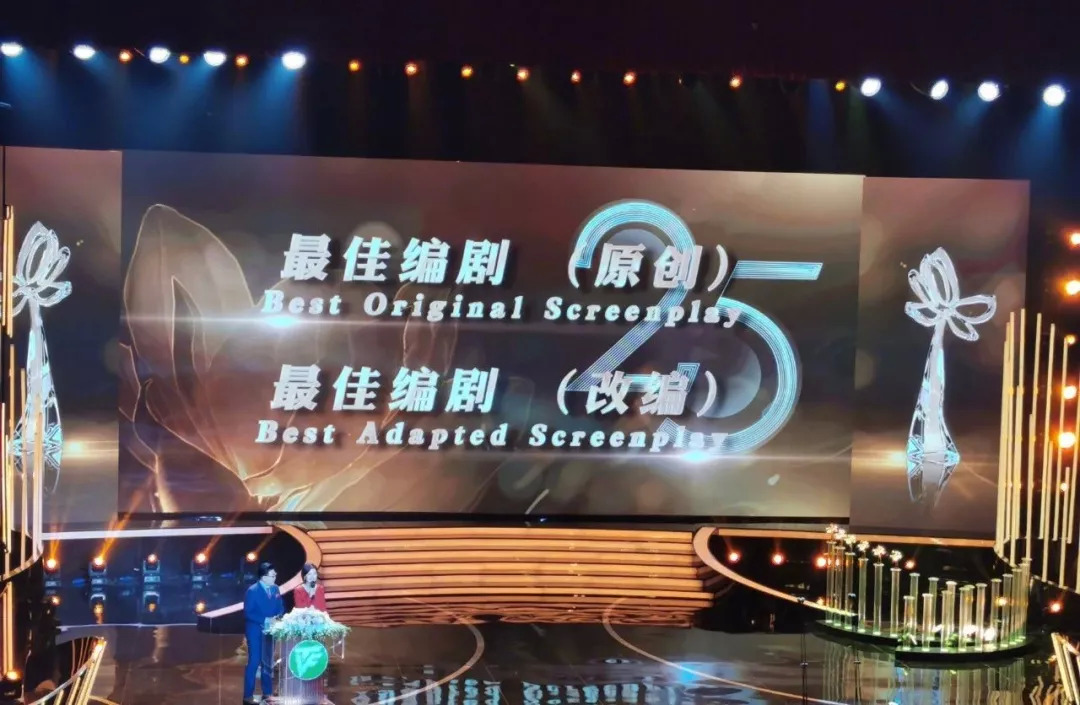
第25届白玉兰奖颁奖现场
提及“信心”二字,就涉及原创在前三五年的艰难处境。我始终认为,原创追求的不是情怀,而是红尘落地。而怎么落地,在之前行业内资本狂潮、盲目追捧大IP的环境下,极不现实。
一切都用数据直尺的话,原创意味着0流量,大IP意味着提前的饱和数据,原创意味着风险高能预警,大IP意味着短平快盈利游戏。
任何选择,未必孰优孰劣,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原创固然冒险,但跟风才是最大的冒险。”说这话的背景,是随便一个网文IP就几千万,而一谈原创,顿时色变,结果变成做原创是在搞情怀了。
绝非如此。中国电视剧是有不亚于美英、日韩的原创传统的。从《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空镜子》、《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年又一年》、《大明宫词》,包括近年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北平无战事》、《嘿老头!》等等。中国原创一度在表达质量、创作欲望,作品水平方面,都相当拔群,且原创血统作品,往往能创造出品质剧现象,且具有很强的留存性。

风吹猪飞,风停了,天上的猪们纷纷落地,在地上走的,还是扎实搞创作的那批,虽然姿势寂寞了点。随着大IP的纷纷折戟,行业中的出品方和制作方,都开始进入冷静期。也正因为这种以失败为代价换来的行业沉淀,才让原创编剧,得以鸡尾酒般分层,清晰了,有色彩了。
所以这次白玉兰颁原创,对行业也是一个正本清源的信号。
其三,原创是风险,也是机遇,但唯独不是情怀,因为从创作者的角度说,原创其实是挑战、是自我博弈、市场博弈。虽然编剧的总体数量在增加,但优质编剧终归稀缺,只因编剧本身的专业门槛很高,原创编剧更需要生活体验、感受力、想象力、卓然的敏锐、扎实的技术,在我看来,还有难以被动获得、甚至求之也不可得的热情和胆识。
原创的工作更像抟土造人,不是补天,而是开天辟地第一宗。星罗棋布,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物,是人物背后的作者世界观和审美存在,一切的优点会在原创作品中绽放,就意味着一切缺陷会在原创中放大,放大到责无旁贷,为什么?因为原创,就意味着作者是第一责任人。
但凡光彩的,永远是重担。照我看,除非真心爱写作,如果只为稻粱,原创并非编剧个人的上佳选择。因为所谓胆识,也不过凭借热情而来,否则不必千难万险,去做战原创风车的堂吉诃德。
血泪没有,不掏心肺,做不了原创,也不必做原创。
这样看来,白玉兰细分的这个奖,既是两两召唤,也是促使一批创作者自我扪心,到底如何定位,诚不我欺。

第25届白玉兰奖颁奖现场
二、IP是中性词,改编经典仍是花开一枝
与原创编剧对应的改编编剧,仍是影视剧中的很大一支力量,无论在商业上、艺术上,都有发展价值。
这就说到一个IP问题。照我看,对IP不应捧杀,要么捧,要么杀。
犬虎难画,邪魅好涂。对IP应该先去妖魔化:IP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本来就是一颗平常心。如何让这颗心跳得更好,我个人觉得就是回到改编对象本身来判断质量。
商业属性和艺术属性并不矛盾,大数据只要不是唯数据论,也是很有一番参考价值——大家都是来帮忙的,帮的什么忙,就是判断这个故事,或者小说,值不值得改。
这个值不值,我觉得主要角度要从以既往数据为核心,转变到以内容质量为核心。
关于改变对象,经典文学仍有灼灼其华者无数,好的国外影剧,不光是中国引进改编,在本土也是一改再改,比如简·奥斯汀,光是《傲慢与偏见》就有数百个改编版本。所以在改编的内容把控上,引进更多专业人才,借助更多有判断力的头脑,才能“不是为了IP而IP”。

电影《傲慢与偏见》
迎合观众已逐步曲终人散,想要不在数字游戏里撞南墙,只需跳出IP,以剧做剧,有这种逐步剥离、回归内容质量的心态,也是产业成长的积极面。
其二,我一贯认为真正好的改编编剧,也是一个创作过程。IP为什么之前纷纷重挫,涉及一个文化产品的专业转化问题,正如上言,编剧的门槛很高,改编编剧的门槛也很高。即使原作再好,只要作者本身没有编剧背景,几乎都难令自己的剧本表现优于前者,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子,比如美国女作家,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安妮·普鲁。作为小说《断背山》的原作者,经由她自己改编剧本,也是拿了奥斯卡学院奖的。除了凤毛麟角,就意味着大量的原作需要专业的编剧来进行影视改编——我们既难以想象一段只有数据没有质量的朽木,如何被改编编剧雕得游龙戏凤,也很难想象一个读不懂故事、对原作缺乏热情、编剧专业素质堪忧的创作者,能改编得出一部杰作。

电影《断背山》剧照
因此,只要产业存在,好内容永远稀缺,而好编剧,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编剧,昨天缺、当下缺、未来还缺。
每一部最后成品优秀的改编作品,都注入了编剧的二次生命体验,而每一部最后失败的改编作品,改编编剧也难逃其咎。无论原创还是改编,编剧永远和作品是命运共同体,需要的都是殊途同归的创造力,这点,无疑。
对内容越重视,行业越有生机,能令行业促发生机,真是善莫大焉、头功一件。
只因造血力,才是一具肌体的最大安全感。此次编剧奖项细分,在上海之地,可谓浮云散,明月照人来,照来的,就是“剧作中心制”。
剧作中心制的序曲时代,呼之,欲出——今年的白玉兰,是为破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