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张颖
编辑|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个夜晚,北京东棉花胡同的江湖酒吧门口,一位准备上台即兴表演的乐手着急地寻找自己丢失的手机,酒吧里的队友催促他赶紧准备登台,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机拨打自己的号码,多次尝试未果后留下一句“完了,我还得分期贷款买个新的”,便转身走上了舞台。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鲁斯乐迷的乌托邦之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台下的观众多以布鲁斯爱好者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这位丢手机的乐手,也许是江湖和全国大小Livehouse的台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灯和流量很少能向他们汇集——即便拼命做着各类演出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收入,就连换一部手机都可能要分期贷款。

北京东棉花胡同的江湖酒吧
这些乐队的命运,让人想起在参加《乐队的夏天》的节目录制时,借钱买新琴的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打车费能省则省的Click#15,很多乐队都表现出不符合他们音乐和名气的“贫穷”。
好在就在这个夏天,一批好乐队的命运却因为《乐队的夏天》而发生了扭转。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满为患,老板调侃来的姑娘大多是为在《乐队的夏天》里大火的Click#15乐队键盘手杨策。在节目之前,杨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鲁斯乐队mojohand经常在江湖演出,但现场远不及此火爆。至于Click#15本身在全国的演出,则和节目里其他热门乐队的一样,变得一票难求,甚至出现过“秒空”的情况——而在上节目的时候,Click#15的主唱Ricky还曾透露,过去一个月玩音乐的收入可能还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国演出一票难求
但这些少数幸运儿的背后,仍然站着大批“命不好”、在温饱边缘挣扎的乐队和乐手。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全国范围内有近三万支乐队,但上了节目并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积的乐队还没能被“夏天”的热浪包围,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乐队图鉴。
事实上,自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乐队在国内萌芽、兴起之时起,这项文化在国内就始终处于“寒冬”中:早年间玩摇滚乐的人聚集在树村、霍营一带,连方便面都要去隔壁借着吃;现如今,方便面自由基本得以实现,但想靠玩音乐赚钱在大多数时候仍是奢望,“要是指着玩乐队的钱生活,大家早就饿死了”。

年轻时的乐手们
由于目前国内演出市场、版权体系和乐队运营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潜伏在地下的独立音乐人们还未等到一个对他们展开怀抱、给予回报的成熟市场。然而与这样看似毫无希望的现状对立着的,是那些不愿意用“穷且益坚”这样的词汇描述自己的乐手们。他们对音乐的坚持,似乎也印证了白岩松在《乐队的夏天》总决赛上说的那句话:“可能你觉得这是一个怀旧的节目,不,这是一个与明天有关的节目。”
而促使他们奔向这个“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爱”再无其他。
“单指着玩音乐养活自己?天方夜谭!”
“2000年之前我就没怎么挣钱,也干活,一礼拜干两次,一次赚150、130,勉强度日,有一顿没一顿的。”成名之后,音乐人臧鸿飞在回忆起自己当年的艰苦岁月,而对于大批不知名的乐队来说,遭遇可能会更惨,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钱只够吃顿饭、挨着饿也要“摇滚”的情况,正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05、06年左右,我们乐队曾在一场拼盘演出中拿到过一笔让人记忆犹新的演出费。”成立于2004年的金属乐队霜冻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对毒眸说道,“六十七块五毛钱,连乐队里几个人一起吃顿饭都不够。”过去的十几年里,霜冻前夜的遭遇是绝大部分中国乐队都会经历的。

霜冻前夜巡演郑州站 (图源见水印)
上世纪末、21世纪初,以Livehouse和音乐节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场在国内刚刚兴起,为无法登上演唱会大舞台的独立乐队们提供了表演的机会和收入的来源,可由于当时演出市场起步阶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难的情况下,独立乐队想要从中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后的今天,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演出市场总体规模已达到514.11亿元,对多数独立乐队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某金属乐队的主唱告诉毒眸,去年他们在北京的一场演出收入仅为4000元,乐队成员5人进行分成后每人拿到800。“这样演出还并不多,基本上是一个月里依靠乐队获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时租排练室、换器材,或者演出结束吃饭、打车加起来的费用远远不止800块。”
这样一种窘迫,在新乐队的生活中属于常态。
吉他手小严(化名)曾有过一场“难忘”的演出经历:他所在的乐队曾在业内前辈引荐下于一场拼盘演出中“压轴”登台,可是演出进行到后半夜,现场观众在看完心仪的知名乐队表演完纷纷退场,等到他们上台时,台下只剩下乐手们的朋友、场地工作人员和零星的观众。一场演出下来,一分钱的演出费也没有落入他们的口袋。
据了解,目前如新裤子、痛仰等知名乐队参加一场音乐节的费用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晖对毒眸表示,这样的乐队在国内只是凤毛麟角。“好比我小时候喜欢踢球,觉得自己长大了能成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养活自己,但是长大后才发现,大多数人是无法靠踢足球赚的钱买房子、买车的,玩音乐跟踢球一样,初心都是因为热爱,而不是想着能靠它赚钱。”

新裤子的彭磊和庞宽
“朋友的乐队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点解散了,最近新歌发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国各地跑巡演,终于能赚着钱了。”去年秋天,已经从国内某重金属乐队退队的主唱大明(化名)对毒眸感慨道。这个所谓“能赚着钱了”,仅仅只是每个成员年入三、四十万,可即使是这个数字,对大多数独立音乐人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台上十分光鲜的乐队,在台下都显得有些“落魄”。在一个月只能赚取1000块演出收入的日子里,Click#15使用60块一小时的排练室还得与人讨价还价。更有很多吉他、贝斯手想换把新琴必须勒紧裤腰带“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于乐手来说,生活费可以节省,但玩乐队练团、买乐器等和乐队相关的硬性支出却省不下来。

Click#15在《乐队的夏天》演出现场
更叫许多人头疼的是出专辑的支出,无奈之下,不少乐队不得不选择众筹等方式来筹钱。现如今,打开一些演出购票软件,常能看到乐队们的众筹信息,对国内的乐队而言,这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聊起这点,大明也颇为唏嘘:“如果我当年继续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赚钱的那天,太难了。”
可惜大多数人并没有等到那天。小严向毒眸表示,独立乐队赚不到钱的情况往往会持续很多年,因此有不少乐队最终都会为生计所迫而解散。在仅仅依靠玩音乐无法养活自己的情况下,放弃音乐似乎才是很多乐手最终的归宿。
“玩音乐还是大城市适合一些,但长期赚不到钱、生活成本还大,家里人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不靠谱。”曾担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诉毒眸,随着年龄增长,来自家人的压力和现实生活的打压日益明显,回到家从事无音乐无关的工作、过着与创作和演出毫无关联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而想要坚持下来,则意味着乐队和乐手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求养活自己的方式。“千万别死磕,做什么都能养活自己。”盘尼西林的经纪人徐凯鹏对毒眸说道,“音乐绝对不是逃避现实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借口。”

盘尼西林乐队演出现场
于是乎,一些希望坚持下去的独立音乐人纷纷在乐手之外兼顾着其他的身份,像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做程序员这样的“兼职”白领乐手还有很多。“我们从来也没指望过乐队赚钱,像鼓手老纪,在长春做音乐培训也做得不错。”萨满乐队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调侃鼓手为长春音乐培训产业的“辛迪加”,并表示乐队成员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让生存现状比预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乐队主唱则偶尔给一些“三四线”明星写歌、编曲,尽管不是自己擅长和喜欢的类型,但为了生计、为了运作乐队,也还是要继续写下去。“讨厌的是,那些写过的曲子老在脑子里,忘不掉。”破碎乐队主唱姜微对毒眸说道,“但没办法,总得吃饭。”
做独立乐队为什么这么难?
演出市场逐渐壮大、大小音乐节遍地开花,可在中国做独立乐队,为何还是这么难?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独立乐队收入基础的演出机制并不够完善。”有演出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毒眸,演出行业作为传统行业,其发展一直较为落后,存在商业模式落后、数据化能力不足、缺乏技术支撑、二级市场混乱等诸多问题。因此虽然乐队看似红火,但实际上的盈利空间并不像外界想的那么乐观。

上海某音乐节现场
以作为乐队收入重要来源的音乐节为例,根据小鹿角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2018年新出现的音乐节品牌达到140个,但是2017年出现的音乐节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仅有48.7%。有资深从业者对毒眸表示,由于少数成功的音乐节带来看似赚钱的繁荣假象,让大批非专业的选手进入“玩票”。
由此带来的很多音乐节质量堪忧的情况并不少见。打扰一下乐团主唱陈圣仑谈到,有些商演打着音乐节的旗号,承办方也不具备现场演出的专业知识,邀请乐队演出事先却没准备调音和音响设备,甚至反问乐队:“你们不是自己带吗?”葡萄不愤怒乐队主唱小臻也告诉毒眸,从2013年开始陆续参与各种音乐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么设备都没有”的音乐节——

葡萄不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乐节都在赔钱。”有资深业内人士对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乐节投入六千万最后只有300万票房收益的惨痛案例,而这对于乐手来说,音乐节主办方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能给予乐手的经济回报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音乐节之外,作为另一个重要收入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样很难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据了解,国内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达百万,且成本回收的周期很长,这让很多中小体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仅音响设备敷衍,连乐队演出宣传也草草了事,无法为演出的推广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乐队在巡演过程中遇到只有老板一人,并且身兼调音师、保洁员、酒保数职的Livehouse。
有业内人士曾经对毒眸表示,国内优质的Livehouse数量极少,且大多只存在于一二线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难,“靠情怀养着”的不在少数,在近几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内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为经营无力等问题而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

仙人掌音乐节跳水的观众
而在“以演代宣”的独立乐队商业模式下,音乐节和livehouse两大演出阵地的不稳定,除了不能够给乐队带来稳定的收入外,也同样阻碍了很多乐队形成稳定的、有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进而乐队的一些版权工作、衍生品生意也无法随之展开。
据网易云独立音乐人报告显示,超68%的音乐在音乐上获得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版权收入仅占9.8%。有多位乐队主唱对毒眸表示,从未想过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台上的播放获得收入,“百八十块的也顶不了什么用”。而在国外成熟市场中,已经能让很多乐队赚得盆满钵满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国内也大多是一个月卖出个位数的T恤的状况。

版权收入仅占9.8%(截图来源网易云独立音乐人报告)
大环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独立乐队自己也相对缺乏“经营自己”的运作意识。早在2008年,环球音乐营销部门Bravado的首席执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义:“每一个乐队是一个品牌,你必须这样想。”但目前国内专业的运营团队少之又少,很多乐队压根意识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个“品牌”。
徐凯鹏告诉毒眸,中国大部分乐队还是处在被动地“等活儿少上门“的状态,运营人员大多也因为非相关专业出身而经常显得极为毫无章法。“不是现在的年轻人音乐创作上能力不够,而是市场上没有一个商业上成功的乐队作为标杆,让年轻人觉得做乐队是个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与多个乐队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乐队对打造人设和粉丝运营的抗拒,他们认为注重粉丝运营意味着讨好和妥协,而“真实”才是乐队最宝贵的东西——但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思维往往限制着乐队信息的传播。其实反光镜乐队就曾在《56网红人馆》中说道:“只有当乐队商业化成功了,才能让大家知道乐队是可以作为一种职业的。”

反光镜乐队在音乐节的演出现场
缺乏良好、专业的运作,由此带来的独立乐队和音乐人的无法获得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的缺失则在某种程度影响着他们的“走红”,进而让赚钱成了一件有难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职做音乐的能力。”小臻对毒眸说道。
“总有人一直在玩音乐”
成熟产业机制的建立和乐队运作意识的养成,都并非一朝一日可以实现的。可以预见的是,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多数乐队还是必须面对生存所带来的困境——而与这种困境相“矛盾”的,是并未熄灭的对于音乐的热爱和玩团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营胡同里,被称为“Underground气质最正的摇滚圣地”的SCHOOL学校酒吧,几乎每天都有乐队和乐手演出。作为一个尊重独立音乐人、支持他们演出和成长舞台,它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各种音乐类型的乐队的到来,很多乐队是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气、能被台下乐迷喊出名字调侃,有朋克、金属,也有嘻哈、电子和爵士。

不少乐队聚集在SCHOOL学校酒吧
“没有人来演出是为了赚钱的吧,能上台演、有观众听就够了。”一位乐手在上台前对毒眸说。而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的Livehouse里,这样的乐队和乐手不计其数,他们组成着国内独立音乐充满生机和可能性的版图,当“穷”已经几乎成为玩音乐的标签时,乐队和乐手仍然无处不在,从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选择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今天,当人们站在每一场演出欢呼的观众群里,甚至不用去工体、音乐节等更大的、专业的舞台前,只需要在DDC、坛、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里,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兴表演里,从每一个听众的表情和欢呼里,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音乐始终被需要着。
而这种从台上到台下,对音乐的渴求,换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乐队的生生不息。

日本乐队 Crystal Lake现场
尽管他们之中有的音乐人已经“老大不小”了,“红起来”的渴望早已不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对得起听众的音乐。“与行业发生关系是惊喜是意外,最重要的还是闷头做音乐,外面热闹成什么样和我们关系不大,只要我们对得住这一屋子的观众就好,这是立足之本。”萨满乐队主唱王利夫对毒眸说道。
作为受众范围相对有所局限的金属乐队,成立了十几年的萨满似乎并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经接近中年的乐队成员们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场演出都卖力得像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岁月和现实完全没有在他们的音乐中留下负面的影响;而霜冻前夜也同样展开着自己新一轮的巡演,只不过他们在与音乐硬碰硬的这些年里学会了更加沉浸、专注地热爱音乐本身;破碎乐队把新的EP命名为《我将献身于这一非福即祸的理想》,并带着这种理想主义重新投入到新一轮的演出中,尽管他们并不知晓观众是否会对这种情怀买账,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为他们的音乐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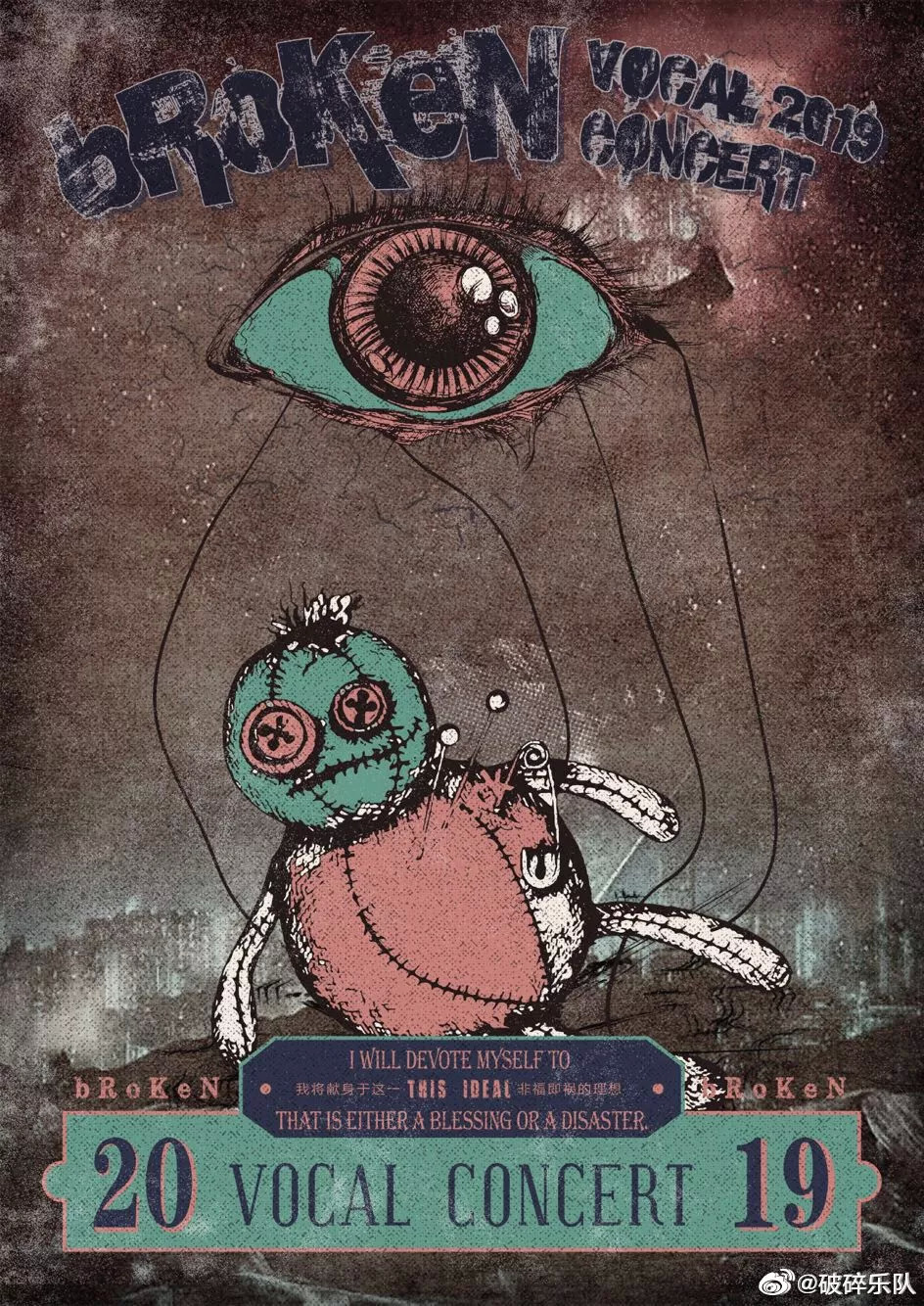
破碎乐队的《我将献身于这一非福即祸的理想》
不少乐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较传统,做音乐不是他们能接受的,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告诉他们,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小臻对毒眸表示,之所以还坚持着,是因为始终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乐证明我自己”。
用时间证明自己和音乐,这似乎成了很多乐手的习惯。打扰一下乐团的主唱米时可也曾经历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对,可四五年下来,观众对他们的关注、认可让他们的音乐更加坚定和成熟,而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米时可家人的态度,“现在他们非常支持我。”主唱陈圣仑对毒眸说道。

打扰一下乐团在演出现场
年轻的乐队也一如既往地热血与坚持着,葡萄不愤怒的主唱小臻在巡演中忘情地试图“跳水”,享受着表演本身,他和团员们没有着急着去“扩大热度”,而是决定先把作品做好、希望能被人们长久地记住;而一些更初期的小乐队,即使没有演出机会,只能“蜗居”在大学校园的某个排练室里,但仍然一边打鼓弹琴一边对前方的舞台充满憧憬和期待。
一代音乐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总有人正在舞台上燃烧着生命和热血去诠释义无反顾的音乐精神。
坚持过后,曙光似乎就在前方。《乐队的夏天》之后,原本鲜为人知的Click#15在全国巡演多站门票秒空,MAO Livehouse内容总监河岸对毒眸透露,Click#15票房至少上涨了400%;观众们喊着要给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打钱、面孔乐队甚至与知名汽车品牌合作打起了广告,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也下沉到了广场舞伴奏中;一些在此前并不知道Livehouse是什么、不知道放克和朋克有什么不同的粉丝们,都一股脑地涌向了独立音乐圈。
“允许一部分乐队先‘夏’起来,先夏带动后夏。”某媒体人在知乎撰文写道。虽然并不清楚,在全国其他数以万计的乐队里,还有多少能“后夏”,但乐队们似乎并没有想过放弃。

《乐队的夏天》现场
而在节目之外,更大的变化也在酝酿当中。随着演出基础设施、渠道等各方面条件的完善,到线下观看演出的生活方式会最终“扩圈”,圈到更多乐迷。以MAO Livehouse为例,其内容总监河岸表示,最初“扩圈”的方法是硬性要求每家店周五、六、日三天必须有演出,“让乐迷养成MAO在周末一定有演出的认知。”
作为国内头部音乐公司的摩登天空,从最早进入音乐节、扶持独立音乐人开始,也将继续更深地涉足音乐产业并为之贡献力量。“中国那么大,我们才干到哪儿到哪儿啊。”在沈黎晖看来,国内音乐市场是一片充满希望的蓝海,从《乐队的夏天》《我是唱作人》《这就是原创》到《一起乐队吧》等,都在印证内容生产者和观众已经关注到了原创音乐领域,说明原创音乐本身已经是“大流量”的存在。

摩登天空主办的草莓音乐节现场
而乐迷群体的热情,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甚至有很多乐迷因为喜欢的乐手而学打鼓、学弹琴,被节目点燃的摇滚之魂从全国各地的高校中“复苏”,新的年轻人们前仆后继地投入到音乐里——这似乎是一场永远都不会散场的聚会,上世纪属于乐队的辉煌年代过去,一个新的、比以往更热烈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乐队的夏天》大幕落下,31支乐队从节目的舞台走下,更多的乐队却走上了属于他们的舞台。鼓声回荡在每一个音乐节的土地上空,与那些摇旗呐喊的观众们呼应,站在台上的每一位乐手,不管是饱经生活磨难但不觉辛苦的,还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怕的,他们始终都站在那里。

也许世俗眼光里的成功、金钱和名望,对于他们而言都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出,去了MAO!我们把乐队的名字写到了MAO的墙上,太厉害了!”吉他手小李(化名)对毒眸兴奋地分享他们第一次演出的经历。事实上,不管是在高校自己“瞎玩”的年轻乐队还是已经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炮儿”,对始终热爱着音乐的他们而言,乐队早已成为注入血液的一部分,“站到台上,沉浸在音乐里,才能感觉自己真正活着。”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