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造就 雁行
1969年5月,阿波罗10号达到了4万公里的时速。两个月后,阿波罗11号宇航员踏足月球。自此,再没有人企及同样的飞行速度,或是踏足同样的高度。如今,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筹备载人火星任务。但即使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代能毫无离愁别绪地告别地球,彼时的人类恐怕已经不是智人,而是另一种更加智能的设计物种。现在的人类适应不了外太空。
在进化生物学家看来,“适应性”是一个物种内,所有个体存活下来并成功繁殖的平均倾向,它是自然选择的标尺。从解剖学上讲,现代人类起源于30至20万年前的非洲,跟他们的共生微生物携手进化,并迅速遍布全球。在地球上,人类如鱼得水,但太空对我们这个物种有害无益。那里寒冷、空虚、没有空气——这还是最不值一提的。真正的问题是数不清的压力源,尤其在辐射面前,太空服和飞船的保护都显得捉襟见肘。
地球磁场和大气层屏蔽了太空中肆虐的电离辐射,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而在火星表面(没有磁场,大气稀薄)或太空飞船上,高电荷态的宇宙射线的长期辐射,或是太阳质子事件的爆发,这些都会杀死细胞,或导致其功能失常;也可能撕裂DNA链,敲除上面的碱基对。死亡或功能不良的细胞会诱发心脏疾病,或导致认知衰退;DNA损伤就更可怕了:在细胞自我修复的尝试中,错误会不断累积,形成突变,最终引发癌症和遗传疾病。
凡是低地轨道和范艾伦辐射带以外的长期载人航天,都超出了NASA当前的“可接受风险”范围。除非技术突破接连降临(可能性很低)——开拓快速航线,在飞船内部安装辐射屏蔽装置,在目标星球建立地下宿舍,以及快速折返,诸如此类——人类生理跟火星任务水火不容。要在火星或更远星球建立殖民地,这根本不可想象。
但物理学家,包括与NASA合作的一些物理学家,已经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人能否通过基因改造,变得适应太空旅行?这不禁引人思索:在下一阶段的人类进化中,我们肩负着何种责任和使命?
这些物理学家的提议中不乏讽刺。人类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对扩张的狂热。就我们所知,其他古人类倒没有这项特征。作为我们表亲的尼安德特人和人类共同生活过5000年,但始终没有离开欧亚大陆。对我们而言,探索是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古往今来,曾有多少不堪一击的小圆舟、独木舟仅仅凭着对陆地的一丝希望启航,去占领汪洋大海中上所有的岛屿!
人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火星。但要满足这种渴望,我们得动用手头所有的技术,创造出一个“接班人”物种。
乔治·彻奇(George Church)是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领先的合成生物学家。他认为:“要降低太空飞行的风险,一条较为可能的途径似乎就是针对成年的候选宇航员进行生物工程改造。”
他找到了40来个有利于长期太空飞行的基因。该清单中包括CTNNBI——赋予人抗辐射能力的基因;LRP5——增加骨密度的基因;ESPA1——常见于藏族人群,使人适应低氧环境的基因;以及一堆可能增进智力、增强记忆、减缓焦虑的基因。其中甚至有ABC11——对封闭空间颇为友好的“轻体味”基因。(根据一位空间站成员的描述,载人航天飞船的气味跟监狱类似。)
彻奇联手其他知名生物学家,比如抗衰老研究者大卫·辛克莱尔(David Sinclair),创办了哈佛医学院的空间遗传学联合会(Consortium for Space Genetics),旨在研究太空环境下的人类健康,并推动该领域的探索。他的设想,是用“病毒交付的基因疗法,或微生物组、表观基因组疗法”,改造航天员的机体。“有关小鼠对辐射、骨质疏松、癌症和衰老的抵抗,我们已经掌握不少知识,”彻奇说。他强调,很多基因都在医药公司的名单上,有的药物正接受临床试验。将基因疗法作为宇航员的预防性药物,这听上去并不为过。
基因疗法或能改造人类,使我们更适应太空,但要殖民新世界,我们得培育出一个新的种族才行。遗传学家克里斯·梅森(Chris Mason)提出了太空殖民的“五百年计划”,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 拓展我们的基因组学知识,包括哪些基因应挂出“免打扰”牌,因为动了它们,结果不是致死就是致残;
- 微生物的基因工程改造;
- 通过基因的添加、删除和修饰,创造出永久性、可遗传的变异。
梅森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让人类细胞结合Dsup基因。该基因由缓步动物所独有,能抑制辐射对DNA的破坏。缓步动物极其坚韧,可以在太空环境中存活;或许,它的基因也能增强人类对太空的适应。梅森的实验室还构筑人为情境,探索了p53基因的癌症预防作用,并希望有朝一日,P53能被植入人类基因。大象有很多p53基因的副本,且很少死于癌症;在人类基因中添加p53或能遏制太空辐射的破坏。
梅森还有一些更接地气的研究,包括编辑抗辐射奇异球菌(Deionococcus radiodurans)。这是一种嗜极生物,可以承受寒冷、脱水、强酸和高强度的辐射。它们对抗辐射的方法,是重新编译受损的染色体。梅森希望,微生物能像植被一般,生活在我们的皮肤和肠道内,或是在太空飞船的表面,保护我们不受太空射线的伤害。“微生物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东西。”
一些研究人员的提议更具科幻色彩。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斯·王(Harris Wang;音)希望以诱导方式让人类肾脏合成身体无法制造的九种氨基酸。假设有这样一种全能型人类细胞,它能在一个细胞之内合成健康所需的一切有机化合物,那么要培养这样一种细胞,我们还需要250来个新的基因。但人体组织真要由这样的细胞构成的话,宇航员只要喝糖水,就可以生龙活虎了。这样,太空飞船就不需要携带或者先行运送大量食物。还有科学家提出了“光合”太空旅行者的概念,还有人提议编辑“太空战队”成员的个性,使他们无畏地奔赴最远的前线,因为,那是他们真正的终点站。
我们恐怕得换一种面貌,才能奢望离开地球。但即便技术上可行,我们应该这样做吗?优生学一直是个邪恶的词:只有种族灭绝的暴君,才会把它挂在嘴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且没有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这样做符合伦理吗?支持制造“航天员种族”的论据是:造就他们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优生学:没有人会因为不受待见的习惯或品质而被迫减少生育;没有哪个群体被囚禁起来并强行绝育,乃至更糟。
至于征求同意这一点——没有人的遗传是自己选择的;我们都是父母的产物。梅森认为,这种尝试是无关道德的客观必然。他的“五百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多个行星系统中建立宜居环境,以避开太阳系中灾难性事件导致的人类灭绝。”他解释说。“不论你道德上首推什么,生存总归是第一要务。”
阿波罗10号、11号任务完成后不久,索尔·贝娄(Saul Bellow)出版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一书,他写道:“再过多久,地球就不再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了?主啊,可不是嘛!若要离开,现在不正是时候吗?要么抛弃这颗蓝色、白色、绿色的伟大星球,要么被它抛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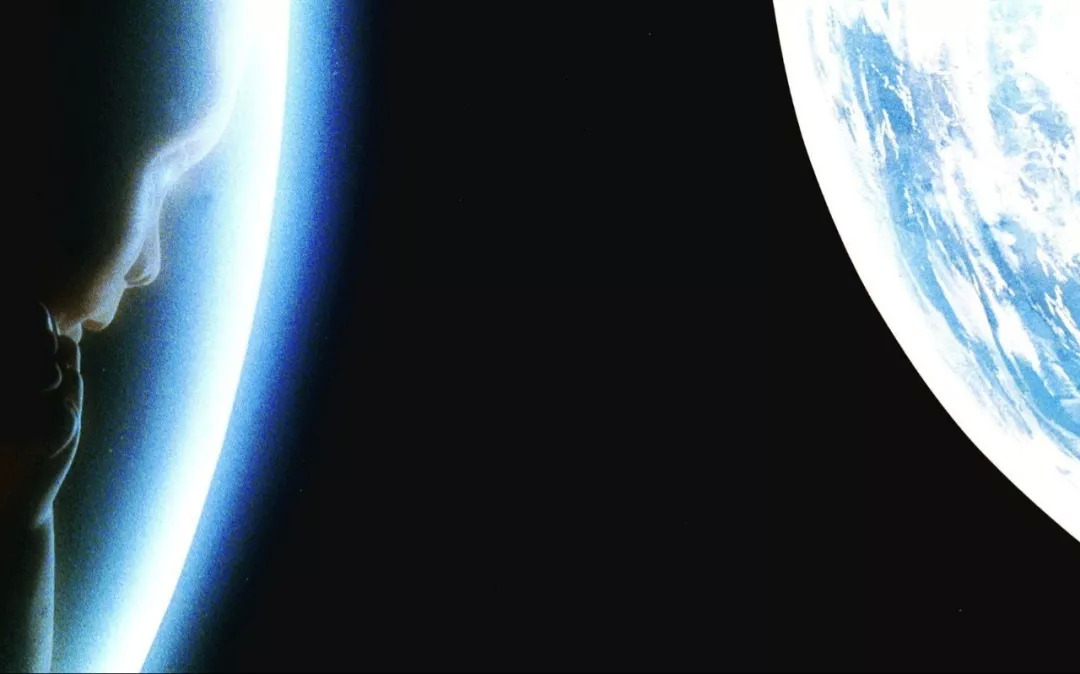
《2001太空漫游》
眼下的我们,倒是可以想想后代告别地球之事。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应有意识地引导自身进化,而不是将命运交给时间、偶然和死亡——历来为进化服务的因素。当然,未来告别地球的“接班人”跟我们的差异,将不啻我们与尼安德特人的差异。“将有新的物种形成,”梅森说,“问题不在于会不会,而在于什么时候。”
校对 | Lily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