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都观察特约作者维舟
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最近热播,剧中邀请了三种形态的家庭:魏大勋一家三口原生家庭;袁弘、张歆艺代表夫妻家庭;汪苏泷、尤长靖则代表青年合租群体。虽然网上也有人吐槽“节目本意是探讨男性做家务,播出的内容却更像《我家那小子》+《我家小两口》+《Hi室友》的综合版本”,试图融入更多血肉亲情、明星笑料,对待“家务”这一真正的关键元素则多点到为止,不过“男人做家务”本身变成一个公共话题,这仍然值得认真对待。

▲综艺《做家务的男人》倡导新家风,树立新美德,创领新传统,让“男人做家务”成为和谐共创的社会新风尚。节目以“有故事的生活”为创作理念,呼唤家庭责任,增进沟通方式,分享生活智慧,在平凡中刻画出温暖、美好、幸福的生活图景。爱奇艺
实际上,节目中也并不隐瞒家务话题在不同家庭形态下的差异:魏大勋及其父所代表的传统家庭模式中,爷俩基本是不做家务的,老母亲差不多包揽了所有家务活——不过,即便她也说:做家务这么多年,“委屈是肯定的”,只不过“中国传统的女人就是这样,但是我希望下一代不要这样”。张歆艺夫妇俩可就是“新一代”,袁弘的确早起做饭、带孩子,对妻子的要求几乎没有拒绝。而汪苏泷、尤长靖两人则因为是合租,那就完全不存在传统家庭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因为彼此本来就是陌生人,本就理所应当公平地承担各自的家务,甚至作为室友合租规则严格执行。
当然,这毕竟是“节目”,很可能三组人只是按照剧本的人设来“演”。从剧中做菜、犁地等很多场景看,他们的“做家务”,与其说是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倒不如说更像是下乡采草莓,是一种“体验”——偶尔为之说不定还觉得挺新鲜有趣。像袁弘这样的明星夫妇,难道真有多少家务需要两人动手做?甚至就算是生活中的普通家庭,小夫妻俩在孩子出生之后,家务通常也都多是家里老人承担的,而此时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分工负担不平,才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
话说回来,现在“家务”分工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之一,其实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征兆,因为在更为传统的时代,是没有“争议”一说——那往往就是全社会都认定天经地义是女人的活,甚至连女性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样的时代距今不远。1944年,李式金在云南发现,当地“家庭妇女工作劳苦,而男人除间有职业外,很多是安居坐食”;在福建则有出名的“惠安女”,里里外外的家务活都是女人承担。这与其说是男人“懒”或女人“地位低”,倒不如说是社会默认的分工就是这样,因为按说女性地位不低的泸沽湖摩梭人母系社会中,情况也是如此:男人历来负责的是打猎、伐木、战争这些,家务事从不插手,只不过现在无仗可打,打猎伐木也不允许了,于是他们就无所事事地打桌球。在他们看来,男人不应做家务,就像女人不应去打仗一样,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使许多男性心安理得地享受家人的服侍,并无任何不安,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务技能当然不可能高。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学问世所公认,但他不理家务,甚至有时连自己居处的地址都搞不清楚,因为平日都由夫人安排。前些年李娟的文集《阿尔泰的角落》里,所描写的北疆社会,很可能也是许多传统家庭的写照:“几乎我们所知的每一个哈萨克女人都终身沉没在家务活的汪洋之中,也不知道她们都从哪儿找了那么多事来做。而男人们从外面回来,鞋子一踢,就齐刷刷往炕上躺倒一排,就一直那样躺着,直到茶水饭食上来为止,真是可恶。”
感到这样“真是可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现代女性意识,因为在传统社会,一如辜鸿铭曾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所说的,“无论是希伯来人,还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本质上都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一样:通常,真正的理想女性总为家庭主妇。”在晚清民国的上海宁波帮商人家庭中,研究妇女史的学者曼素恩甚至还发现有一种“主妇居家崇拜”(the cult of domesticity),也就是将女人外出工作视为一种有失身份的事,虽然这些富商家庭的女性在家未必需要做多少家务,常常只须管理仆佣完成即可,但她们的社会角色被限定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上,抛头露面去谋食是被社会所非议的。
这乍看可能令人惊讶乃至不适,但其实却是当时的人之常情。别说是在中国,就算是在20世纪初的西欧,据《私人生活史》第四卷的说法,“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待在家里,不用工作。如果不得不工作的话,也最好能在家里做——比如做做缝纫。只有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才会迫不得已到外面去工作。”这与今天的社会心理形成鲜明对比:“多少代以来,妇女们的理想都是待在家里,照顾家庭。对女人而言,外出工作意味着极度贫困和落魄。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做家务是与社会脱节的,是从属于男性的,而外出工作才切实标志着妇女的解放。这也是20世纪的主要社会变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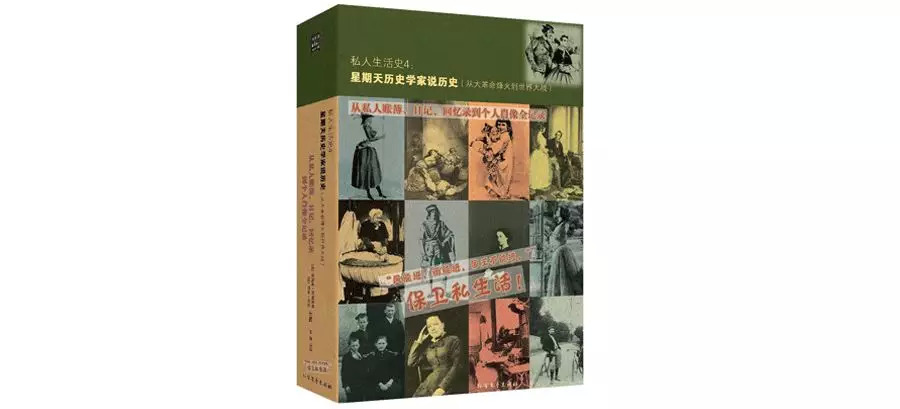
▲ 《私人生活史》第四卷讲述了西方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业化、民主化、交道阶级绘至沓来,现代性走上历史前台,形成一种新的私人生活模式: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爱恨情仇、生死欲求、交往模式均呈现出今日我们时代所熟知的图景。但与此同时,工业时代的来临,亦给私人生活埋下了致使的威胁。 私人生活史
虽然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已经率先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真正推动社会剧变的,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因为太多男人上了战场乃至战死,妇女就不得不被动员起来作为补充的劳动力,而一旦让她们走出家门,再想让她们回去就难了。现在看来或许不可思议的是,连欧洲最宽容开明的荷兰,1934年还禁止与男性同居的女性担任公职,次年又进一步规定,已婚女性将被开除公职;1950年,荷兰的天主教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母亲应在家里,而不是工厂!”当时社会默认的分工是:男性养家糊口,已婚妇女不必赚钱工作,而应呆在家里做家务。二战初期,苏联男性劳动力严重短缺,意识形态也强调妇女解放,但尽管如此,一项调研却发现,苏联妇女平均每天要做4个小时家务,而男人只做1个半小时。这与美国在19世纪末的情形类似:尽管美国妇女地位较高(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中说“美国女人是最糟糕的家庭主妇”),但一百多年前90%的美国妇女每天至少花4个小时做基本的家务劳动,特别是烧饭做菜、清洁房屋和洗衣晾衣。
实际上,工业革命可能反倒强化了这种性别分工。这里值得再次引用《私人生活史》第四卷的观点:“婚姻平等的结束是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明确分离之后。从此,妇女就变成了婢仆。男人之所以能坐在扶手椅里看报纸,而听任妻子在家里忙活,是因为丈夫‘下班回家’了,即他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同时,家庭经济也‘金钱化’了:节省花费变得不如挣钱重要。”这也是至今在我们的社会中常见的一个逻辑:家里谁挣钱多,谁就有话语权,而挣钱多的人,理所当然地豁免于家务琐事。
不过,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不仅是让一部分女性走出了家门,还催生了一系列我们如今熟知的家用电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以往仆佣的职能,多少使得家务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例如,在洗衣机发明之前,人们需要花不少时间洗衣服,冬天冷水里浸泡尤其不舒服。此外,工业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对人力的更高效利用,这就使在家做家务的妇女劳动力看上去像是被“闲置”了。1920年秋,美国教授梅亚访日后提出建议:“在我看来,首先解决问题的根本点在于家庭。现如今,日本家庭必须立即改变的是,把主妇的手从做饭洗衣里解放出来,使她们能把时间用于其他的生产事业。实际上,日本主妇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饭洗衣等事情上,连教育子女这一‘社会根本’都无暇顾及,遑论提高自己的修养,思考其他社会事业,这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战后的“年功序列制”下,一度反倒是更多女性都成了只依靠户主工资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专职家庭主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最终改变这一点的,并不是女性的抗争或男性主动承担家务的觉悟,而是因为两个特殊的契机:首先是1990年后持久的经济疲软,使得很多家庭需要两人工作才能分担经济压力,因而希望妻子婚后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的男性,从1987年的38%,到2002年暴跌到了仅仅18%。其次是2007-2008年日本修改了有关退休金的制度,如果妻子是全职主妇,那么65岁起可以分到丈夫的一半养老金。消息一出,顿时掀起一股“银发离婚潮”,妇女们觉得无须再忍,很多一生埋头工作但完全不会做家务的工薪男在退休之际,被当成“粗大垃圾”般地扫地出门。

▲ 日本家庭主妇常常被看做一种专门的职业,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日本主妇的社会地位也不断变化。去年有相关日语论文发表,针对三部主妇相关的电视剧《昼颜》、《遗憾的丈夫》、《逃跑虽然可耻但有用》分别从婚姻文化、家庭构成、经济等方面展开分析。pakutaso
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简单地说,近代中国女性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走出家门,更多的不是因为经济、文化方面的变迁与推动,而是政治动员的需要。“做家务”与“革命女性”的形象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而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这不仅是一部分革命精英的事,因为社会上的女性都被动员起来参加运动与生产,《百姓生活记忆:上海故事》一书便说:“从1958年出现里弄生产组以来,上海再也没有家庭妇女这样一个群体了(个别的当然会有)。”
这可能也是一种特殊的遗产:上海女性本来在近代社会就有较为独立的收入来源(这与棉纺织业的发达有关),再加上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和生产运动,因而龙应台一度惊讶地发现,在上海社会竟然是男性做家务——所谓“马大嫂”(买、汰、烧,即买菜、洗菜、烧菜)长久以来是对上海“家庭妇男”的谑称。反倒是近些年来,这一优良传统有些淡化了,年轻一代的上海男人,已经不如父辈那么善于操持家务了——当然,某种程度上,女性也一样。
到了今天,已经很少人还将做家务视为自己的理想生活了,那大不了也只是一项生活技能,所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无论男女,都期望自己从家务中解脱出来,在更广阔的空间施展自我、实现自我,毕竟在人们的心目中,家务劳动仍然是重复、无聊、且无报酬的。麻烦的是,无论多么现代化,普通人毕竟总有家务需要做,一如《跨国灰姑娘》一书中所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通常要么外包给钟点工或老人,要么实施一种新的分工模式:主妇将那些粗笨的家务外包出去,而把诸如给家人准备餐点、陪孩子读书这样更能表达对家人情感的机会留给自己,这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将家务活变成了一场“在烹调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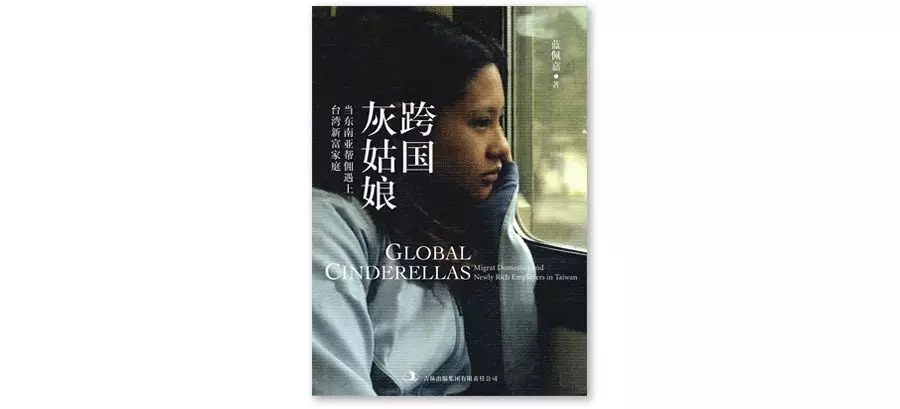
▲ 作者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全书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经由作者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 跨国灰姑娘
在《做家务的男人》中,主持人朱丹有一次说:“男人一旦能够做家务了,女人都能变美。”这固然是打趣,但倒也提醒了一点:在当下这个时代,男人对“理想女性”的想象在根本上就是相互冲突的,你不能既要对方貌美如花、又包办家务,能把所有条件都匹配的,你也未必配得上了。当然,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样:“男人做家务”这一点究竟有多重要?生活现实中,不少男人尽管会操持家务,但因为赚钱不多,还是在家里受够了嫌弃,甚至他们的沉默忍让仍被讥为“窝囊废”。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无论男女,其实往往还是将“男人要有事业心/会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家务”往好里说也只是个“加分项”。
新的改变不是没有,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在日前“阿里P8男”征婚引爆的讨论中,尽管很多男性反复强调170万的年收入是你无法想像的生活优越,但女性仍然很实际地坚决不要丧偶式育儿以及包揽家务,在她们看来,光有钱请保姆这种模式不是优选,而更希望是“中产+互相分担家务”这样一个模式。
要改变这一切,不仅需要男女平权的意识,还需要婚恋观的转变,以及对“男性气质”的重新塑造与认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