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卓然
这两天看到朋友圈里的消息,才发现原来前奥美广告创意总监、一般工作室PIY创始人兼设计师沈文蛟去世了,死因是熬夜猝死。
姑且不论沈文蛟之死和盗版侵害有没有关系,今天我想聊聊原创。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认识他是因为两年前他发过的那篇文章——《原创已死》。而沈文蛟是一个获得过多次设计界大奖——红点大奖的设计师,他设计的nude衣架为人熟知。
但长期以来,沈文蛟都在遭受盗版之苦,去世前依然在自己的微博上挂了错买盗版道具的剧组。
他在那篇点击率高达百万的《原创已死》一文中痛诉了网上数不清的山寨商家对一个原创者造成的打击。而戏剧化的是,这篇文章的确救他于水火。他那濒临倒闭的小店因此奇迹般地复活了。



是的,“原创”就是这么一个口号型词汇,是一种立场表达,一旦使用它,在舆论上马上能得到一方支持,哪怕在现实层面是另一番图景。
有些时候,原创也是一个不吆喝就不存在的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发文章,如果不申请个“原创”的标,那就等于对抄袭者说“欢迎光临”。之后再去维权、再去发奔走呼号“我才是xx第一个人”,没有人再会在意,可能还有人骂你炒作、骂你蹭热点。
而沈文蛟这件事,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搞不清到底应该去怪谁。作为一种终局性的裁判手段,法律是我们最容易归罪的主体。的确,评论区里的大量留言都说这是法律不健全的错,是执法者的失职,但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是无孔不入的。
但凡了解中国法律体系的创制,就会知道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设计在中国的标准并不算低。在民商事范围内,中国缔结或参与的国际公约、条约原则上可以直接并优先适用,而知识产权条约可以经过转化适用,这意味着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法律是国际标准的转化和腾挪,我们拥有的法律保护维度并不低人一等,并且已经经过了国际社会的认证。
对于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这份改革成果,我们不应该去否认和忽视它。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知识产权从君主制度下的地域性“特权”转变为“法权”,象征着民主制度的进步,见证了国际法律秩序的建立,也彰显了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融合的正面效应。
国际社会迄今已经制定了《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1994年的TRIPs协议得以签署,更加从根本上促进了司法改革在全球范围内的进阶。而其中的核心,即在于协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拿中国举例,中国加入WTO即意味着它必须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我国既存的法律体系进行大幅改动,以适应国际化标准,这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别国的作品和专利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成为参与者。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在落地上的难点在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问题与法律体系建立的规范性期待之间存在沟壑。TRIPs协定无法解决中国的城镇化矛盾,无法规避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旧疾和新伤时,国际标准亦无法给予我们答案。
可以说,山寨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市场逐利之罪,也是文化沉疴之果。而这种结构性之恶意味着,无论我们站在哪个环节向敌人出拳,都只会是打在棉花上。

我曾零星地参与过一些工业设计、建筑、时尚的知识产权保护座谈,这些座谈囊括了中国司法体系和产业方方面面的专家和企业,但大家每次的发言都差不多。
一是呼吁法律为“原创设计”开辟专属绿色通道,以适应每个行业的商业属性,比如时尚设计师的服装在走秀发布后要等6个月才上架,但如果走完秀后立马被抄袭,原创者根本还来不及打赢官司就被抢走了市场份额。
二是呼吁行业形成维权组织,用产业内的力量去给盗版者施压。但你只要扫一眼那些在维权上最能蹦跶的企业名单,就不难发现这个市场早已是劣币驱逐良币。行业的话语权大多掌握在家大业大的大企业手里,而这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做大,便已经是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低成本、高回报的经营方法。
还有比“拿来主义”更快更便宜的生产路径吗?
这些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严重。沈文蛟曾在文章里曾痛诉淘宝平台上无良商家盗版他的设计,盗版截图密密麻麻。曾经无形的、有地理限制的知识产权如今变成了公开可得的信息,已经很难被权利人控制。
这种现象在文字工作领域同样普遍,一篇文章刚发表,马上被抄袭和洗稿,抄袭的人手段稍微高明一点,打散结构、更改句子,维权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网络空间带来的边界模糊为原创者了解侵权范围造成了困难,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自己被侵权的认知错位,你以为侵权者只卖了50万,其实侵权者的抄袭者、抄袭者的抄袭者还卖了100万,但原创者是无法和这整个链条对抗的,他们大多数最终只能艰难举证,或者在诉讼请求上提出有限的赔偿额度,去面临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的现状。
当然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确在处理平台投诉侵权案件上优化了便利性,也加快了时效,但由于流量是其制度设计的基因,这导致整个平台必须张开怀抱欢迎更多商家入驻,并把资源交付到流量拥有者手里。因此在知识产权的维护上,平台始终只能站在防守的位置。而商业社会何其残酷,时间何其珍贵,等到发生了问题再去解决,原创者不死,谁死?
但更令人无奈的是,在《原创已死》一文在当初走红后,还有一大波“理性声音”出现。在知乎上、豆瓣上、微博上,一群“电商专家”告诉你,沈文蛟自导自演了一场大戏,用一篇哭天抹泪的文章把自己的店救活了。他们告诉那些被原创感动到去下单的人说:“你们被套路了!他是为了骗取大众的同情。”
原创固然不等于销量,一个屡获大奖的设计师也不一定等于好的商人,但“不懂电商”、“运营能力低下”的指控和“支持原创”不在一个逻辑维度里。我大概有些悲观,认为模仿是人类的天性,而经济是带着原罪的,《资本论》里说,一旦有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为了10%的利润,它就到处出现,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律法,如果利润有300%,它就会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假币在古代的欧洲就开始流通,美国曾经历欧洲盗版书盛行的时期,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寄希望于普法教育带来行业底线的提高,我们不能期待商业世界自己去筑造道德围墙。
回到中国,抄袭在这里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一直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去讲解Copycat的故事,百度词条上说“山寨”是广东话,是民间IT力量发起的结果。姑且信它。可以看到,在整个IT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一直很大,而资本对效率的追求、对短期内投资回报的看重都逼迫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也为其他行业创制了参照样本。
《福布斯》在2010年发布的文章《China’s Copycat Startup Problem》中写道,中国一度对风投文化的执迷,加重了资本对山寨初创企业的偏爱,鉴于投资者明显倾向于投资模仿者,“这可能是来自中国创业理念的直接结果。这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创想法并不好,也许是中国未来的企业家们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而这条路则对中国真正的创新能力造成了直接打击。
在这篇文章里,Google前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提出了中国的创新上限问题,这要求孵化器为创业者创造更系统性的生态。
但结果能做成什么样子,我们这两年也看到了,孵化器自己也可能倒掉。在社会大背景的局限下,投资者、创业者都很艰难。事实上,随着全球各国的互动越频繁,在知识产权的问题只会更多。
而在发达经济体里,特别是在北美地区,天使投资者的作用是帮助填补早期创业和风险资本融资之间的空白。天使投资人在支持更广泛的创业组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由风险资本资助的不同且独特的创新的可能性。
但在中国,“中国的经济和投资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一跃成为了一个只有少数穷人的社会。”上文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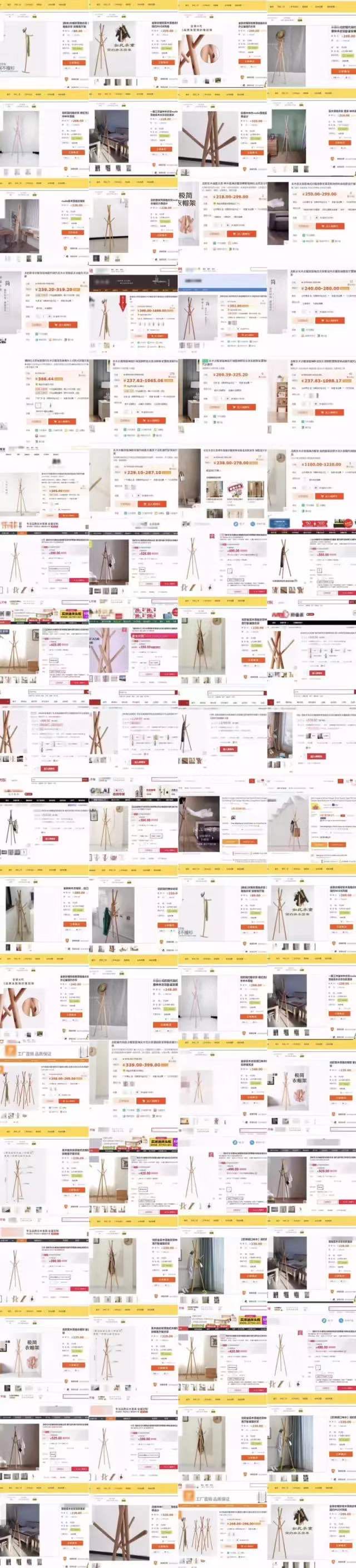
而这种跃进式的差异在短期内都不会消散,这在任何一个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里都不会消散。对山寨用品的大量需求体现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渴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两种权力诉求的交流方式。
因为在另一个层面,这种市场行动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我基本同意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观点,他曾在一个采访中说道,“山寨文化”是一种草根文化,但与主流文化并不对立,而是一种补充形式,这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而文化是具有滞后性的。山寨问题的解决,将等到一个结构性风险的化解或一个社会系统的重新构建,还要很多很多时间。
而文化也是会倒退的。很难说,复制思维如今不是因短视频的流行而不断增殖和培育。诸如抖音、快手等平台正用各种制度鼓励着每一个用户去翻拍原创视频,只要你点开配乐就能看到,少男少女们在镜头面前做着一样的动作、哼着一样的歌、露出差不多的小表情。
而观看者的工作,就是在这些众多模仿者中选拔出一个表现突出的人,然后点一点他主页上方的“follow”。等到他成长为新的流量拥有者,他也才能从巨头手里接过被允许“原创”的权力棒。
头部创作者永远不会死,原创也不会死,但它的每一步都踩在别人的尸体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