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电影情报处 卡西法
从1月到现在,电影院已经关门足足一月有余。在公共观影空间缺席的这段日子里,人们又开始无比地怀念电影,以及曾经自由出入电影院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大片定期上映,也没有新片贸然定档,疫情阻断了电影的正常上映,却无法阻止盗版资源的流通。转眼间,奥斯卡新片已经几经易手,从大银幕来到到显示屏,最后流转到人们手中的方寸屏幕上,还未上映就已被一睹为快。
尽管“盗版”两个字被写进法律明文禁止,但从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生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它却总是有一种特殊又复杂的情感。那个时候如果想看国外的电影,需要跑到音像店租借,或者在流动小摊贩那里用5块钱、8块钱买一张包装粗糙的盗版碟。很多人对电影的认知大概就来源于那几块钱一张、刮痕斑斑的盗版光盘,也正是借由这个媒介,意外地闯入了斑斓的光影世界。
情报君并非鼓吹盗版文化,而是希望在等待电影回归的日子里,通过讲述一个个故事,打捞一代人关于电影的热血记忆。情报君跟几位电影爱好者聊了聊他们的私人记忆,他们也大方地分享了在那个精神资源匮乏的年代,与电影相伴的日子。
讲述人:千寻,85后,电影爱好者
主题:小镇孩子的童年
记得人生中第一张电影碟片,是从我们家乡小镇上一家音像店里租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家小小的、从塑料门帘望进去黑咕隆咚的音像店,开在闹市街口,店主是一个三十多岁、头发常年油腻腻的男人,经常坐在收银柜台一个大屁股电脑的后面。

跟它结缘说来还挺有趣。我是在小镇上长大的孩子,小镇的童年总是很尴尬,既没有城里孩子的少年宫麦当劳新华书店,也没有乡下孩子的摸鱼钓虾掏鸟窝,无数个大白天都是自己跟自己度过,精神生活贫瘠得可怜。
记得有一年暑假,城里的表哥来我家玩,拿着一个神秘的塑料盒。一打开,嚯,崭新的一排《猫和老鼠》光盘,从第一集到第十多集码得整整齐齐,盘面锃亮,美不胜收。当时家里有一个老旧的VCD,可能还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家产,把光盘推进去的时候,会发出“咣、咣”的转动声,然后屏幕变蓝,那就代表开始了。
我记得我和这台VCD以及这十多盘《猫和老鼠》度过了一个相当快乐的暑假,它们给我的暑期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不过最后表哥走的时候,把光盘都带走了。
表哥走后,怎么才能再看到《猫和老鼠》是我当时最迫切的心愿,上课也不专心听,老师讲的东西到了脑子里全变成了动画。在终日的日思夜想中,我终于想起了街上那唯一一家音像店。音像店,尤其是黑咕隆咚的音像店,在当时小镇孩子们的心里是跟网吧是一个级别的,普遍觉得那是坏孩子虚掷时光的地方。可是剩下的那几集《猫和老鼠》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了,纠结很久之后,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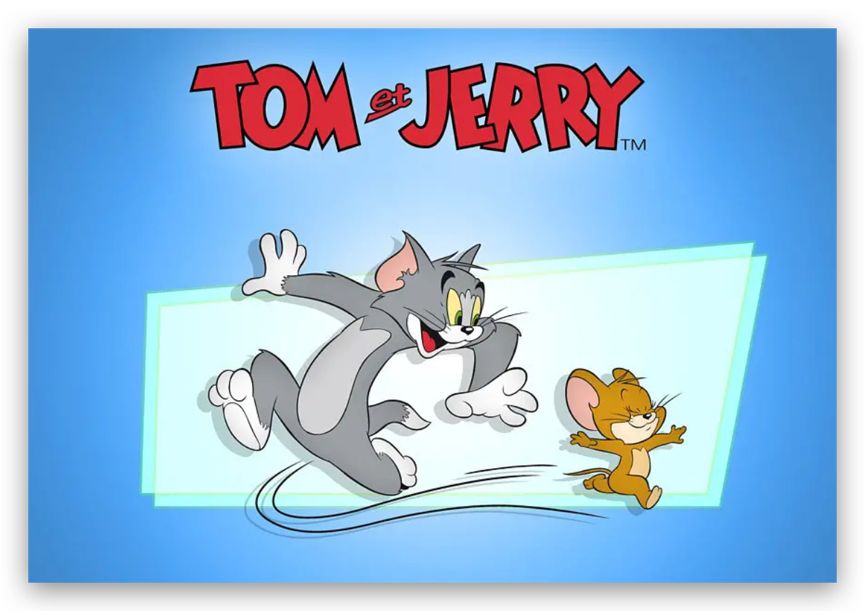
一次之后就有第二次,之后去的就多了。《猫和老鼠》当然是看完了的,更重要的是后来还从那里看了很多其他的动画片。小学四年级之前,我已经跟着《哆啦A梦》探险完七大洲四大洋,跟着《丁丁历险记》考古完埃及法老的陵墓,还从《数码宝贝》那里学会了各种进化技能,这些影碟和那台老式VCD基本构成了我童年全部的幻想土壤。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我看完了《哈尔的移动城堡》,那种震撼感让我很长时间无法平静。电影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第一次知道动画片还可以是这个样子。

音像店蓝色的玻璃门上贴着褪了色的海报,门口常年竖着一块黑板,每周都有新电影在黑板上出现,大部分都是畅销的灾难、战争大片。常常是一有更新,我就会跑进去找有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那个时候租碟一星期大概两三块,超时了再另外算钱,我看了碟总是忘记归还,因此总是四处收集家里的硬币并旁敲侧击地跟父母敛财。不过那个音像店的叔叔永远在电脑后面抽着烟,对别人租碟是否延期了也毫不在意。奶奶说他没上大学,没什么出息,只能在小镇上守着自己家几平米的店做些小本经营。他机械地做着收钱、把碟片交给顾客的动作,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很少与顾客攀谈。不过,“宫崎骏”这个名字我确实是从他嘴里听说的,在刚开始借碟的那段时间里,我所看的电影基本都来自他的指引。现在想起来,日本动漫对我的启蒙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后来小学毕业后,就去外地上学了。暑假鱼贯而过,前几年回家的时候看到音像店还在,后来某一天它突然变成了一家冷饮店,再后来它变成了一家服装店,春节回去的时候,发现那家服装店还好好地开着。家里有几盘碟到现在还没归还,我不知道那个叔叔去了哪里,后来又从事了什么工作,欠他的碟心里总觉得有点愧疚。
我偶尔会想起那家音像店,它在我单调的童年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那个在外面看起来黑咕隆咚的门店实际上并不恐怖,里面陈列特别简单,除了两排碟架,四周也都是用纸盒子装着的碟片,连小暗房都没有。不过,对于一个生活单调的小镇孩子来说,它代表着一个无忧无虑的斑斓世界。

对了,那家音像店的名字,好像叫“家唯数码音像”。现在想想,那个叔叔,可能就叫家唯。
讲述人:蒸汽,90后,自由职业
主题:地下音像时代的青春期
我对盗版碟的记忆,最早是来源于我舅舅。好像很多人的生命里都有那么一个喜欢电影、沉迷游戏,被亲戚们嘲笑不务正业的年轻长辈,我的舅舅就是这样的存在。
舅舅三十岁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每年去他那里玩,一有空他就带着我走街串巷淘碟,什么叶家宅、大自鸣钟、音乐学院,都是他带我去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上海有很多淘碟圣地,从黑胶唱片,到各国艺术片、地下电影的DVD应有尽有,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些交易二手电子产品的商铺,实际上却涌动着各种活色生香。有些碟店是有固定门店的,有些只在夜晚6点后的弄堂里出没,但无论是在门店还是在弄堂里,光线总是很暗淡,淘碟就好像变成了一件鬼鬼祟祟的事儿。
那个时候商家卖的大部分是包在一张纸壳子里的D9DVD,封面左下角贴着镭射防伪标记,壳子里还附赠一张海报。也有店家售卖一些制作精美的铁盒、木盒或者塑料盒包装的电影合集,但这些都不如前者畅销,所以它们的作用大多都是摆在墙角装点门面。
舅舅经验丰富,一般不直接逛大堂,他知道大堂架子上都是时新的电影,那不是他想要的。他会从店主那里接过提前预定的碟片,也会跟着店主闪进小房间挑选个一时半会,他总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些店主跟舅舅都很熟络,跟他说找不到的电影,可以帮他从供应商那里进货。
大约在高中的时候,我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电影,喜欢上了淘碟。最开始是从舅舅那儿拿自己喜欢的回来看,后来上了寄宿学校就开始网购,小心翼翼地从门卫处把包裹领回来,周末回到家就没日没夜地看。学校书店的《看电影》、《环球银幕》杂志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买碟的风向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伯格曼、杨德昌、黑泽明、侯孝贤、小津、今敏、老塔、安哲、大卫·林奇等大师,还有一些擅长香艳镜头的像丁度·巴拉斯、贝托鲁奇、阿莫多瓦、菲利普·考夫曼也是当时收藏的对象。

某天我爸突发奇想,突然给家里购置了一套家庭影院,其中包括一台索尼蓝光DVD播放器,自此之后我更是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喜欢的碟片氪金。不过我从来不喜欢让父母介入我的私人观影。万一出现意料不到的香艳镜头,会让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即便是阅片无数如我也要假模假样地维护自己的清白,义正言辞地把屏幕关掉。
将一盘碟片推进DVD播放器时,那种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一般电影开始时,先会播放大段的电影预告片,然后才会弹出正片的音乐界面,你可以选择字幕,也可以选择观看附带的花絮、导演访谈等。那个时候D9的DVD是可以在任何区域的机器上播放的,而且质量相当感人,它们不仅集画质最好的一区、字幕最全的三区、以及各个区域的音轨为一体,还会整合各个版本的花絮、导演评述音轨、预告片等,最后推出一个“终极发烧白金珍藏版”,有些连正版DVD都无法做到。我记得我当时买过一张蒂姆·波顿的《断头谷》,里面有个导演访谈,详细地介绍了那血淋淋的人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虽然网上买碟的快乐跟在实体店消费相比还是打了折扣,但淘碟过程还是相似的。先跟店主寒暄一番,问问有没有XX导演的片子,懂得人会跟你讲上半天,然后就可以开始激情下单。一些找不到片源的电影先拍下订单备注,等店主下次进货。如果电影实在太冷门,店主会花上好一阵子寻找,之后寄给你的电影很可能被刻录在空白光盘上。不过,几乎就没有他们找不到的片子,所以我常常怀疑,全网的卖家是不是秘密地共享着一个庞大片库。
那个时候总共买了两大箱碟片,大概有一千多张的样子吧,其中一部分都是看过的,更多是买了没看的,没看的后来也就一直没有看过。在我看来,收藏这些碟片就像是收藏自己的青春期,看到它们,我总是想起那些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发梦的日子。后来因为打击盗版越来越严格,店家跟打游击战似的不断更换着ID,再后来,那些在网上开碟店的店家陆陆续续关闭了,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在网上卖碟了吧?
记得有一年,舅舅回家,突然搬回两个大麻袋,里面满满当当两袋碟片,说要送给我,当时我开心得就跟中了500万似的。后来舅舅从上海辞了职,回到老家工作,从此以后再也没提起过电影的事,而我的淘碟时代,也渐渐落幕了。
现在仍然喜欢着电影,但基本不会再买碟片了,想看的网上都有,各大字幕组也相当勤奋。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观影口味没怎么变过,也仍然爱着那些带领我走进电影大门的大师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造就了一部分现在的我。

舅舅的那两大麻袋碟片,跟我学生时代的两大箱收藏仍然安静地在我床底下躺着,这次回去,我可能想看看它们。
讲述人:四月,90后,电影从业者
主题:关于开一家碟片店的梦想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卖碟的,有个装满碟片的屋子,向进进出出的人们兜售精神食粮,顺便展示财富;如果当不了卖碟的,我还可以当个走街串巷的放映员,骑着骡背着放映设备云游四方。

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天真可爱,且不说这两个职业现在是不是还存在,可能维持自己的温饱都有问题。
说起自己的淘碟记忆,大概也是从高中开始的。十多年前,在我所生活的小城市里,开音像店还是相当热门的职业,小小的地方盘踞着四五家不同特色的音像店,店里总是流连着很多年轻顾客,我也是其中一员。
每家店、每个店主都有自己不同的归类方式:有按照演员、导演分的,一个演员或导演的片子用橡皮筋捆成一打出售;有按照类型分的,美国大片、小众欧洲文艺片、港片、恐怖片、情色片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有按照上映时间分的,新片总是摆在显眼的入口,老片往往归纳在箱子里,要找自己想看的只能靠耐心与火眼金睛。
我一直觉得挑选电影就是与自我品味对焦的过程。你可能会意外收获某个大师的冷门作品,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收获一部获奖佳作,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反复的筛选、对比中锤炼出品味,并且延伸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感。记得有一次在外地玩,我和朋友来回花了三四个小时去不同的地方淘碟,腿都快走废了,但买到了一整套大卫·林奇早期的黑白作品以及尤里斯·伊文思的整套作品,我整整开心了一个月。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豆瓣这样的网站,为了买到心仪的碟片,每次淘碟前都会提前收集信息,去贴吧里查哪里有碟店,去翻论坛里大神们出的碟报。碟报类似于碟片评测,一些热爱电影的网友广泛购入碟片,然后不定期在网站上写评测,内容大多是哪些版本值得买,哪些版本有遗憾等等。我记得影评人妖灵妖在当时的网易上做过一阵子碟报,不仅包括电影还有音乐,这些都构成了我买碟的参考。
上大学之前,市面上已经开始流行轻薄的笔记本,但我特地要求爸爸给我买了个带光驱的电脑,因为只有这种电脑才可以播放碟片。就这样,我带着我巨大、沉重的电脑,以及十多包电影光盘走进了大学校园,我觉得我就像个行走的碟片库。
大三大四的时候,电驴、风行开始流行起来,各种资源可以在网上观看并下载,舍友买了移动硬盘来装从网上下载的各种资源,渐渐地,我也开始在网上看电影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市面上一些碟片店开始没落了。后来回家,常去的那一代碟片店基本关闭了。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参加工作后,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回家,看到楼下一家小店亮着昏暗的光,走进看才知道是一家碟片店。搬进这个房子不到两个月,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楼下竟然还有家碟店。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曾经淘碟的快乐时光一下子又浮现到了眼前。
店主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阿姨,身边有个小小的男孩趴在收银柜上写作业。这家店并不大,墙壁上的承重架都是用木板打的,整个店看起来也是摇摇欲坠的样子。
阿姨店里的货还是挺全的,除了新上映的片子,还有很多小众的文艺电影,逛了很久之后,我最后找到了岩井俊二的《四月物语》和文德斯的纪录片《皮娜》。整个过程中,阿姨包括那个专心写作业的孩子都没有来打扰我,仿佛店里没有其他人,他们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付钱的时候,我突然有点伤感。曾经的狂热与不顾一切,变成了如今大晚上在这个昏暗小屋子里一个人的掏掏摸摸,淘碟这件事在我心里突然变得孤单起来。我和阿姨互加了微信,跟她说有新货上了记得微信通知我,我也不记得最后阿姨有没有答应。
第二天这家店就关门了,从此以后就一直都没有开过,店铺的卷帘门上贴上了转让的白条。我给阿姨发过几次微信都没有回,后来再打开阿姨的朋友圈已经是一片空白。
在这个年代,经营一家碟片店大概是一件很辛苦又不讨好的事。我想,那一晚,在那样沉默的空气里,她可能在思考着第二天该带着她的碟片去往哪里吧。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