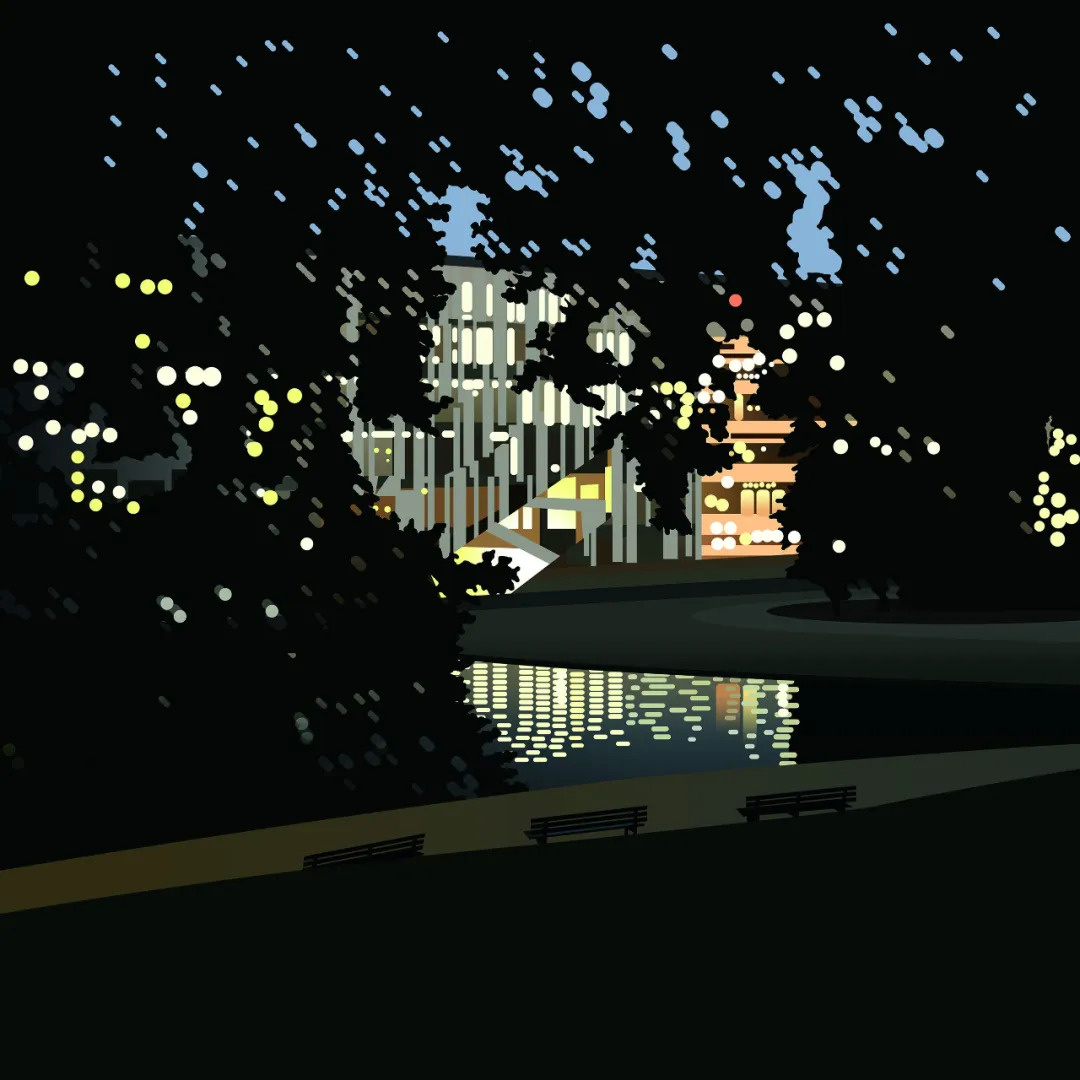
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出没于岩石间的游牧族,
身材矮小,脸画十字的部落
和那些工厂小镇黑暗的早晨里
鹅卵石一样密集的房屋
对于他们,生活就是慢慢死去。
——菲利普·拉金《无话可说》
今天下午我死了
文/插画|田克
天堂就在丰台区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的地下室里。今天下午我死了,他们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地址。我搭地铁来到了这里。
进门之后我填写了一张表格,除了一些个人信息和死前的部分经历之外,他们在“全息体验——昨日重现”这栏的选项里列出了我之前的人生中所有的美好经历——真的是所有的,很多连我自己都忘了,直到读到我才隐约觉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这是一道多选题,我选择的项目可以在稍后再次完整地体验到。这真不错,我确实想再闻闻妈妈那件印满了自行车的连衣裙上的味道,1990年夏天,她每次抱着我,我都浸没在那甜甜的香味中。考虑到我刚死不久,确实没有比现在这个时机更适合重温这一切了。
我坐在舒适的软椅中慢慢勾选这些选项,冷气开得正好,作为地下室来讲,通风也很好。天堂的工作人员穿着灰色制服,来来往往,提供恰到好处的服务。和我讲话时,他们的目光好像穿过了我,看向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被人看着。我喜欢既和某个人交流同时又不被他注意到。不愧是天堂。
关于死后生活的愿景,问卷给了多个选项。我知道我爸曾经选的是哪一个:“彻头彻尾的白”。16 岁的时候,我爸曾给我讲过他的一次濒死体验,他说:“我来到一个地方,周围全都是白的,什么都没有,脚下没有地面,头顶也没有天空。没有透视,没有远近。低下头,连我自己也是不存在的。而且这里一丁点儿声响都没有。”爸爸的表情无限怀念,“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特别的好受。安详,宁静,圆满,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
在我小得还可以带来带去的时候,我爸偶尔也曾试图建设一下亲子关系,又无经验,只好模仿外国电影:带我去钓鱼。外国电影里,木屋外是莽莽大湖,父子俩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父亲小臂结实,儿子笑容灿烂。可是在那些个星期天的清晨,我蹲在水库的大坝上,放眼望去不见一丝绿色,既没地儿洗手也没地儿上厕所,一脸尘土,胳膊晒得生疼。水面的浮标纹丝不动,我和我爸长久地盯着它,心里厌烦着彼此,而且依旧没什么可聊的(当时还不会聊星座)。我盯着自己的鞋,每隔十分钟就偷看一次表。就不该跟他出来,我想。就不该带他出来,我爸想。人都有自我戏剧化的需要吗?还是说人们不知道如何生活,只好模仿电视剧。男人当不成帝王就想做侠客,女人等待王子,不可得就转而套进苦情戏。年轻人希望鲜衣怒马,不劳而获。我爸想做慈祥的父亲,带孩子去钓鱼。星期天的下午,只有我蹲在无聊的现实的堤坝上,埋头盯着自己的鞋。
我爸那次没有死太久,他很快就被长沙市第九人民医院急诊手术室抢救了过来,所以他并没来得及知道那里有没有时间的存在。而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彻头彻尾的白”,体验上一百年是什么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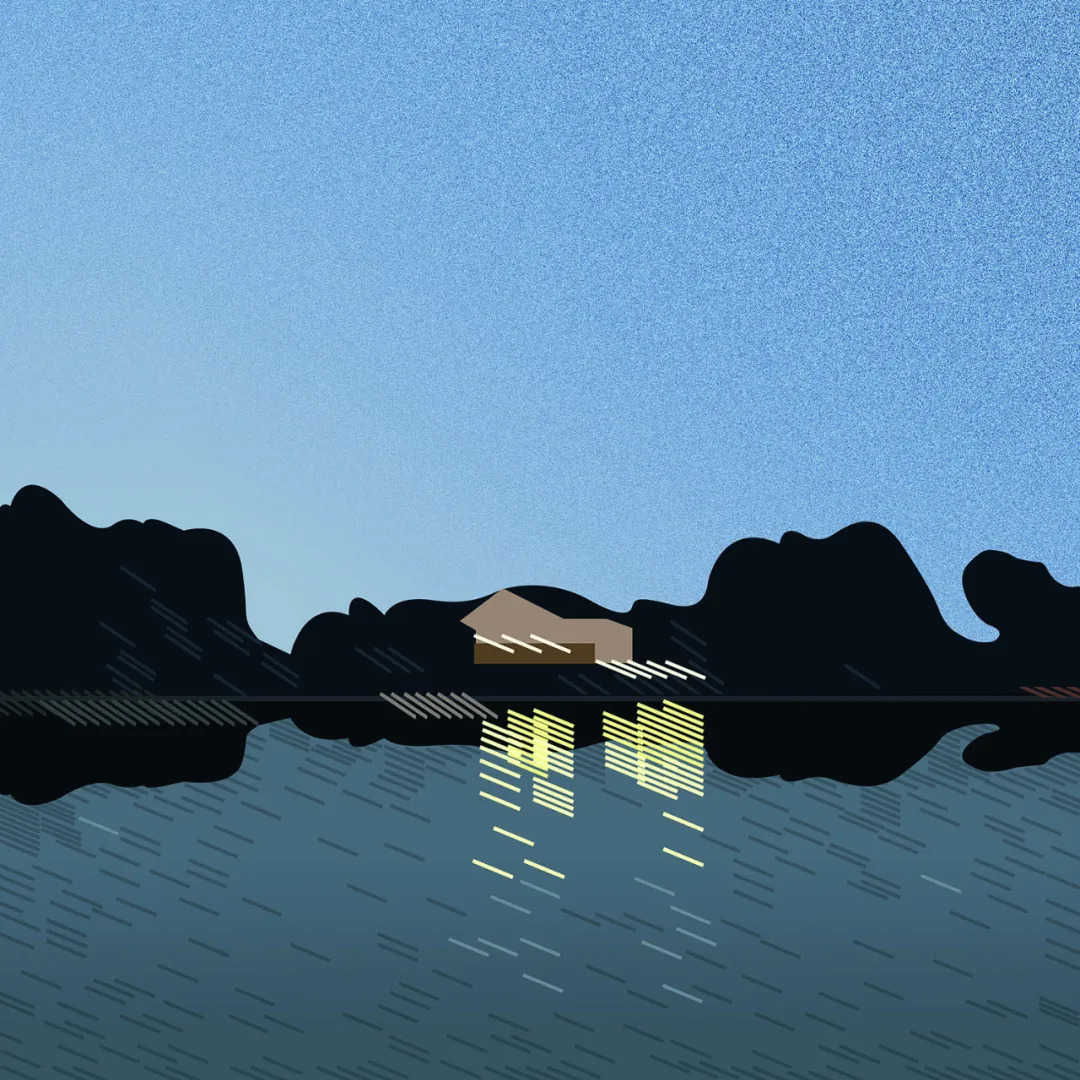
十四五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成为别人。我认识一个别的班的女生 P ,是那种每天放学之后要和其他小流氓站在校门口,等等看有没有人可以揍,没有的话再回家的人。她有一头超短的自然卷,一脸恰到好处的雀斑,拿着新华字典向我普及过肏字的正确写法。她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每次她说自己在做兼职电台主持,有男生为她而死等等这些一听就知道是扯淡的事情时,她自己是那样深信不疑。整个初二和后来的暑假,有时候她来我家,有时候我去她家,有时候我们能连续打两个小时的电话。她始终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那些故事甚至有着不同的结局。我有次在书上读到“叫醒梦游的人会让他疯掉”,我小心地保护着她的故事,一次都没有戳破。在有些厌倦之后,我还是会 Call 她的 BP 机。是谎话又如何,别人根本不像她这样,能编出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她就像自动点唱桑鲁卓,我是乐在其中的国王,我们走在秋天落叶的新华大街上,她会给我唱零点乐队的歌,她的嗓音沙哑,非常能模仿周晓鸥,我还要求她模仿窦唯和高旗,但是没有成功。她出国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络。
后来我又遇到了许许多多说谎的女孩,她们都沉浸在各自形态各异的美梦中,不愿醒来。但是那些次,我没有再爱上她们。
回到手中的表格,我对“资源无限”类型的死后生活也持谨慎态度。很多,更多,更多,更多的更多……多到很快就会精疲力尽。那选择理想生活的模板呢?像罗辑那样在瑞士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隐居,再让政府发个女朋友?最后的女朋友选择了在 QQ 上和我分手。在她之前两周,当时的男朋友也和我分手了,男朋友说和我在一起觉得压力很大,女朋友的留言则更具体一些,并体贴地提供了解决方案:“最近和你在一起觉得压力好大,我们这段时间先不要见面了。”要不是因为这俩人根本不认识,我都怀疑他们是串通好的。
2010年,公司的空调晚上 10点关,公共区域的灯 11 点关。一般到了 12 点的时候我就把工位前的窗户打开,放一点晚风进来。她的消息就是在这时显示在屏幕上的,伴着风里的槐花味。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把它复制到 Windows 的记事本上,放大,继续盯着看。这里面每个字我都认识,但合在一起怎么都理解不了它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是需要一点时间。接下来的日子,我一改工作到后半夜的习惯,每天 9 点准时下班,到单位楼下坐着,盯着在间歇喷泉里面玩的人。我试图消化,理解,理解她,理解我,理解我目前的处境。喷泉升起又落下,我脑中滚动播放着一行字“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根本什么都理解不了。
继续看天堂的表格,我对“资源无限”类型的死后生活也持谨慎态度。很多,更多,更多,更多的更多……我怀疑我有点儿司汤达综合征,好的东西太多我受不了,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可能只有我自己能体会那种感觉,每天都那么好就受不了,累,所以这个选项我也不要。
选择“弥补生前遗憾”作为死后生活方式的人可能是脑筋不好:重新过一遍现在的人生,不过是被自己修改过的。生在首富之家,天生貌美惊人,哪怕什么都不做身材也永远完美,带着这辈子的智慧重新被生出来,拳打变态小学老师脚踢小学同学,看不顺眼的人一个个排着队死了,喜欢的人再没有分开。算了吧,美好的人生也是人生,那可是人间的日子,没有尽头的日夜。

刚刚 28 岁时,我的心态有些微妙,自己终归没能在 27 岁成功死去,并加入 27 岁的俱乐部。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为那些真正做过什么的人准备的,加班加死的也进不去。我的想法也渐渐不同了,原来总想做出自己真正满意的东西,最近已经开始觉得,就算真的做出来了,一切也不会有任何改变。那种快感只会持续 5 分钟,而吃半张比萨的快感大约有 20分钟(吃一整张 40分钟)。我每天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在帮别人清尾货,死去的朋友死去了,活着的朋友在选择月子中心,我努力做过的杂志停刊了,喜欢的歌手老死了,摇滚乐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只有路边咖啡馆里依然充斥着狂想之人,“我要的是那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团队。”一个男人说。“明年我们只接那种一千万以上的案子。”另一个男人说。他们的语气如此笃定,自信,仿佛这时代依然一路高歌猛进。而我呢,怀疑与失败笼罩着我。( 人生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在 28 岁后如何选择生活,没有父辈的经验,也许除了消费,旅游,还有吃鸡胸肉,跑健身房,“二十天养成一个好习惯”,所有教你如何过得幸福的建议都是让你要得更少,往昔的日子像竭尽全力对着空气挥出的一击,它们消逝了,原地徒留气喘吁吁的我。)
如果我随时可以重新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有随时可以从一个选项跳到另一个选项的权利,是不是以后的日子就万事大吉了呢?这样的话,死后的生活可以从在瑞士的一座半山小镇里开始。看腻了阳台上的云雾之后,再选择金手指模式的人生重演,玩到手刃了小学老师之后再跳转到“彻头彻尾的白”,体会那种心满意足,宁静完满。接下来进入资源无限模式,这里可是天堂,JoJo(荒木飞吕彦所著漫画)在这里连载了一万多部,一部更比一部精彩。
“须知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罗素这句话真的管用,它指导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选择。我填完了表格,开始东张西望。周围有一些其他刚死的人,在我的认知里他们是存在的,但我感觉不到他们,他们也感觉不到我。这样真的不错,我喜欢自己确实在人群中又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存在。毕竟是天堂。

田克,创意编辑,视觉编辑,插画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