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周哲浩 鲁舒天 余佩颖
编辑|李墨天 戴老板

2021年开年,农村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横空出世,老戏骨张嘉译发挥稳定,小鲜肉黄轩地气十足,豆瓣分数更是直冲9.4。
原汁原味的方言配音也让宁夏卫视迅速出圈,一晚0.1%的收视率见证了这家地方台的巅峰。观众们被里面那种战天斗地,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精神所感动,电视台也乖巧地把插播广告从微商风的降压表,火速换成了宁夏宣传片,后来索性放起了扶贫纪录片。
《山海情》以及之前《大江大河》的热播印证了一个道理:城镇化狂飙后的中国观众偶尔还是会为优秀的农村剧买单的。在大小荧屏上充斥着五环内的职场焦虑、伦理撕扯、狗血婚姻、商战算计、纸醉金迷的当下,睽违已久的农村总算展现了些许存在感。
曾几何时,农村电视剧是荧屏里的主流供给,农民主题的电影也在银幕上产生过巨大声量,第五代导演们擅长用细小的切口来展开宏大的叙事,这让他们在各大电影节拿奖到手软。而作为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影像里的乡土中国至少部分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变迁。
但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农村题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光明日报曾统计过[1]:到2015年底中国的农村常住人口仍然有6亿,尚占总人口的44%,但在2015年当年,荧屏里的当代农村剧仅有15部和490集,分别占当年电视剧发行总量的3.81%和2.96%。
数据告诉我们:影视剧里农村消失的速度,要远快于我们城镇化的速度。
其实不光是农村,“县城”这个代表城镇化“初级阶段”的事物,也在影视里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中国的1300多个县,在当代影视剧里的出镜频率可能还不如黄浦江畔的大平层高。即使它们在各类摩登时尚的片子里出现,也往往被刻意描绘成愚昧和落后:
在《欢乐颂》里,代表农村县城的是樊胜美那个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在《三十而已》里,是跟江疏影相亲、满口官腔的小镇公务员;在《安家》里,是孙俪那个让她帮兄弟买房还贷的母亲;在《我们都要好好的》里面,是上班时找老乡来雇主家k歌的农村保姆。
新一代编剧和导演们离农村原来越远,新一代观众们也离农村越来越远。在刚过去的这个史上返乡者最少的春节里,人们热议的是:贾玲的处女作,能抵得上喜欢拍农村的张艺谋一辈子的票房;而陈思诚的一部电影,则抵得上喜欢拍县城的贾樟柯十辈子的票房。
所以银幕里的那些县城和农村,都去哪儿了呢?
01.那些辉煌的
上一部能让大众热议的农村剧,还是被誉为“中国村斗剧”巅峰的《乡村爱情》。
《乡村爱情》始播于2006年,目前已经播到了第13部,片中“象牙山F4”(谢广坤、赵四、刘能、王老七)的表情包甚至一度满天飞。尽管剧集本身的口碑早已崩盘,但它的确曾经跟《刘老根》《老农民》《暖春》等一起,维护了2000年后农村剧的些许体面。

《乡村爱情》泰国版海报
喜剧色彩是《乡村爱情》能够出圈的重要保证(大量使用二人转演员),但在80~90年代的农村影视剧里,“喜剧”是一个奢侈品。在当年热播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里,沉重和挣扎是核心词汇。
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恰逢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工进城潮。仅1992年,就有大约4000万农民流入城市打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里,宋丹丹跟黄宏抱怨候车室的乘警叫自己“盲流”:
“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许多人在想象90年代时,都以为那是一个黄金遍地的时代,但往往忽略了城乡结构的变化给中国广袤腹地的普通人带来的影响,“经济吸纳,社会排斥”是进城农民工身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打工诗人”谢湘南在诗里写道:“我从农村流落到城市,多像一只丧家之犬”。
和农民工进城同时发生的是轰轰烈烈又跌跌撞撞的城镇化,身在山西汾阳老家的贾樟柯目睹了到处拆迁的盛况,花了三周时间写了一个关于扒手的剧本,因为总能想起身边的人,贾樟柯说自己当时“边写边笑”,以至于后来反复向人澄清,人物都是虚构的。
这个剧本后来变成了贾导的成名作《小武》,主演是同班同学王宏伟,只不过口音从处女座《小山回家》里的晋语,变成了河南安阳方言。虽然镜头粗糙,演员生涩,但20多年后罗翔老师评价《小武》时说:贾樟柯拍出了他想表达又无法表达的90年代的感觉。

电影《小武》剧照
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三环还没有修好。北影厂所在的三环路边,当年还是遍地的工棚。从山西汾阳来北京的贾樟柯对此情此景再熟悉不过,这位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初衷:“我觉得跟民工有同质性,同样的质感[1]。”
90年代,《黄土地》和《红高粱》渐成往事,中国电影的勾勒的对象慢慢从“乡土”变成了城乡融合中的种种光怪陆离。1992年,完成从摄影师到导演角色转换的张艺谋,用《秋菊打官司》呈现了农村人民的无奈。又过了五年,《有话好好说》成为当年票房的亚军。
这部电影为电影史贡献了两个经典镜头,一个是片子里收废品的张艺谋那几声“安红我想你”;一个是赵本山在里面演了个民工。据说出演之前,赵本山专门去大连皮口体验了一遍生活,结果当地一个服装外贸集团听说赵本山来,特意组织了模特队表演节目。
当时赵本山的主战场还是一年一度的春晚,《有话好好说》上映同年,他把皮口这段经历变成小品《红高粱模特队》,讽刺了一把范伟饰演的城市小资。小品的编剧是何庆魁,他和本山大叔一起合作过《昨天今天明天》《卖拐》等经典作品,主角也大都是农民。

赵本山在《有话好好说》中的客串
《有话好好说》上映一年后,贵州导演王小帅的《扁担·姑娘》拿到了龙标但没有上映,《小武》也只能通过盗版录影带流通。王小帅13岁从贵阳去武汉上学,同学把他称作“乡下人”。在《扁担·姑娘》里,王小帅讲了一出青年农民、“越南姑娘”和“城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片子改到最后,王小帅觉得导演不是自己,而是“那帮哥们儿”。
90年代末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又一轮剧变,商品房改革、大学扩招、国企关停并转,城市与乡村代表的两个平行世界开始了剧烈的交融与摩擦。剧本也随之对准了街头巷尾上演的一幕幕人情冷暖,试图寻找一种对话的方式,但它时而真挚,时而失真。
城镇化往往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在2000年后突飞猛进的“进城”大潮中,人们其实急于摆脱乡土带给他们的束缚,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更有吸引力,《平凡的世界》不再是年轻人的案头读物,郭敬明洋气的小说才是城乡结合部的新宠。
贾樟柯也这样写道:现在汾阳中学的孩子也知道汾中出过一个导演叫贾樟柯,有时候也会谈,但基本上都是不屌[21]。
02. 那些消逝的
世纪初的国产片有两个师父:一个在好莱坞,另一个在香港。
1994年,美国电影《亡命天涯》登陆内地,在城镇普通居民月薪几百元的情况下创下2500万的票房佳绩;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在第二年引进,斩获1.2亿票房;《小武》柏林受捧的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卷走了3.6亿人民币,占当年全国票房的三分之一。
张艺谋曾不止一次地提到,90年代电影投资捉襟见肘,拍不了波澜壮阔的场面,把目光转向乡土,也有成本所限的因素。
中国入世之后,电影业开始高举市场经济大旗与国际接轨。香港影人也在政策利好下分批北上,为内地影视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百废待兴的商业院线里,张艺谋的《英雄》一经公映便狂揽当年票房四分之一的2.5亿人民币,一手将中国电影推入大片时代,也让行业的天平从艺术向票房倾斜。
与贾樟柯一批考入北影93级、后来转行写武侠小说的徐皓峰,做客访谈节目时说,“掌握电影资金的人认为,海外商业片的仿制品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素来不喜欢迎合观众的姜文也承认,电影本来就该展现非分的东西[10],“你要连个火车都不敢劫,实在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2005年,陈凯歌拍了《无极》,贾樟柯拍了《世界》。前者在毁掉香格里拉500平方米林地后收到了环保总局的处罚通知,后者令“汾阳宇宙”首次拿到了获准公映的龙标。在《世界》的导演手记里,贾樟柯写道:“人们能复制一种建筑,但不能复制一种生活。”
《世界》里客串的韩三明,原本是贾樟柯在汾阳老家挖煤的表弟。片中那个意外身亡的民工,贡献了全片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桃姐,你说这飞机上坐的都是些啥人?”
一年后,贾科长的《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天上映,科长想在遍地黄金的年代为好人赌一把,一番求仁得仁,威尼斯捧得金狮的《三峡好人》仅有30万票房进账,被后者的2.3亿完爆。

《三峡好人》剧照
“解放思想”逐渐让位“市场经济”的那些年,《孔雀》拍出了阶层跃升的无助、《迷城》反映了农村大学生的身份焦虑、《天狗》里终于出现村霸、《苹果》聚焦了都市边缘群体,《人山人海》刻画了农民工千里追凶的绝望,成为现实主义黄金时代的绝唱。
银幕追求类型片,观众想看宏大特效和刺激剧本,下面有需求,上面有压力,现实主义题材不可避免的要兼顾艺术与市场。冯小刚摆下《夜宴》的2006年,不满30岁的宁浩拿着刘德华给的300万预算,拍出了2300多万票房的《疯狂的石头》,为黑色喜剧找到了一条夹缝。
海归导演李扬在山西拍《盲井》时,当地势力误以为他们是“管闲事”的记者,直接带人围上了,幸亏剧组有人动用社会关系,才最终顺利完成拍摄[5]。“盲系列”的第二部《盲山》拍摄时,李扬干脆搞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为刁亦男日后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做了表率。
同一时期,跨界资本大量涌入影视领域,产业进一步升级,伴随着热钱激增与资本运作,影视作品形成了家庭伦理、架空玄幻、抗日神剧三条线批量作业。
《捉妖记》《寻龙诀》满载而归的同时,国产银幕成了现实主义的坟场:《心迷宫》豆瓣评分8.7,,导演忻钰坤却说“只想给市场多一种选项”,8.3分的《暴裂无声》也只有6000多万的票房;而尔冬升为横店群演拍了《我是路人甲》,坦言早已做好赔钱的准备。
最惨的是一手培养了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遗作农村电影《百鸟朝凤》在2016年上映时,面对1%的排片,制片人方励在直播中不禁向院线经理下跪。吴导生前就被发行商告知:“市场就看没头脑的,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卖[8]。”
超人撕鬼子,妃子斗皇上的时代悄然而至的档口,编剧汪海林曾调侃过资源造富反哺影视行业的那段时光:“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张猛拍《钢的琴》的时候,一度买不起胶片,以至于很多胶片是从隔壁顾长卫的《最爱》剧组借来的。后来上海电影节给了25万元创投基金,主演秦海璐以出品人的身份慷慨解囊,勉强过关。片子里人工降雪用的泡沫代替,属于正宗的塑料质感五毛特效。

《钢的琴》剧照
张猛生长在辽宁铁岭,父亲曾在铁岭评剧团工作。1970年代,剧团因为买不起钢琴,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架,这给了张猛创作的灵感。电影的原名就叫《钢琴》,“后来我想中间加个‘的’,因为有种分离的感觉,一个钢,一个琴。”
据说2011年上映前,片方一度想换一个“更商业化的名字”,但在张猛的坚持下没有更改。
电影里,下岗工人陈桂林的老婆移情别恋跟了大款,为了同妻子离婚时争夺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的帮助下,用一家废旧的工厂里的钢铁造出了一架钢质的钢琴。凭借本片荣膺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的王千源,是攥着白条登的领奖台,拿片酬比拿奖杯都难。
《钢的琴》没有具体的时间与地点,但观众都能感知到那片时空。在“东方鲁尔”褪色的十年里,城市的繁荣大多只剩下了可以用数字计量的幅员。十年间,那些远去的骄傲、卑微的愤怒和渺小的忧伤不断凋谢,最终散落在一部107分钟的小成本电影里。
电影上映时间是2011年7月,这部成本不到500万元的片子最终以亏损收场。《钢的琴》上映一周后,《变形金刚3》登陆大陆影院,狂揽11亿票房。
03. 那些尴尬的
票房是个你死我活的阵地,你上不去,别人就要占领。
在拍《我不是药神》之前,徐峥的商业片征程前所未有的成功,只是从《泰囧》到《港囧》再到《心花路放》,它们的嬉笑怒骂都跟广袤的中国没什么太大关系。而陈思诚票房及其成功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故事背景有样学样,全部“安全地”放在了海外。
当然,在市场环境下,电影的内容天平必然向票房号召力倾斜。除了少数爱好者,普通观众的确很难被现实主义题材吸引,另一方面,县城和农村背景天然缺乏商业卖点与广告植入,往往沦为艺术小片——在电影院外这么辛苦,来电影院里享受享受怎么了?
去年柏林电影节的“传承中”环节,贾樟柯跟导演霍猛谈到了近年的观察:“中国农村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存在……在国内制片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农村不要拍,没人看;生病的人不要拍,没人看;老年人不要拍,没人看[14]”。
霍猛在2018年拍了一部成本仅为40万元的“乡村公路电影”《过昭关》,讲述了农村老人李长福带着孙子蹬三轮跨越千里看望老友的故事。该片在2019年北京电影节荣获“最受观众注目影片奖”,最终录得票房30万元,差不多是《翻译官》里勤工俭学的杨幂一身行头的价钱。
而在近几年,国产电视剧更是跑步接轨小红书,主角的职业被限定在了医生/律师/CXO级别。前有《谈判官》里的黄子韬“只吃M9牛排”,后有《甜蜜暴击》里送外卖的鹿晗住着带院子的公寓,更有《我的前半生》里咨询公司的普通项目经理住着滨江大平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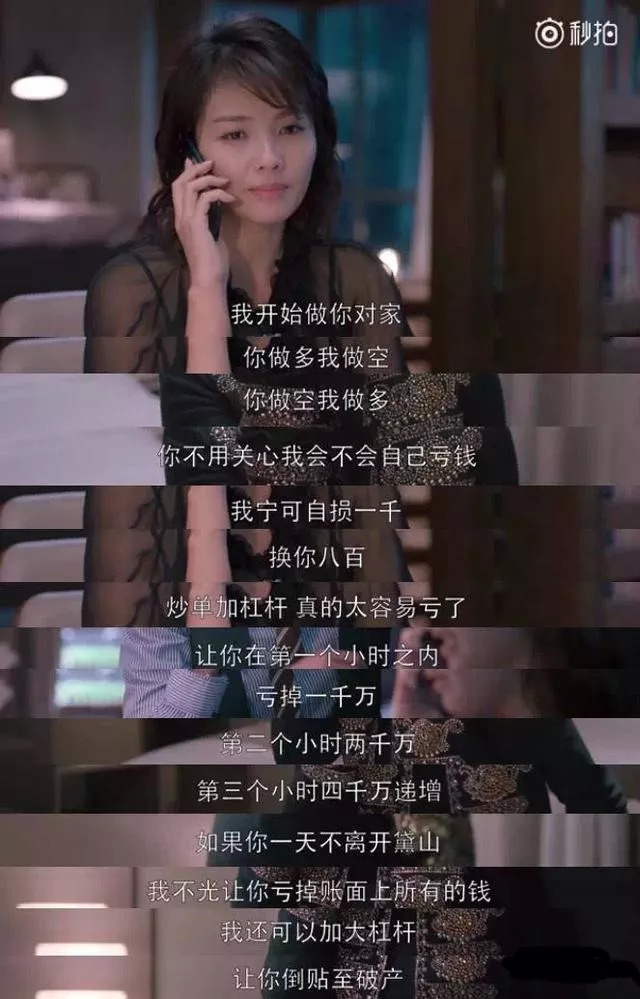
《欢乐颂》名场面
2017年开播的《向往的生活》,明星们来到乡村,白天种地做饭,晚上K歌游戏。人还没到,菜先点上,固定的主持住两月,流水的嘉宾住两天。去年播到第四季,狂揽14家品牌商赞助,在5月新播综艺里一枝独秀[4]。这种所谓乡村生活,跟《乡村爱情》一样假。
深圳大学教授谢晓霞写过一本《在银幕遇见中国》,书中有一段一针见血的概括:诗情画意的乡村不是第四代的忏悔之地,不是第五代古老中国寓言的发生之地,只是都市人怀旧情怀的暂时憩息所,消费和资本逻辑撑起想象的天空[17]。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六代电影人的成长环境大多与农村隔膜,加之电影教育的专业性与入学门槛不断提高,“捏锄头的作家存在,捏锄头的导演几乎不可能[17]”。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与县城为代表的真实中国乡土很少被关注,反而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取而代之。
B站有一位叫农民工川哥的up主,因为喝2元一瓶的农夫山泉被网友质疑身份虚假——“为什么不买1块钱的矿泉水喝”;他双手干净,被质疑摆拍——“农民工的双手哪有这么干净的”;他说自己这辈子没有吃过一盒18块钱的自热米饭,又被质疑在卖惨。
2019年的春节,电影宣传片《啥是佩奇》网络爆红,创意引人入胜之余,一边是被遗忘的乡村,一边是为融入城市话语体系却几经波折的窘迫;城乡间的疏离隔阂,爷孙间的天然亲近,二元矛盾构造的戏剧冲突,让看过影片的人都自发成了宣传员。
但问题在于,这也是一个将乡土符号化的过程,银幕中的农民往往以一个落后愚昧的形象,成为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一个泥土味的喜剧脚本。银幕上的中国乡土,往往只剩下了滤镜式的清新和范式化的贫穷。
19年寻找佩奇,20年入驻B站,城里人没有成为村里人,村里人却在努力成为城里人。全国的“梁庄”都在消失,中国人最厚重的乡情无处皈依,而出走的人却发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路远比想象得要长得多。
贾樟柯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县城与我》。在他的电影里,中国县城是一个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场所,它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又保留了很多尚未褪色的原始和荒蛮。2018年初,贾樟柯借宣传新书接受了北京青年报采访,把1996年到2008年概括为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阶段”:
“我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它让我振荡、激动,我拍《站台》,也拍小武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巨变中他无法适应改变。”
在拍完《三峡好人》之后,贾樟柯觉得自己的创作到了第二阶段,需要把目光转向历史,”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地区差异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我所忧虑或者感受到的是这样一个改革的结果,其实它已经呈现了。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话,要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采访整理成文,刊发时的标题叫:《我们拍电影,用摄影机对抗遗忘》。
04. 那些真实的
2019年10月底,号称国剧门面的正午阳光接受了《山海情》的创作任务,2020年6月备案,8月开拍,次年1月12日开播,播出前一天导演孔笙都还在后期机房调细节。
剧播到三分之一,弹幕里的群众身临其境,算是高度认可了叼着叶子剔牙的张嘉译、灰头土脸的黄轩、讲着福建普通话的郭京飞。剧评文章近来也层出不穷,一篇称《山海情》为“最搞笑最土味扶贫剧”的文章刷出了十万加。
早年拍过《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等西部题材的第五代导演何平,在看过《山海情》后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叙事不再拖沓,演员也不抻戏,对白节奏也快了不少,可以不用倍速看了。”
尽管跟2018年《我不是药神》与《江湖儿女》两盘现实主义大菜比起来,《山海情》多了些宣传的意味,但至少片子里的农民不再是一个脸谱化的喜剧符号,不失为一次对资本“有眼无珠”的打脸。
广袤的中国本应该是文艺作品就地取材的绝佳对象,在一个个跨越崇山峻岭的超级工程之外,还有一个个被崇山峻岭所遮盖的窘迫,以及更多我们尚不知晓的或平凡或不甘或落魄的生活。银幕里虽愈发稀少,现实中却从未远去,只不过更多浮现在社会新闻的边角,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佐料。
当然,尽管面临“叫好不叫座”的窘境,国内文艺工作者们仍然生产出一些“可看”的供给: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坊间传闻不进电影院,却对记录中国不同社会切面的电影情有独钟。2020年,他在家看完400多部独立电影后,给出了个人年度十佳片单。
在这份被称作“看不见的片单”里,大都是农村和县城题材:有关于民间信仰的《游神考》,有讲述农村跨性别者的《湖边散步》,还有描绘国企老旧厂房和半百工人的《岁月如织》,还有《矿民、马夫、尘肺病》这种可以去豆瓣找导演要网盘链接的奇葩电影。
这些电影里的主人公,在我们所不知晓的某些角落里真实生活着。摄像机可以制造欢乐,摄像机也能够挖掘真实,摄像机更应该对抗遗忘。
参考资料:
[1].农村剧为何越来越萧条,光明日报
[2].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程青松
[3]. 电影扁担论文王小帅·漂泊者,孙朋/周雪
[4]. 在欢笑和泪水中选择坚强,海南日报
[5]. 《盲山》前的李杨,读库0703
[6]. 专访焦雄屏:有几位大陆导演,我可能永远不会和他们合作,瞭望东方周刊
[7]. 张猛:坊间孤独电影人,中华儿女报刊社
[8]. 宁浩:我只想反映时代,聚焦
[9]. 制片人为《百鸟朝凤》下跪求排片,新京报
[10]. 圆桌讲究派,优酷
[11]. 为何银幕上农民形象越来越少了,谷雨计划
[12]. 宁浩什么都明白,人物
[13]. 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剥洋葱people
[14].《山海情》将播,孔笙谈创作过程:太不容易,澎湃新闻
[15]. 贾樟柯: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年轻导演的新创作,腾讯网
[16]. 《向往的生活》如何成为品牌方的香饽饽,澎湃新闻
[17]. 拍了三个月节目桐庐小山村变身“新网红”,杭州日报
[18]. 在银幕遇见中国: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谢晓霞
[19].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吴晓波
[20]我们拍电影,用摄影机对抗遗忘,北京青年报
[21]县城与我,贾樟柯
[22]看不见的影像,张献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