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联网指北
正如科马克·麦卡锡在《天下骏马》中所写——“世界对生活在其中的男与女、老与少、贫与富、黑与白,对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荣辱贵贱、乃至生老病死更是一概不闻不问”——在当下中国的互联网语境里,“东北”已经无限类似于那个年代的美国西部:
游离的现代文明、殖民统治的遗迹、电视里经常看到熊与猛虎出没的新闻,人与自然共同构建了一幅落寞的文化景观。
东北人似乎并不反感被摆在橱窗里供人凝视,快手、低房价、体制内、烧烤、搓澡……他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后代离开东北,也确实很热爱这种土味罗马式的生活,热衷于传教士般地将这种生活方式完整地移植到新的聚居地。
以至于当“社交牛逼症”在2021年9月忽然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这个词条很快就和“东北人”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在微博热搜词条“东北人自带社交牛逼症下”,能刷出数万条当代马可波罗来到东北、或者与东北人深度交往后的惊讶体验:
原来在烧烤店,不认识的两桌可以随意凑到一起,瞬间升级到肝胆相照的关系;原来洗浴这么私密的事,在东北居然可以成为一种社交,甚至人的身体可以被搓澡师傅随意摆弄,仿佛误入伊甸园;原来等红灯时,东北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摇下车窗,问你的车“全下来得多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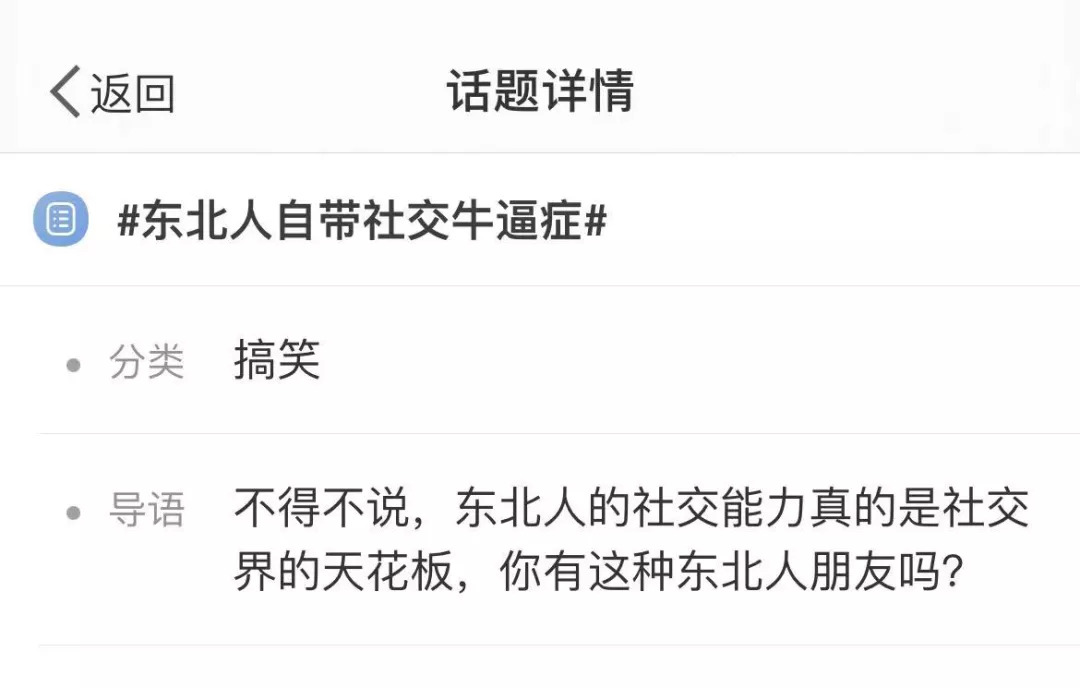
但东北人对这个名誉的不拒绝,对应着的不是骂名,而是被遗忘。

其实关于“社牛”这件事,在网上享有的并不仅仅是“搞笑”这个标签。有外地人惊诧于这种与人交际的随意,有人则直接将这种“随意”上升为“缺乏边界意识”的落后表现,认为个人空间和社交选择权是件必须用藩篱捍卫的,否则会轻易被剥夺的东西,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担忧充满了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命不凡,更表现出来其认知上的简陋。
因为东北人不仅与人交际没有边界,与鬼神和天地同样如此。
一百多年前,那些从关外朝着柳条边走的拓荒者,满脑子旋转着农耕乌托邦幻想:山林璀璨,红松白桦五光十色;江心上渔船如织,鱼虾欢快跳跃;沙洲上盘旋着成群的大鸟,芦苇里野鹿奔跑;脚下的黑土地肥沃得仿佛能踩出油花,年夜饭有吃不完的饺子。
但事实上经历九死一生来到这里后,他们发现如此广阔的平原,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适宜的生存空间。往上走,是沙俄的兵营,往下看,是日本人修的铁路,硬进林子里,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黄皮子迷了去。找块没人管的荒地,种上几百垧的高粱大豆,所有人拿出在老家的本领,盖房子、磨豆腐、烧酒,百里间炊烟升腾,才渐渐有了人间的样子。
很多人就是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彻底安顿下来。但他们始终知道自己是外来者,在东北几乎看不到任何宗族祠堂,因为移民文化的本质,就是拜码头,这里是黄鼠狼和狐狸的地盘,所以萨满仪式的主角,永远是森林里的动物。
有人烟的地方,就有生老病死,就需要仪式。
我曾观摩过一次萨满表演,农家老人得了重病,得找大仙看看,大仙是个精瘦的中年妇女,她走到炕头前,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便开始击鼓唱到:“脚踩地,头顶着天。迈开大步走连环,双足站稳靠营盘。摆上香案请神仙。先请狐来,后请黄,请请长蟒灵貂带悲王。狐家为帅首,黄家为先锋,长蟒为站住,悲王为堂口。”
炕上的男女认真听的,会露出看恐怖片时的惊悚神情配合大仙的表演,但大多数人,就是借着三分醉意权当看二人转解闷。即便面对生死疾病,大仙的唱词里还有狐仙往男人被窝里钻的剧情,来讨得炕上醉汉的嬉笑,以期多挣个三五十块的赏钱。
我从未见过如此卑微的祭司。

(二人转里的“神调” 就源自民间跳大仙)
后来听说,这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大仙,是因为有人看到她半夜爬到房顶,体态似禽又似兽,用东北方言说,她被“出马”(附体)了。
这样的异人理应交给卫健委,但东北人却习以为常,大家心知肚明:她只是想找个当大仙的活计而已。
当出马仙,出一次活公价是五百到一千块钱,有人多给有人少给,全凭表演状态如何,和乡下的婚礼司仪相当,算是个俏活儿。自古以来村民与大仙的关系,就属于“一把一利索”,给钱办事,办完走人。
移民的精神谱系里,没有不容消解的神灵,蛇鼠鬼怪、奇人大仙其实和单位领导一样,你牛逼是牛逼,但只在我用得着你的时候才算你牛逼,而且用你的时候你得给我整明白的,要不然不好使。
在全人类的巫术文化里,能保留如此清晰自我的,恐怕只有东北人。

当然如今的东北萨满文化,在流行文化里正在被重新定义。在《鬼吹灯黄皮子坟》等影视作品中,一切都被赋予了不可知论色彩,大兴安岭、穿着皮草的东北人、甚至那些不会动的房屋墓地,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怪力乱神的“他者”,唯一的任务是展示奇观。
但你若真给大仙一部手机,大仙还给你的可能不是你期待的灵异视频,而是一段水平远超大碗宽面的神调喊麦。你觉得土味视频没格调,大仙会觉得你太能整景。
天下霸唱们施加给东北萨满的故事,也许并不是东北人自己想讲述的。

东北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走出乡村,城市里的生活也未必如宣传画般理想。
比如近来关于东北的文学,都离不开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作家写下岗,是非常讨巧的路数,这里有足够多的戏剧张力,也有充沛的苦难奇观。男人下岗后,醉酒死在雪堆里;女人下岗后,去按摩房做起了皮肉生意——就像前不久热播的《双探》《再见那一天》,还有文艺青年们热衷的《钢的琴》——这样的故事在流量至上的时代,真假有时还挺难辨。
其实无论南北中外,对于卖力气的劳动者来说,艰难与误解,本就是生活的常态,想走出困顿,想保持热情,必须与自我和解。
东北城市里四处可见的洗浴中心,已经被无数公众号描绘成了裸体嘉年华,过时的奢华、夸张的服务、还有一些暧昧的想象。等走进去才发现,大多数洗浴中心并不是声色犬马之地,一年有恨不得五个月冬天的地方,大家就是很自然地想找个地方暖和暖和而已。
“皇家公馆”洗浴中心,听名字就有一种属于上世纪的酷,俗不可耐,但令人神往。其实里面很简单,无非就是一泳池的温水和二十平米不到的蒸汽室,楼上有电影厅,屏幕里常年放着《战狼》,沙发椅上有几个醉酒的大哥打鼾。
按摩可以找,但六十块钱就捏脚属实有点犯不上,还是二十块钱搓个澡比较合适。
外面天寒地冻,浴室内奇热无比,搓澡的张师傅带干不干五六年了。他喜欢一边给客人搓,一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触得到的惬意,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敞开心扉。
张师傅年轻时,赶在工厂倒闭前就去了南方,掌权者尚未扣动扳机,他就已经逃出了射程,算是幸运儿。他去珠海批发服装和BP机,倒腾回吉林卖,确实挣了不少钱,成了大款的他,是让所有下岗工友眼红的偶像。
“我们的青春就要开,往哪开,往理想里开。”
但儿子上小学那年,突然流鼻血不止,去医院被诊断出了白血病。张师傅做生意攒的钱全拿来给儿子换了骨髓,爱去舞厅的媳妇决定抛弃这个返贫的破家,去了韩国打工。
“你们年轻人找对象不能学我,得找个过日子人。”张师傅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沉重。
为了供儿子上学,他在菜市场卖过血肠、蹬倒骑驴送过煤气罐、甚至当过日结工资的装修力工。那个年代的东北,工人出身的男人如何与失败的人生共处,是一门必修课,不及格的会被赌博和酒精绑架整个人生,而张师傅,属于坚决不服输的。
今年儿子高考,考进了吉林大学,他一边给我敲着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再干四年,儿子上班我就不干了!”
搓澡的时间一共不到二十分钟,但我能在这二十分钟里听完一个男人完整的一生。如果有闲心,我还可以站在旁边的淋浴下,听他跟下一位客人再讲一遍。
没有客人会想起用“社交牛逼症”这个词来形容他,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此刻达成了奇妙的平等,张师傅说起愤恨处时,客人们也会附和着骂脏话;他说起儿子的高考成绩时,客人们也会跟着啧啧赞叹。
赤身相对的浴室社交里,人们都展示出了足够的优雅和耐心,衣服脱下了,才看得出东北男人都是绅士。
按理说人不应该如此随便地描述过去的时光,中老年人说起过去,往往会想象并渲染自己的独立与勇敢,我见过有老人回忆动乱年代自己的坚守:“他们都打老师,就我没动手。”
但实际上呢?谁也不知道,谁也没看见。但他这个岁数说出这番话,最起码出自他此刻真诚的正义感,换别人到那个岁数,未必有这种认知。
与人社交时,尊重当下的良善,确实是个很牛逼的优点。与其说这种与陌生人交心的能力是社交牛逼症,不如说是我们面对人生波澜的敬畏与温情。
而且现在的东北人也是很缅怀这种集体记忆的。至少在现在的东北文艺作品里,爱唠闲嗑的澡堂子员工从来就没有缺位过。老四不演老丈人、小媳妇、上门姑爷那一套之后,首选的就是吆五喝六的澡堂子大堂经理。赵本山的徒弟田娃得了老师的真传,底层小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然后把洗浴中心服务生这个形象带上了辽宁台春节晚会小品。
没有这种不可名状的共情,事情很容易变得麻烦。试想一下,如果他模仿的是公务员,恐怕会有带编制的年轻人上网狂怒,然后演员会发出一篇措辞工整的微博道歉。
真正赤膊讨生活的人,反而更豁达。这不是假设。我不止一次在洗浴中心的门口看见服务生反过来模仿小品里的台词,他们被调侃、被当作笑料,却满不在乎。
这种豁达,其实是在把姿态降到最低,姿态降到最低了,以便随时酝酿出反击。尊严和底线一旦被践踏,他们会让所有人知道什么叫“不好欺负”。
觉得劳动者和善便产生欺侮或调笑的兴致,是最愚蠢的傲慢。江湖人眼中世界运行的规律,和社会法则并不完全平行,在消费场所,有钱有权的大人物被整成小丑的事,并不罕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值得叫上一声牛逼。

其实“社交牛逼症”看起来更像是某个市场部脑暴出来的成果,因为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它巧合地拥有着互联网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特质:个体行为是频繁的、个体又是无法独立完成的、个体行为是积极寻求外在互动的、个体是可以自我产生驱动力的。
按照这种造词逻辑出发,很多的事就很好解释了。比如为什么“社牛”一诞生就很快联系到“东北人”,因为足够常见且拥有“个性鲜明”和“天南海北”的二象性,天然地适合市场部用行业话术进行进一步翻译:活跃度高但个性化需求没有被洞察,私域流量效应明显,裂变传播配合度高——上一个被这么形容的群体,是六环外跳广场舞的大妈,而众所周知,中国没有几个城市修到了六环。
“社交”这个词的含义也在这轮“社交牛逼症”的观测里坍缩,它变成了唠嗑、处对象、拜把子、讲段子,变成了“如何主动和对方产生语言上的互动”的一门很像PUA的学问——区别是结果是积极的,要么最终成为UGC内容沉淀在内容社区里,要么真的让当事人获得了一段不错的友情或者爱情。
也可以换句话说,“社牛”和东北人没关系,更和东北人理解的社交没关系。
社交是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体制、人与权力的关系,是人作为个体怎么定位自己在整体中的角色。
东北人社交牛逼症的另一面,就是对所处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准确把握。在面对冰冷的铁幕时,起初是不情不愿地敷衍,但说不上什么时候,匹夫之怒喷薄而出,掏出家伙就来一下,给你们留个不好欺负的深刻印象。
无数的“你瞅啥?”“瞅你咋地!”的争斗背后,都是这种底层逻辑。
世上的事,本来就有一套法则,无论在吉林还是纽约,一加一肯定都等于二。但从历史的基因到现实的变迁,都让东北人不得不学会放下偏狭和执着,成为可爱又不软弱的实用主义者。
你管这叫社交牛逼症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病也罢,随意。松花江从不结冰,见惯了流水的人,会觉得沉稳和静止是虚幻。生活本来就是不断增益的过程,多交一个朋友、多唠两句磕、多整一点事和多种一盆花、多修一条路一样,都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社交是手段,不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是自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