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乐乐
近期的张杨频繁进入公众视野,跟他的电影《皮绳上的魂》有关。
这是第六代导演张杨自1997年以来的第九部电影,在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入围了最佳电影金爵奖,斩获了最佳摄影奖,并作为7月份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再次被放映。
一部酝酿十多年的片子
《皮绳上的魂》在上海电影节首映之后,受到了很多影评人的好评,有人说张杨终于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
他自己对这部片子也相当满意。张杨说他在《皮绳上的魂》中彻底过了一把叙事的瘾,这一次他不用再考虑市场和票房,创作进入从心所欲的状态。因为拍片的缘故,张杨在西藏呆了一年,他借此蓄起了中分长发,颇有大学时期玩儿乐队时的张扬与自我风范,但又多了份淡然,成为他现阶段醉心艺术片创作的外在注脚。
《皮绳上的魂》创作动机由来已久。1991年张杨去西藏旅行,便萌生了要拍西藏题材电影的想法。后来他看到了扎西达娃的先锋派小说《西藏——系在皮绳上的魂》,被其强烈的魔幻现实风格吸引,开始着手改编。2007年张杨就联合原小说作者扎西达娃完成了剧本改编,为了寻找剧本里“莲花生大师掌纹地”的理想拍摄地点,他把西藏跑了个遍。但胶片电影时代,在西藏拍片是个疯狂的举动,时间和成本代价都太大。
直到2014年,他们可以用数字化摄像机拍了,设备变轻了,灯光量也变少了,扎达土林(电影《皮绳上的魂》拍摄地)也不再是往返需要15天的闭塞之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
他用一年拍摄了《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两部关于西藏、信仰和朝圣的故事。张杨称,在这两部电影中,他试图做一些关于电影本体的探索和讨论,“跟过去的拍摄方法完全不同,有种从头做起的感觉”。
通过这两部电影,张杨尝试了两种极端相反的电影风格。
《冈仁波齐》是一种纪录片式的剧情片,具有很强的真实感,“不需要什么花招,就是平静地观察记录,一样可以成为好电影”。张杨说,拍《冈仁波齐》的时候,他会跟纪录片的主角们边拍边聊边改,“那是一种特别奢侈特别幸福的创作状态”。
《皮绳上的魂》横向展开了杀生者、复仇者和写作者三条线,通过复杂的结构和时空交错来讲救赎、信仰和复仇的故事,同时交杂了西部片、公路片等多种风格,“用这种结构讲故事对我来说非常过瘾”。

张杨的贪心与多面
但拍这两部电影之前张杨一直处在焦虑中,焦虑于没有明显的风格,焦虑于做的商业电影背离了自己的创作意图,焦虑于没有自我超越。
以前的张杨是个有点儿贪心和多面的人,你甚至不能用一种明显的风格去定义他,既拍商业片也拍文艺片,既可以特别商业化,又可以相当地自我。“我的电影比较杂,喜欢的类型和导演有点儿多,没有很早确定自己的风格。”张杨因为缺乏辨识度也焦虑过,“当你一下抓住某种特别准确的风格,辨识度就有了”。
因为从小生活在北影厂大院,小时候的张杨看了不少电影,从革命主旋律电影到各国电影展。他的父亲是知名导演张华勋,张杨曾经有过跟父亲的剧组《神秘的大佛》、《武林志》全国转景的经历,“剧组是个大染缸,特好玩儿”,打小的这些经历在张杨看来当导演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戏导演系毕业后的张杨做了一段时间父亲的副手,但父子间固有的代际矛盾和艺术理念的不同,使得张杨对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摆脱父辈的权威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从踏入电影圈开始,赢票房和拿奖对于年轻的张杨来说看起来尤为重要。
从1997年执导第一部影片《爱情麻辣烫》起,张杨接下来的4部电影都跟一个名叫罗异的美国制片人绑定在一起。1996年美国人罗异创建了艺码电影公司,挂靠西安电影制片厂。罗异担纲制片人,扶持新导演,与当时还是新人导演的张杨建立了一种市场化的合作机制,脱离了当时主流的国营电影厂生产体制。这一对黄金搭档在商业与艺术,中国题材与世界表达上做得尤为成功。
在《爱情麻辣烫》里,张杨试图以商业电影的类型来操作都市爱情题材,通过一对正在筹备婚礼的情侣遇到的5段不同年龄段的人的爱情状态,来展现爱情与时间的命题,从初恋美好到热恋缱绻到中年危机和晚年相守,张杨想在一部电影里将他所理解的爱情全貌呈现给观众。这部由高圆圆、徐静蕾、濮存晰等人参演的电影,集结了当红明星、热门题材和金曲配乐,投资300万却在内地创下了3000万元的票房,张杨也通过票房和市场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你获得了拍片子的权利和通行证的时候,就会想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而且越往后,这方面的诉求会更强烈。”此后的张杨在他的商业片中逐渐强化了自我表达和艺术表达。
这种强化一方面体现在题材的变化上,张杨开始聚焦父子关系,并把这个命题放到了更加具象或边缘的人身上。《洗澡》从要不要继承父辈集体澡堂经营入手,呈现代际隔阂和社会变迁;《向日葵》则从父亲将人生理想强加给儿子入手,展现中国式父子冲突与和解。
另一方面,张杨开始尝试更加个性化的电影语言,其中《昨天》以伪纪录片的形式,邀请贾宏声和他的父母亲自出演,再现了贾宏声戒毒时期的黑暗与孤独,同时又经常以旁白的形式切断主线叙事,在舞台剧空间和电影时空的切换中探索真实与虚构,具有强烈的作者电影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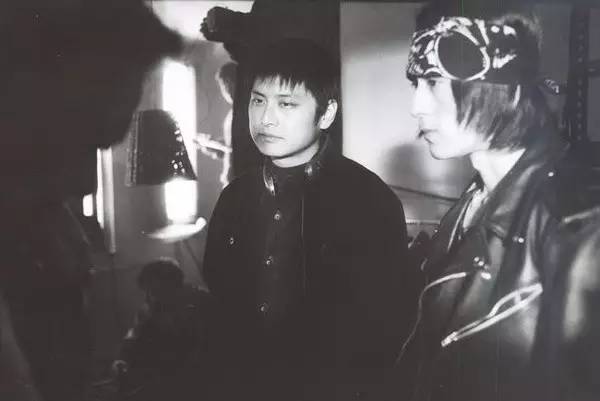
张杨的焦虑与转型
2007年以前的张杨没有彻底文艺,也没有彻底商业,在两者之间摇摆的他相比同辈导演,辨识度要差很多。他也并不高产,即使拍商业电影,也要自己操刀剧本创作。“别人拿给你一个剧本,你会觉得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拍自己内心长出来的东西。”
从2007年《落叶归根》开始,张杨试图以黑色荒诞风格讲述赵本山饰演的一个农民工背工友的尸体返乡安葬的故事,影片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奖。
但到2012年仍想延续黑色荒诞风格的《飞越老人院》,仅仅拿到了525万票房,张杨说自己在《飞越老人院》中走偏了,因为过多地考虑市场效果,背离了他想要的荒诞风格,走向了肤浅的感人和煽情。
这其中2010年的都市爱情片《无人驾驶》是张杨所有电影中唯一一部没有参与剧本创作的,张杨对于它也不想多谈。在他看来,商业电影是一个工业化的组装过程,导演做的只是执行层面的东西,在这其中没有进步对他来说是件可怕的事。
被商业牵制的创作给张杨带来了巨大焦虑,2012年到2014年之间,张杨移居大理,让自己停了下来,重新考虑电影风格和自我表达。之后张杨决定彻底告别商业片,拥抱文艺片,将筹谋已久的西藏题材提上了创作日程。
现在的他经历了文艺片《皮绳上的魂》创作后,已经不再焦虑于风格,市场也不再是他要考虑的因素,“拍东西最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表达自己”。张杨说,他们那代人更偏理想主义,玩儿摇滚、排话剧、拍电影,都是为了自我表达。
张杨也褪去了早期的商业属性,除了任职和力辰光的艺术总监之外,张杨没有入股或投资任何公司。“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自己更自由,公司这样的事儿对我来说太麻烦了。我又不拍商业片,也不在乎多卖1000万或500万。”
从500万到5000万,只是渠道问题
但《皮绳上的魂》如果公映,如何收回投资成本是张杨背后的投资方需要考虑的问题。艺术电影在国内院线的遭遇普遍是500万票房,而且这种体量的票房还是建立在通过电影节获奖及宣发充分造势的基础上。三声注意到,像《冬》这种没有光环的电影,据艺恩数据显示只有29.6万线下票房。
“艺术片的观众是大量存在的,《百鸟朝凤》最后卖了8000多万,它是个孤立事件,但它告诉我们,艺术片至少存在5000万票房的观众群。从500万到5000万的十倍增长,这是个渠道问题,渠道不畅通就是500万,就像《路边野餐》。”张杨说道。
他告诉《三声》,《冈仁波齐》投资了1300万,《皮绳上的魂》投资1700万,背后的投资方为张杨多年的好友李力的和力辰光和由李力拉来的乐视影业。相对艺术电影来说,这两部电影算是中等规模投入,但在市场中的命运目前来说仍旧前途未卜。
这两家公司在营销和发行实力上闻名业内,其中和力辰光一手打造了“小时代”系列粉丝电影,乐视影业在国内影视公司的发行实力也稳居前列。背后有这两家公司的包底,张杨却说他不关心市场了,“我不在乎多卖或少买500万或1000万”。这其实是一种无奈,一个具有强烈表达意图的创作者,也有强烈的欲望为自己的电影找到更多有共鸣的受众。
张杨说,他认为国内艺术片市场远没有成熟,《山河故人》和《聂隐娘》的票房分别只有3000万和5000万,“这个体量太小了!”。
“艺术片院线发行本身是个不成熟的网络,其中渠道不畅通是关键症结所在。”张杨说的渠道,涉及从本该存在的分线制院线系统到政策对艺术片的支持力度,“这是一个系统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不单单是资本挤压排片的问题。”
这句话背后的现状是中国电影市场艺术电影与商业市场之间的互斥。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开始涌向商业片、类型片和网剧的拍摄中,“像毕赣这么年轻就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语言和偏好的在青年导演里少之甚少”。
在2016年票房冲破600亿的大跃进中,院线市场因为缺乏优秀片子,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张杨说,他也觉得最近的院线电影太乏味了,除了刚看过的《路边野餐》,今年几乎没去过电影院了,“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片子”。
三声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授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