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丽贝卡·特雷斯特
翻译 | 贺梦菲 薛轲
2002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向读者建议:“请你们听一听成功女性如何谈论自己未能生育的事,当中充满了悔恨和遗憾。”言下之意就是女子未能生育便是失败,这种一概而论的假定在我们阴魂不散的性别身份观念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许多成功女性并不这样认为。
“要是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一定会怨恨我。”奥普拉·温弗瑞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可能会在另一个类似《奥普拉》的节目上说我如何如何;因为(我的生活中)肯定会有人受罪,而且受罪的很可能就是孩子。”
温弗瑞似乎理解,并非每个女性都有同样的做母亲的愿望。她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她的好朋友盖尔·金作了比较。她说盖尔·金“就像一个七年级的孩子,在家政学课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孩子们的名字。在她梦想着生儿育女的时候,我在梦想着如何成为马丁·路德·金”。

2009年美食广播网明星瑞秋·雷在记者辛西娅·麦克法登问到她“曾经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忙得没有时间要孩子’”时解释说:“我今年40岁了,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瑞秋和温弗瑞一样,认为把工作责任让位给育儿是不可思议的。“我对待我的狗狗无异于一位好母亲,但我无法想象如果这是一个小孩会怎么样,而且,我真的不想……我无法想象有人给我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假去生孩子,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这样不仅对孩子不公平,对我的同事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很少有人承认,女性可以通过无数的办法在这个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生儿育女长久以来都是女性生活的首要原则,生育状态往往被认为是女性身上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而这掩盖了她们身上的其他兴趣点。伊冯·布里尔是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火箭科学家,她发明了能使卫星保持在正确轨道运转的推力机制,但是2013年布里尔以88岁高龄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是这样描述她的:“她的俄式酸奶炖牛肉堪称一绝,随着丈夫的工作搬迁,有长达八年的时间,她放弃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三个孩子,她的儿子马修说‘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这段文字出现在整篇悼文的第一段,接下来才是对她一生科学成就的介绍。
没有孩子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无论是谈到孩子还是事业,都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你想要孩子吗?你打算生孩子吗?没有孩子你后悔吗?2013年《嘉人》杂志给33岁的女演员佐伊·丹斯切尔做人物专访,在记者问她是否会优先考虑生孩子时,她回答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是生气你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曾经说过,你们不会问男人这样的问题”。
他们确实不会问男人这样的问题,即使问了,也没有人奇怪听到对方说他们要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因此不要孩子,他们肩负各种责任,心怀各种理想和抱负等等,也不会奇怪听到他们说有了这些就可以心满意足,没有孩子又有何妨。但是,难道女性就没有理想和抱负,女性就不能从孩子以外的地方得到满足吗?网上有个帖子叫“多萝西·海特的女儿们”,发帖者罗宾·考德威尔这样描述这位刚刚去世的传奇民权领袖,“多萝西·海特终生未婚、身后无嗣,对于有些女性来说这可能是奇耻大辱,但是对于我和其他庆幸世界有这样一位民权活动家、女权运动领袖的人来说,她留下了无数的女儿”。
2015年,《欲望都市》主演金·凯特罗尔在被问到她没有孩子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指导年轻的演员,我有和自己非常亲近的侄子侄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无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孩子的出生证也同样可以为人母。你可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母性的一面,很有满足感”。

凯特罗尔和考德威尔并非是最早说出这样煽情话语的人,在她们之前还有单身君主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这位君主在议会一再要求她结婚时回答说:“我恳请诸位不要责怪我没有子嗣,因为你们中的每一位,以及英格兰的每一位子民,都是我的孩子和亲人。”“在我过世之后,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取代我成为你们的母亲,然而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更愿意成为你们所有人的生身母亲。”
即使没有孩子,女性仍然肩负各种责任,包括对其他人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以及对别人家庭的责任。
20 世纪70年代,有十分之一的美国女性未曾在育龄期生育孩子。2010年,这个比例将近达到五分之一。在增加的人数中约有一半是想要孩子却未能在生物钟滴答完之前及时找到生育的途径,另一半则是因为有别的生活模式可供选择而放弃生育,至少她们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历史学家露易丝·奈特曾说,她和她的一些调查对象,创作与写作的动力大大超过了生育的动力。“有一种真实的情感需要表达出来,那是她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东西,”她谈到简·亚当斯和萨拉·格里姆凯时说,“我理解对于有些女人来说,那种东西就是当母亲的愿望。但是我的内心并没有这种愿望,如果有,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奈特解释说:“她的意思并不是说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就没有表现自我的欲望,“而是她们的激情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奈特回忆起她7岁的时候,看着她妹妹玩婴儿车和布娃娃感到非常不解,就想,“为什么要这样呢?”她说:“但是单身状态使我这样的人获得了解放,如果不想要孩子就无需假装渴望有孩子”。
不仅是奈特这样的未婚人士感到了解放,那些结了婚但不想生育的妇女,也获得了释放。互联网上有无数的网站支持爱侣们主动选择不要孩子的想法。新闻记者皮珀·霍夫曼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她曾经写到她和丈夫如何逐渐意识到两人都不想为了孩子而放弃自己的工作,尽管他们这样做面临着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巨大压力,因为他们都虔诚地信奉犹太教。她说发现有这样的群体后就像解放了一样,那些人也像她一样“没有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动力”,而且都非常幸福。“他们说了没有孩子的种种好处,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和所爱的人过着二人世界,培养忠诚的、有满足感的伴侣关系”。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告诉我说,经常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没有孩子,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印度一个贫民区的妇女中心里,“有人问我说,你不后悔没有孩子吗?当时我想这地方的人思想非常传统,我若是如实回答就会失去这些听众,但我又转念一想,说假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就如实相告,‘一点也不后悔’,没想到她们竟然鼓掌了。因为对她们而言,生孩子是迫不得已的事,所以她们很高兴有人可以不用生孩子。”

不用生孩子的自由!这种真切的自由,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罗斯·多赛特在他2012年《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请再多给我们一些孩子》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回避生育是后现代疲劳的一种症状。这种颓唐的状态最早出现于西方,目前正在全球的富裕社会中徘徊……这种精神让人们信奉现代化带来的安逸与享乐,而忽视最初构成我们文明时所需做出的最基本的牺牲”。
当然,一些人所说的“颓唐”正是另一些人的“个性解放”。令多赛特如此困扰的生养疲劳,也是那些已育有孩子的女性感到的倦意,她们直到最近都还是独立抚养孩子,正是她们做出了“最基本的牺牲”——牺牲了个人认同,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牺牲了对公平平等的追求。
虽然女性可能已将伴侣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双方所做的牺牲也更加平等,但是不管从生物学上来说,还是从依然围绕男人挣钱、女人造人而设计的社会政策来说,女性还是得做大部分的“算术题”:有了孩子之后工资、晋升机会的得失、风险和回报,有没有病假和休假制度,有没有泵奶室和两边靠窗的办公室。即便选择生育孩子,女性还是非常在意这些得失的。
“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失去生育的能力,”安·弗里德曼这样写道,“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失去在职场上的权力。”歌手凡妮莎·卡尔顿对记者杰达·袁说起她的人生导师史蒂薇·尼克斯解释她在玩摇滚的年轻时代,为什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母亲。“她说:‘我希望那个舞台上的每一个单身男人都尊重我,如果我半途而废做了那样的选择,一切都将不同。’”
* * *
据估计,在40至44岁没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并不是自己选择不要孩子,而是没法选择。梅兰妮·诺特金在她的《生活在他处》一书中讲述了她所称的“条件性不育”,她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单相思”。对于像诺特金这样的女性来说,没有孩子不是自己的决定,也绝不是她们想要的生活。“我们没有伴侣所以没有孩子,但总是有人误解我们,以为我们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选择,这样的误解令我们更加伤心。”她这样写道。诺特金说,渴望有孩子而自己没有孩子的女性,她们“有许多孩子”:“我们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孩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我们的侄子侄女,我们朋友的孩子”。
有些女性没有孩子既不是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什么偶然的原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复杂原因导致她们无法生育。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喜欢别人的孩子并不总能产生满足感。这些女性并非没有考虑过单独要孩子,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不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华盛顿的小说家艾略特有一个女性朋友,38岁仍然没有和任何男性交往,心情非常焦虑。艾略特写到她们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她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结婚建立家庭,但是她算了一下,感觉(一个人抚养一个孩子)绝无可能。她是老师,每个月的收入只够勉强维生”。艾略特搬到华盛顿离她的两个侄女更近一些。她说,她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接受了将来自己不会要孩子的事实,从经济和情感上来说,“我一个人抚养孩子负担太重了,我并不是那种有了孩子就认为生活完美的人,所以要接受没有孩子的事实,比接受单身生活更加容易”。
艾略特说在她35岁左右的时候特别想生孩子,后来她就写了一本书。“我现在不再有那种渴望也是因为我创造了另一样东西,我的创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艾略特在开始写第二本书了,她说,“也许我的生活本来就该这样,我非常幸运,在写作方面有如此广阔的精神空间”。
多黛·斯特尔特39岁的时候在Jezebel 网站上写到她在发现自己将终生无子时感到的犹豫、彷徨和恐惧:“随着朋友和同事一个个结婚生子,有时候感觉我就像晚会上落单的人,别的人都回家了,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斯图尔特写到娱乐媒体如何向女性发起“生育宣传”的攻势,说哪个名人怀孕啦,产后如何减肥啦。她还写到时下有关女演员詹妮弗·安妮斯顿的空瘪子宫的报道。
在报道里,“(安妮斯顿)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一个笑容满面、健康快乐的女子,但显然她在内心深处却因未婚没有孩子而暗自伤神”。斯图尔特说这个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遵照预期去配偶、交配和繁殖,那么你就是不对的,而且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斯图尔特接着还说,若是在理想世界,“这甚至不是个问题,大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一切安好……然而这个世界却充满了矛盾: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要努力奋斗,要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而一旦奋斗成功,你又要被人指责为什么没有孩子”。斯图尔特怀疑,也许我们“不该将自己想象成晚会上落单的人,而是要看得更远,无需对生育之事小题大做。我们要承认,在藩篱的另一边,我们有足够的爱,有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晚睡晚起,可以旅游购物,可以享受欢愉,可以放纵自己,可以体味成功……即使我最后留在这个晚会上而没有中途转场,那也仍然是个晚会;即使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赞美,我们也可以自己赞美自己”。
的确如此,即使是因没有孩子而伤心落寞的人,也会收获其他意外的回报。
电视评论员南希·吉尔斯说,她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女儿。38岁那年她母亲去世,“我母亲过世后,我在街上看到人家母女在一起我就会非常伤心,”她说。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的两个妹妹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孩子是她们的依靠——早上要起来,让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她们有家庭需要全心照顾,而我却是漂浮不定的,我非常孤单。”但是,也因为母亲去世了,吉尔斯反倒和她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这是她的姐妹们无法做到的。她和父亲之间重新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爸爸的宝贝女儿!”她这样对治疗师说。“和父亲重新建立联系,感受到他特别的爱,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只是晚了一些。”
吉尔斯说,她绝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要孩子。
* * *
但还是有许多女性选择自己一个人要孩子。
帕梅拉是城市学院大四的学生,24岁。她在17岁的时候意外怀孕,“我感到很委屈,”她说,“长辈们都来问我有什么打算,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是不是要和他结婚”。她当时确实有个男朋友,许多人都催着她结婚,但是她不觉得婚后会有什么改变。“即使结了婚我也不会把他绑住,”她说,“所以结不结婚都一样。”她回过头来想,很庆幸自己没有仓促地结婚。帕梅拉认为,女人在决定是否当单身母亲的时候,要认真地考虑她留下孩子的理由,不管当时她有没有伴侣。“不要有了孩子还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她说,“你要有维持生活的能力,哪怕那个人跑了,哪怕孩子的父亲不能帮你,你也不怕。我并不认为结婚是有时间规定的,也不认为结婚是必须的。”
但是她又说,这个社会谴责女人没有孩子,然后又为她们设下层层复杂的陷阱。“18岁到22岁,他们说你还不具备生孩子的条件,因为你还在上学,这时候有了孩子日子会非常难过。是的,每一天都非常难过。可是再晚一些吧,我可能就有了事业,我需要全心投入我的事业。那么,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生孩子呢?什么时候可以生孩子呢?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在这个时间框架里大家都应该设法生孩子。”
单身母亲独立抚养孩子在低收入社区中是个常态,这是因为早婚现象在低收入社区基本上已经消失,而生育孩子可以让女性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未婚生育作为一条可选之路对于成功女性来说也日益被接受。那些确定想要孩子,并认为自己有能力要孩子的单身女性,哪怕只是想到自己有可能单独要孩子,也会感到极大的解放。
在我即将跨入30岁的时候,我已单身多年,身上的纤维瘤也变大了,我将不得不接受切除手术。我知道,从术后到肿瘤复发前我有一个时间窗口可以受孕,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有限的怀孕机会,然而我认为可以持久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30岁的我定下一个计划,决定要将我在三年前离开妇科诊所时的那个心情做一个了结: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的计划是独立生育孩子。父母说过会帮助我,我自己也会存钱开始准备,在我快到34岁的时候我去做手术,同时留意机会到35岁的时候怀孕,通过精子捐助人,或我的某个男性朋友来帮助我。我还和一位女性朋友讨论过是否有可能两个人搬到相邻的住处,互相照顾孩子和饮食起居,彼此有个照应。
一旦有了这个打算我心里就感到无比的轻松。并不是说我很想这样,相反,我非常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形,非常希望到了约定的时间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现在我非常开心,因为我无需被动地等待这个可以和我共建家庭的人的出现。寻找伴侣和生育孩子可以单独考虑,哪怕只是想想也会让人感到轻松。
我这个单身人士所订的计划表,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伴侣的出现则在我意料之外。我32岁的时候恋爱了,33岁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35岁生下第一个孩子,39岁生下了第二个。不管从时机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我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幸运之神眷顾,我的生活会变成怎样。我并不自夸我有做单身母亲所需的勇气,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当单身母亲的想法,才使我在前进的路上充满能量,充满乐观。
35岁的克里斯蒂娜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工作,也有和我同样的想法。她的父亲给她推荐了一篇关于生育并非一定要结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励下,她抛弃结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最近她在俾斯麦重新找了一名妇科医生。“我很害怕,我都35岁了,我非常想要孩子。”克里斯蒂娜身上的节育环将会在她40岁不到的时候失去效用,医生说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环,言下之意就是说,她40岁不到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听完医生的话她紧张极了。
但是令她吃惊的是,这位北达科他州的医生说:“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里斯蒂娜!”没想到这位医生是在上学、仍然单身的时候要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娜说现在她的新年计划是“为36岁的到来做好准备,我要照顾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产前维生素,现在我的指甲、头发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丽夏·威廉姆斯曾经有过一段情感关系,当时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钟生下孩子,但是什么也没发生”。40 岁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她说那个时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问自己:我要放弃生育孩子的想法吗?”但是她说幸运的是,她“有成功的事业,有通情达理的父母,他们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结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认为,家庭和种族是社会建构的基石,但体外受精的高昂费用让她望而却步,而且对于“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观念,她也总是谨慎看待。同时威廉姆斯还关注“非传统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养家庭模式、亲缘模式;即我们现在这种非常计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说,就在她40 岁生日到来之际,“大部分人都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确实是在分手的那会儿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抚养孩子”。
后来威廉姆斯领养了一个儿子。
她感觉自从领养了儿子,人们对她的看法立刻就改变了。她说,在这之前“我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黑人女子,事业上奋进,是黑人族裔的榜样”。一旦领养了孩子“我就成了单身黑人妈妈”。她说起在儿子只有五周的时候,她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基督教联盟的拉尔夫·里德分在一个讨论小组,里德对她进行了发难。威廉姆斯难过地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单独领养孩子,不只是拉尔夫·里德,我家里也有人这样想”。威廉姆斯说,在纽约私立学校的体制里,“就因为我是单身母亲,人们就断定我是谁的保姆,是东家慷慨解囊供我儿子上学的”。
她说,还有别的说法是,“我是特雷莎嬷嬷,这个孩子今后难有出息,这比单身黑人妈妈之类的话更让我讨厌。我讨厌有人说他是个被遗弃的灵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我讨厌人家说什么要感恩,因为我把他从贫民窟里捡回来。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学生,但人们就认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当上单身母亲往往不是一个人有意识计划和考虑的结果。蕾蒂莎·马雷罗35岁的时候,和异地男友在分手之际的最后一次风流后怀孕了。“那个时候,我更想成为一名母亲,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说,“那是我人生的目标。怀孕以后,我之前的忧郁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烟消云散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从未像怀孕这段时间那样爱我自己。我是自然分娩的,因为我知道以后我不大有机会再次自然分娩,我还想尽可能延长母乳喂养的时间。”
蕾蒂莎怀孕期间是《明星》杂志的文字编辑,产假期间她拿平时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产假结束回去上班的时候,现实的问题迎面袭来—每天十五小时的工作时间,没有伴侣,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宝宝。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后来又因为无法协调育儿和工作的时间,先后失去了三四个工作机会。孩子的父亲并没有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纽约,一年只能过来看望她们几次,而且,他的经济也不宽裕。蕾蒂莎数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个比一个便宜,社区条件一个不如一个,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弗吉尼亚州。
经历了这一切后,蕾蒂莎说:“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为了这个小女孩能过上好的生活。她从来不知道我的银行存款是35美元还是3500美元。”
* * *
家庭结构的改变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现象,让无论持有哪种意识形态的批评人士都感到恐慌。有些人说,女人怎么可以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可以不生孩子!举国上下都在担心单身和晚婚对女性自身、对国家造成危害:专栏作家也好,一国总统也好,都将婚姻模式的改变归咎于她们,而长期以来束缚了她们自由的,也正是这些传统的婚姻模式。女性继而觉得相夫教子没那么有意思了。
随着女性倾向于晚婚和不婚,加之结婚的女性除了为人妻母还要为其他事情分心,美国的出生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历史最低,每千名育龄妇女仅产下了62.5 名婴儿,差不多只有1957年的一半。1957年是婴儿潮时期的高峰,每千名妇女产下了近123 名婴儿。尽管婴儿潮时期的奇高数字,并不能作为我们衡量美国生育水平是否正常的常规标准,但是心存顾虑者仍旧不乏其人。
乔纳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2013年出版的《当无人生育时还能期盼什么》一书以“美国即将来临的人口危机”作为副标题。拉斯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低生育率的报道,重复了西奥多·罗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种族自杀”论,他在文中称,“造成我们大部分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虽然和工资滞涨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为所致。“开始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已经和男性持平了(后来甚至超过男性数量)”,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开始扩大她们的事业范畴,不再只是教书和做护理工作了”。最后他写道,“避孕药加上同居的潮流,联合起来打破了性别、婚姻以及生育之间的铁三角关系”。虽然拉斯特谨慎地指出有些方面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会发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还说,受过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杰出代表”的一个群体)的生育率只有1.6,说明“美国有其独特的独生子女政策,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保守派专栏作家梅根• 麦卡锡对此也表示了忧虑,她警告说,那些不重视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腊,看看“当一个国家未来不可避免地出现比过去更严重的贫穷时,会是怎样的情形,那是社会崩溃、政治崩溃和经济瘫痪”。
不只是保守人士,我们的民主党总统对此也表示了关切。虽然总统并没有担心人口数量下降,但是他对单亲家庭的不幸公开表示了担忧。在2008年的父亲节演讲中,奥巴马谴责了不在儿女身边的父亲——特别是黑人父亲——说他们是“擅离职守的士兵”和“失踪的战士”,他认为缺席的父亲要为黑人儿童的糟糕处境,要为辍学率、入狱率和青少年怀孕率的上升承担部分的责任。
奥巴马谨慎地赞扬了“英勇伟大”的单身妈妈,并恰如其分地提出,“我们要为那些靠自己抚养孩子的母亲提供帮助……她们需要帮助,”但是最后总结说她们所需的帮助是“孩子的父亲在家里”,因为“唯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有牢固的根基”。在演讲中,奥巴马——这位从小没有父亲陪伴的总统——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确的家庭模式、社会基础和帮助方式只有一个,他还强调,伴侣同居的双亲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丽莎·哈里斯写到奥巴马对待单亲家庭的态度时说,“奥巴马总统是对的,他说有爱、顾家、在经济上负责的男人,对于孩子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社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进儿童发展的必要因素时却缺乏想象力……这有点奇怪,因为这些因素在他个人经历中是非常显著的”。哈里斯– 佩里指出,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优质的教育、旅游和拓展视野的机会”。
认为单身母亲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不只是奥巴马一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9%的美国人认为单身母亲现象的增多是“社会的不幸”,61%的人认为孩子的快乐成长父母亲缺一不可。其他比较开明的批评人士,包括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则担心,不仅仅是单亲家庭,将单身母亲也看成是新的常态,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影响。“让孩子看到男人也会爱护孩子、照顾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纳姆说,“他们不一定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看到男人关爱孩子、照顾孩子,我们就会回到过去的性别角色关系中,认定只有女人才能照顾孩子。”
当然,社会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好几代的时间,才能适应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当女性从传统预期中解放出来,很难马上有新的方法来应对或重新构建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做出调整,做出改变。凯瑟琳·埃丁继《我信守的承诺》之后,于2013年推出了一本关于单身父亲的书——和蒂姆西• 尼尔森合著的《尽我所能》。为了写这本书,她专门和居住在旧城区里、生活条件贫困的男人相处。这些男人,相比于上一代“缺席”的父亲,有更大的决心建立亲子关系并承担抚养义务。人类总是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且会为了适应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变,我们不能只是环顾四周就妄下结论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永远不会改变。
然而对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这些悲观人士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观点,并且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社会学家发现,双亲家庭的孩子成年后比单亲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苏珊·布朗曾在书中指出,现在约有半数儿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里,布朗列举的一些调查显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其教育结果、社会结果、认知结果和行为结果,平均来看都超过其他儿童”。但是,又由于低收入的单亲群体愈加普遍,我们很难区分哪些结果受到父母亲一方缺席的影响,哪些受到生活条件贫困的影响。布朗这样写道,“在决定育儿方面的事务和面对育儿方面的压力时,单身父母(主要是单身母亲)因为缺少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和他们共同商量的伴侣,往往会减少对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但是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利处境混同”。
正如布朗所写,单是婚姻或是生物学一方面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释不同家庭结构给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长结果,“我们未来的研究任务是提出更加周密的理论,提取更加详实的数据,来破解导致这些差异形成的机制”。那样的理论和数据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的家庭结构、新的男女角色认同,以及这些新角色是否能够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结为夫妻的社会政策的支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世界已经不同,我们要试图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人性化,以适应不同个体、伴侣和儿童的要求。
凯蒂·罗菲是一位社论作家和辩论高手,她在不到30 岁的时候描写过她那些长期单身的朋友如何一边享受性的自由,一边追求事业,但同时她也不掩盖自己对简·奥斯丁时代的婚姻关系心存渴望。然而过了40 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这两个孩子还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罗菲现在定期写一些有关单身母亲话题的文章,其观点令人信服。她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说到她自己享有的经济和教育特权,承认她虽然可能并不是“典型的单身母亲……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亲一样,当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单身母亲”。罗菲认为,正是一直以来认为未婚妈妈是非正常现象的想法,“使得人们无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态度来理解丰富多样的家庭模式”。
罗菲援引了萨拉·麦克拉纳汉正在进行的“弱势家庭”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单身母亲状态的主要风险并非简单地来自于未婚生育,而是根植于贫困,其次是频繁更换恋人(这也可能是贫困加重的结果,因为这些恋人处于抑郁、无业状态、有暴力倾向,或导致家庭经济更加拮据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罗菲从“弱势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论,“经济状况稳定但父母之间关系紧张、存在冲突的双亲家庭,较之于经济状况稳定但父母之间关系不紧张、没有冲突的单亲家庭,对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这番道德说教中没有提及的是,”罗菲这样写道,“家庭形式多种多样”,“没有一种家庭结构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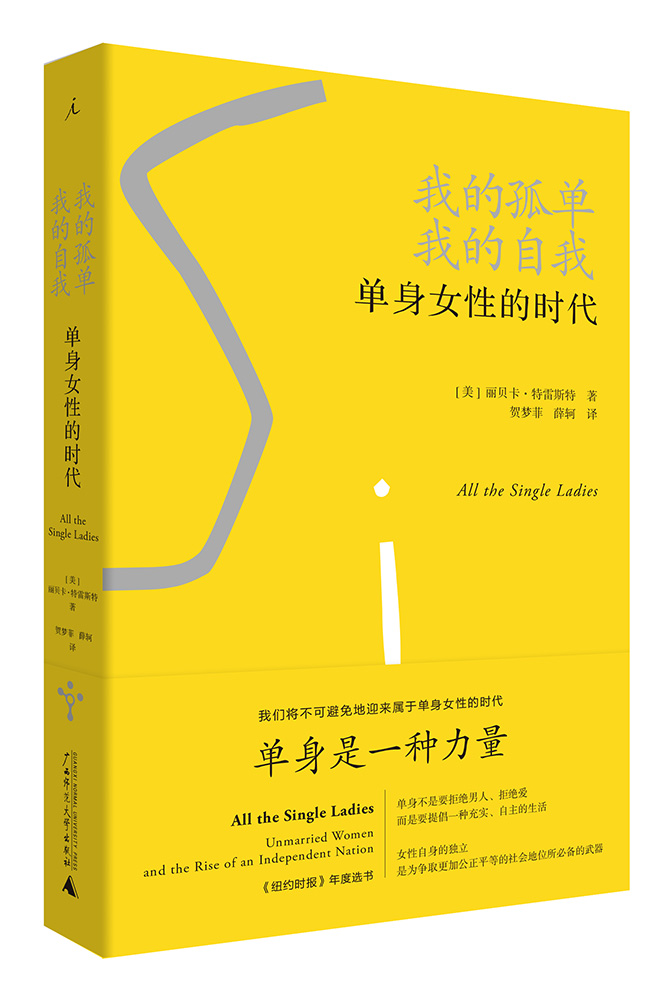
—— 完 ——
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新闻记者,时尚杂志ELLE特约编辑,擅长分析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Vogue等多家杂志撰稿,著有《女孩别哭》(Big Girls Don’t Cry),即将出版《重塑美国的女性愤怒》(Good and Mad: How Women’s Anger is Reshaping America)。
文中图片除剧照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