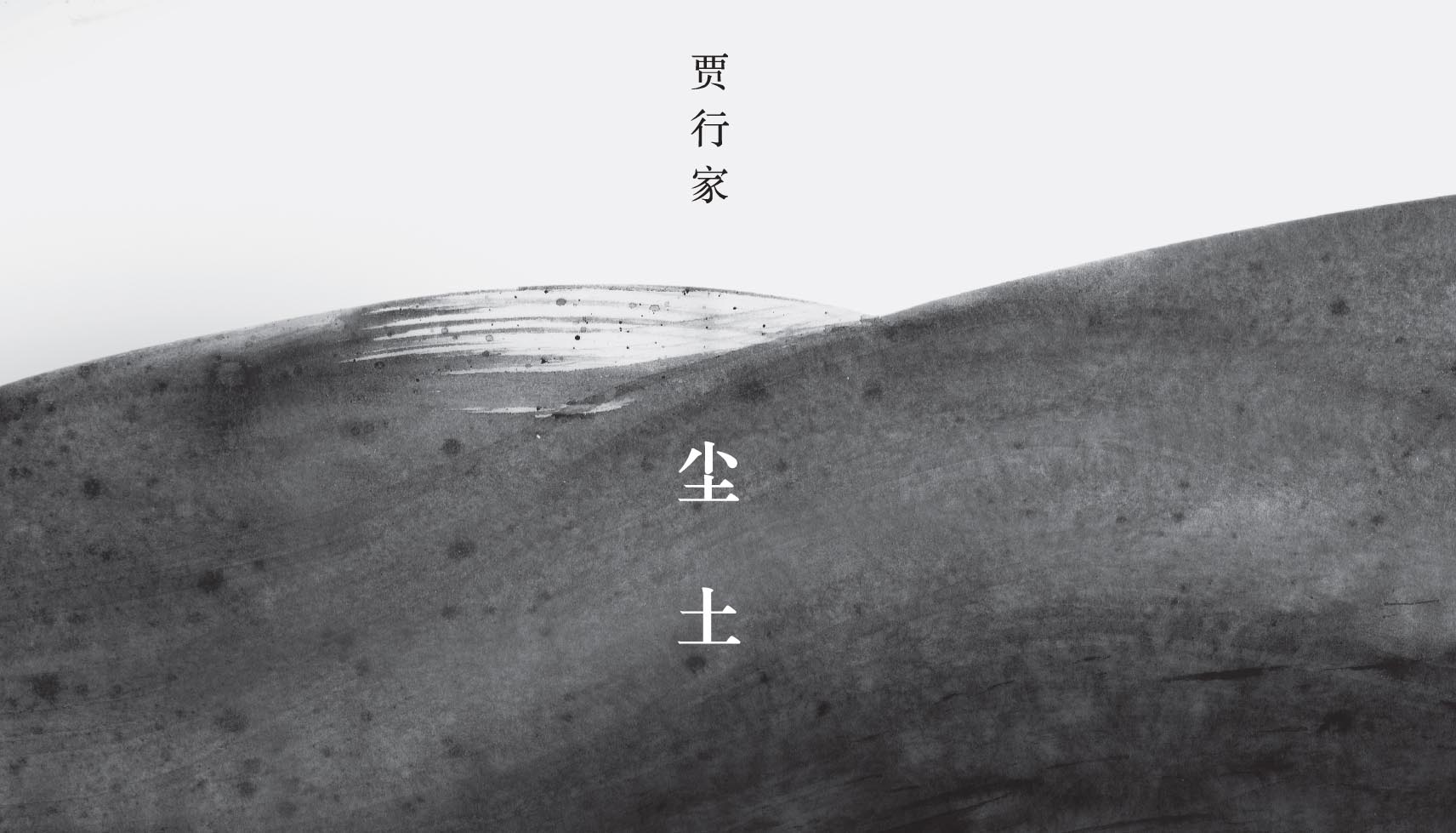大庆得名突兀,是五十多年前的国庆上被人顺口取的。黑龙江境内的大小地名,十二座城中的半数,大多和满蒙语有关,晒网场,射箭地,跑马场,含义简单,译音以讹传讹,有的莫名其妙,像哈尔滨,有的悦耳,像牡丹江。有人说嫩江是满语的“妹妹”。用妹妹来比喻河流和死亡,都只有经历者才能领悟,都很美。
但大庆这个名字也没起错。
从东南进大庆的公路先一头扎进褐黄色的草原,目之所及望平坦无垠,乘客总觉得自己是在草原的正中。草原被运油的公路、铁路切割。表面除了电线杆,只有万千座堆得整整齐齐的牧草垛,盐碱滩上的水草是上佳饲料,不知道什么样的牛羊才能有幸吃到,什么样的人物才有幸吃那些牛羊。大庆幅员上不是座小城,辖区广袤,城区(实则是各采油厂的厂区)间的距离动辄上百公里,冬天降大雪时,狂风在平原上来回,交通时常中断。中间就是这样的河滩、草地。颗粒无收的土地多年来无人问津,草甸上只有独来独往的牧人。女真人曾对这里了如指掌,入关去以后,又把吴三桂的降兵叛将遣到这里看守驿站,被流放和抛弃的记忆让他们在几百年里无法入乡随俗,恪守苗人和兵士的礼仪,吃食,言语,与民间一再混血,痕迹在东北土著中依稀可辨。这里是流放者和历险者经营、挣扎的所在,几百年至今始终如此,有的自知,有的尚不自知。
然后,车上高广的新建公路桥,桥长几公里,被钢索吊起。桥下是大沼泽,为了招揽游客,沼泽被称作学名“湿地”,变成旅游的资源。在桥上看,下面芦苇密布,大鸟穿梭,水面凝滞,日光普照时是无边无涯的难以描述的颜色和形状,塔头草丛沉浮其间,水影起伏妖异奇诡。如果人在下面,恐惧之感就会顿生,沼泽里步步险象,入夜前就会从世间沉没。有人类之前,这里是苍凉如海的大湖,这片区域曾聚集了非洲草原动物的始祖—披着长毛的猛犸、犀牛、野牛,狼群和猛虎出没。动物学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它们是何时消失,或沿着哪里迁徙走的。海枯石烂之后,大湖干涸下沉为沼泽,兽群沉入地下,万年前的湖化作漆黑黏稠贵比金子的东西—石油。随着地下井喷的暴利,随风长出一座大庆,五十年对城市来说太短了,追流行,赶时髦,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就已拥有了一切。除了开放搞活,就是一万年前的猛犸,中间九千多年一片空白,无知觉,无负担,无忧患,无畏惧。
下桥立刻就进了市区,新城这一边,集中了城市主持者乐于展示的一切:治所、在建的巨型建筑、南方土地吃紧之后涌入的CBD,最昂贵的楼盘聚集于此。街上车少,人比车还少,整座城市吞吐吸纳其他现代城市的优缺点,从无个性中选择共性,预算充盈,计划两倍的宽广,必三倍宽广十倍造价。喜的是地域辽阔,防止堵车,马路修得广场一样宽阔,人行道与建筑之间还留有一箭之地,但是地价却奇怪地并不低廉。马路两边几十层鳞次栉比的玻璃高楼,猛犸穿行其间也会心生畏惧。玻璃高楼脚下挖了十个足球场大的人工湖,半人深的湖里放了木船,湖边立着塑料椰子树。选好地段,提前若干年养了一大片草皮和树林,建了一群散放的别墅,楼间几十米或上百米,深处有个钢筋水泥的四合院和官派的主建筑,宦门似海,举行政务活动。与别处不同之处,就是城区里到处都是橘黄色、二层楼高的“磕头机”,一分钟几次起落,本地人会告诉你,每次起落可以赚若干元,一昼夜能产生若干万。大庆的油由国家管控,相关数据地方无权过问,但谁都清楚,五十年下来,地下的石油去之大半,靠注水、添加制剂的“二次、三次采油技术”来压榨也来日无多,油被“调拨”去了远方,狂妄攫取则要这座外表光鲜的城市在不久的将来归还。
陈湣公的廷园里坠落下中箭的鹰隼,那支箭石头木杆,长一尺八寸,与中国的不同,他派人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隼来自极远之地,这箭是肃慎部族所用。武王伐纣,九夷百蛮贡献各自所产,肃慎部曾献来这种箭。(《史记·孔子世家》)
这大箭的箭镞在新落成的大庆博物馆里见到了:几十枚不同的石料,磨成雅致的菱形,并不都是青石。《汉书》说这里滴水成冰,弓矢苍劲肃杀,淬有剧毒,中者立毙,其实,看上去就是猎户的家什(光滑的石头怎么喂毒呢?),绝没有秦人兵器那样望而生畏。几十年来,本地出土了几十具大象骸骨和几百架的野牛,最大者为国内首见,曾长期堆在简易库房里,新城规划了一字排开的几座粗豪大厦,发展文化产业,其中一座是博物馆,中厅高达二三十米,终于挪了进去,成群的象骨在展厅里耸立起一座骷髅的森林,野牛群被复原为迁徙时的样子,点缀着掠食的野狼化石。这笔钱罕见地花对了地方。
三百年前,一百年前,中原人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片天地,辽阔得不像话,肥沃得不像话,奇异得不像话,无主,没有规矩,认错了方向,跑死也见不到一户人家。他们来到这里时,天暖要为半年的冬天准备,最适宜住地窨子,备木柴,腌酸菜,不愁柴米愁住行。只身的女人必须靠上个能劳作的男人,彼此不问从前,也不轻易说起将来,除了活着之外,空空荡荡。
五十年前,以对采油一无所知的复员兵为主,几万人来到这里,树立了一面旗帜“铁人精神”,电视剧里,拿肉身搅拌水泥,用脸盆端水钻井,祖国要石油,为祖国献石油,豪言壮语出口成章,有高度,有气势,有仄有韵;五十年后,坐顶配奥迪A6的大庆中年人,捧着讲稿,坐在一千多万的水晶灯下缅怀他的前任,一是要切实,二是要进一步,三是要着力,自诩正继承着那种精神,偶尔抓起一个来都是九个零十个零的身价,一户口本的华侨。
市民里,有那几万人和陆续赶来者的后代,有络绎不绝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耕种了几代的土著。虽然大庆一直号召发展非油产业,但和油有关的还是多数,政府和油田公司是两套交错的行政系统。本省人都下意识地觉得大庆人富得流油,钱来得容易,八十年代,都传说他们过年家家分一头猪,女人用的高级化妆品都算福利品,福利比津贴高,津贴比工资高。地产刚热的时候,大庆房价一路走高,石油公司的普通干部,年终奖就是半套房子,不买房不知道买什么。大庆当然也有的是低收入人群,但是在人们眼里,在新闻联播前十五分钟,没有他们。
我大学班上有两个大庆人。一个是保送生,时时以油田的霍阔为自豪,父亲是采油某厂的肥白领导,床底下有几十双耐克篮球鞋,在师大养着两个学声乐的女友,对大庆的娱乐场所了如指掌,时常吹嘘要我们陪他回去,见识一下他在那里如何“好使”。在他的嘴里,油田的事儿耸人听闻:几个人,一辆油罐车,和保卫部门勾结一夜,就是几十万……他念到第三年就不再来了,不及格的科目需要另外三年才能补考完毕,听说进了北京的一家石油国企。
另一个很正常。那个同学说,哈尔滨有第一家肯德基时,大庆人礼拜六成群开车过来吃,哈尔滨开第一家假台湾火锅店时,大庆人礼拜六成群开车过来吃,时间和汽油都不在乎。这种事他腻歪透了,这种对大庆的印象他腻歪透了。他回家去,在厂区里遇不到一个生人,在街上看不到一家连锁店,这种被抛下的感觉他腻歪透了,不知道多少年才有真正的繁华,真正的复杂多态,真正的市井。
在他的形容里,那里没有一股味道可供你走出去多年之后思念,没有乡音,像一切移民之地一样,人们的口音都是普通的发音,是个思乡都没有“抓手”的地方。悠久的山城水城,街巷的石板下是前朝的石板,每块石头都蒙着青苔,每扇木窗都有刻痕,人们的神情相像,家里有偌大的祠堂,喝茶和喝汤有世袭的姿势;在古都,你可以不记得,不造访,但历史仍在那里,城墙和老寺被拆毁了,阴影还能矗立一段时间;在五方杂处的城市,商贸发达,各色人等光怪陆离,贩卖稀罕违禁的货物。一座精彩的城,要有怪癖、有恩仇、有文学、有闲人、有传奇、有悲怆。而这里和深圳等其他新贵城市相比,还多了一层乏味,文化只有企业文化和官府文化,上一代饱受军事管理,财富并没有带来自由,人们习惯于等靠“上头精神”,在管理者那里,这被认为是一种“高素质”,在生活上则全无情趣和审美。这片苦寒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一时还没有找到与之对话的语言。
靠一种简易挖掘的资源突然勃兴的地域文明,有点儿像作弊,常常受不住变局的考验。城市要为来者提供一种生活,否则只是过客。大庆为之骄傲的东西,还不足以构成一座城市。
但愿它在经济没落之前获得在历史中生存的机会,要说祝愿的话就是:若干年后,人们说起这里时,使用的词不是“曾经”。
——END——
贾行家,男,1978年生人,现居哈尔滨,网易博客 “阿莱夫”作者,为一些报刊和网络媒体写过专栏。非职业作者。微信公众号:jiahang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