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深林有歧途
败叶掩足印
举步入荒径
只为少人行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与学生陈宁(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学者)往来的信件中,曾写下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中的片段,他在信中告诉陈宁,无论读书还是做人,都需要有不怕寂寞,不随众人的心理准备。今日清晨,许倬云在美国匹兹堡与世长辞,享年95岁,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公布了这一消息。
幼年:看见死亡和战火,知道了什么叫饥饿和恐惧
1930年,许倬云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士大夫世家。出生时因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所以他的手脚是弯曲的,肌肉细胞功能的受损使得他一生需要借助双拐行走。许倬云的童年时光伴随着抗战的时代巨变,当时他的父亲许凤藻担任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职责是保障前线军粮民食的供应。许倬云因身体残疾不能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去上学,所以只能随同父母沿战线四处迁徙。
为了逃离日本人的侵犯,许凤藻需要不断变更办公驻点,从湖北沙市到老河口,再到四川万县,在他的回忆中,八年抗战期间除了最后一年多能够安顿在重庆,其他时候都要“跑来跑去”。在抗战逃难的过程中,许倬云总是被父亲单位身强力壮的同事背着移动,因为身体的不便,他常常只能“被摆在某个地方”,承载他身躯的有过土墩也有过石磨,“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他曾这样说道。


许倬云一家停驻在四川时,他的母亲常带着许多女工为赶赴前线的川军烧热水。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看着那些多得望不着边的军人,当许倬云听到其他人说这些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他说自己就是在这时“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在《许倬云谈话录》一书中,许倬云说抗战是自己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替代的经验”。抗战的经验让许倬云看到了在离乱岁月中普通百姓的牺牲与苦难,这也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在他日后的史学研究中占据着深重的分量。

许倬云 口述 李怀宇 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
中年: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1948年底,许倬云全家迁往中国台湾地区。在插班于台南二中完成高中学业后,1949年8月,他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又在校长傅斯年的亲自劝说下于大二转入历史系,开始与“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结缘。研究生毕业后,许倬云便进入了史语所工作。1957年的夏天,工作第二年的许倬云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主要研究近东(相对于“中东”“远东”的政治地理概念,常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埃及考古。日后回忆起在芝大留学的日子,他曾说:“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住在医院里,参加民权运动,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一般人的信仰、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有了一些观察。”
受到美国民权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倬云在供职于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同时,与老友胡佛、李亦园在台湾地区共同成立了“思言社”并出版刊物《思与言》,以探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福利国家”。1970年,在与妻子孙曼丽结婚的第二年,40岁的许倬云辞去了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职务,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担任历史系及社会学系访问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此后便定居于美国。
许倬云的治史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在写著作《西周史》时,他一改过往史书对周公等政治大人物着墨的书写方式,将目光聚焦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种书写方式遭到了部分史学同行的批评,面对诸如“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等质疑,他回应道:“在英雄和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和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的小民百姓填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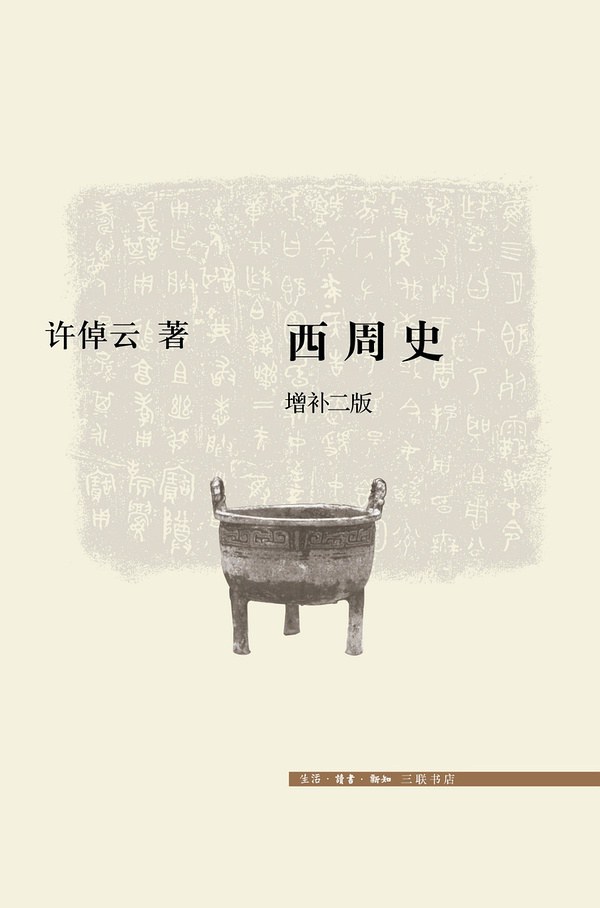
许倬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3
许倬云这种对普通人生活和想法关注的意识在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接受《人物》采访时也有所提及,“他特别有一种愿意从世俗跟民间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问题的倾向,这个跟他个人的学术训练似乎是有所不同”,王德威说,“所以一开始他一方面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但他的‘心’是非常牵动到当代经验的”。许倬云的朋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在采访中也表示:“他是真真切切地去关心历史与历史背后或者历史中的这些人。”
暮年:希望帮助年轻人安顿身心
作为“生长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许倬云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和发展,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对历史和当下的忧思。在2019年拍摄的《十三邀》的节目上,许倬云结合个人经历,从全球政治局势谈到个人的精神危机,一句“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为一些人如何在快速变动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内心安顿和人生意义提供了些许指引。很多年轻观众在看过节目后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很受感动,称许倬云用他的人生智慧疗愈了年轻人的“精神内耗”。

在收到这样的反馈后,许倬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缘”,希望努力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尽管年事已高且身体有诸多不便,但他依然坚持关注时事热点和学术新知。《许倬云十日谈》一书记录了许倬云与数十位院士、学者、科学家、企业家的提问交流:谈到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许倬云通过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分析了大规模瘟疫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在讨论美国社会与政治时,他以其在美国生活、工作六十多年的经历对美国社会与政治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和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许倬云对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表示关注,他强调在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要注重与人文素养的结合。除此之外,他还通过直播对谈的方式与人类学家项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等就当下年轻人关注的“内卷、躺平”等流行社会问题进行对话,以探讨个人成长与时代环境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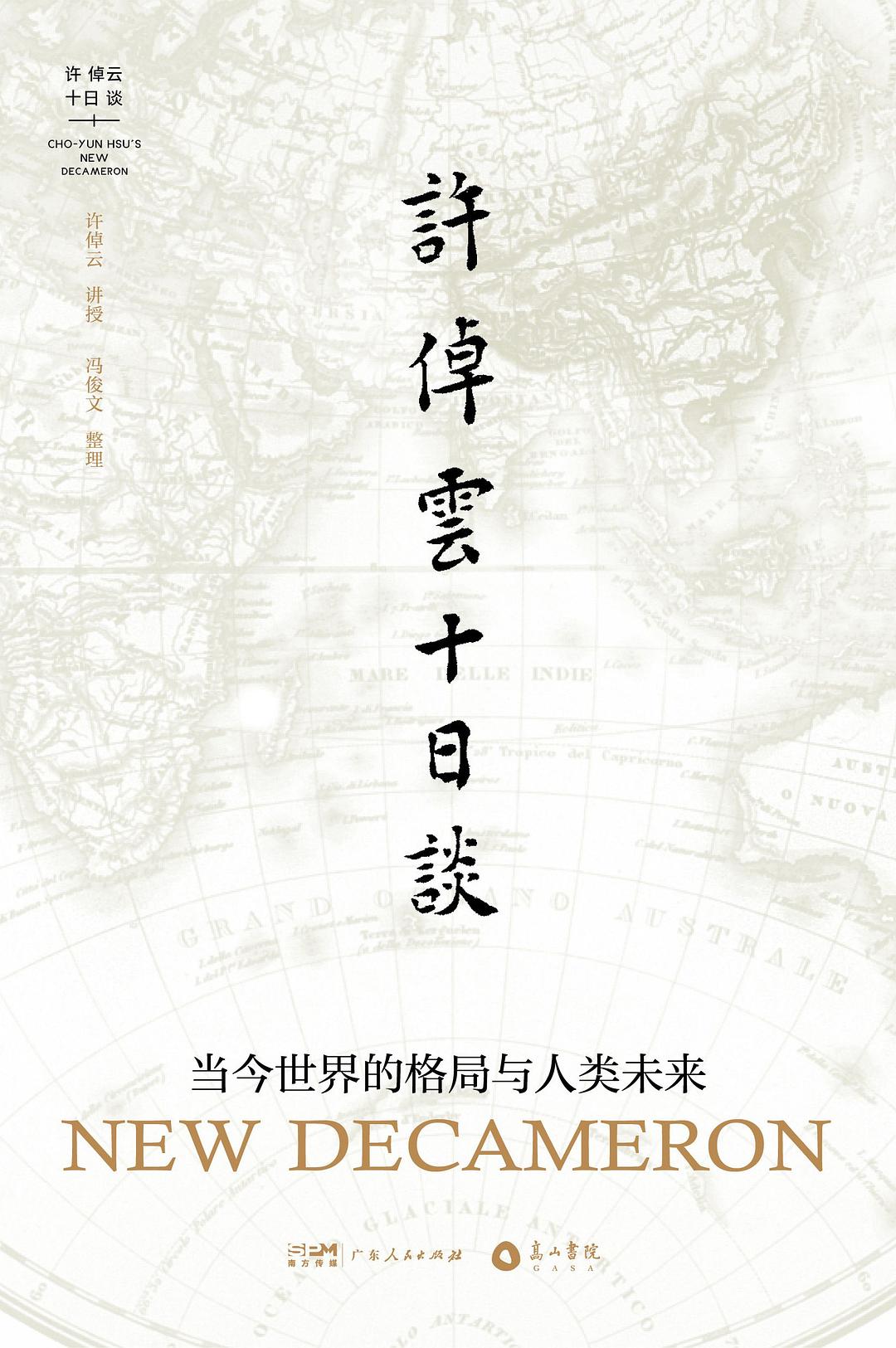
许倬云 讲授 冯俊文 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3
许倬云的这种“不遗余力”王德威非常能理解,在过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疫情后在许倬云的提议下,他们保持着一周通一次电话的联络方式。王德威说:“那种时不与我的感觉,不只是年纪上的、健康上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的那种危机感啊。我觉得危机感是某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他们血液的一部分,他们的DNA里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以那种紧迫感,用一种很俗的话来讲就是感时忧国。”
“我希望尽我的余年,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身心有个安顿”,在《十三邀》的节目中许倬云这样说道,他鼓励年轻人在“惊涛骇浪”之中扎实自己,不要歪曲自己的知识情感。这也恰好与他过去关于如何通过学习历程观察世界的见解相契合,“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他说,“不糊涂并不是聪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正如《许倬云谈话录》的撰写者李怀宇所写的那样,“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
参考资料:
许倬云、李怀宇:《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陈永发等:《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许倬云 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
https://mp.weixin.qq.com/s/q2raP_fFYcHq-1oeXYpHvw
许倬云: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 十三邀
https://mp.weixin.qq.com/s/QMYgvCkOpsYlbQ1Eld2kkg
许倬云:意义危机之下,要有远见超越未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