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并不全是那些公认的慈善家,还有努力付出满足好奇的科学家们。这种纯粹的追求为世界带来了成千上万宝贵的意外之喜,包括抗生素、疫苗、X光和胰岛素疗法。
詹妮弗·杜德纳和塞缪尔·斯腾伯格合著了《造物之隙:基因编辑与不可思议的演化控制》(A crack in creation : 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一书,为读者描述了另一项偶然的发现。这是一种能够彻底改变生物科学技术的方法,我们借此得以改变几乎所有物种的任何基因组。这种方法就叫做CRISPR,听起来就像是冰箱里毫无用处的隔层一样。但从科学意义来看,CRISPR可与双螺旋结构(1953)相提并论,还有20世纪70年代研发获得的测算基因序列片段的能力,以及80年代发明的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借助该技术我们能够增强特定的DNA片段。这三项成就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杜德纳和其法国同事埃马纽埃尔·夏彭蒂耶是CRISPR的主要研发人。因具有极高的医疗价值和实用意义,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很高。
本书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CRISPR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斯腾伯格是杜德纳的学生,但这本书用的是杜德纳的语气。)由真正的发现者来执笔科学写作并不常见,故事往往都是由科普作家或者其同事来讲述的。因此,本书从参与者视角展开叙述这一点尤为吸引人。
“CRISPR”是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的首字母缩写词,这是一种编辑DNA的手段。利用CRISPR,我们能够将ATTGGCG中的序列变为ATTGGGG、CCCCCCC或其他序列。最近,科学家也研究出了其他方式来达到这一效果,但无一例外,这些方式都不实用,不仅费时,效率也很低。CRISPR的优势在于,它使得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编辑基因:它应用简单,似乎在我们挑选的所有物种和细胞类型中都表现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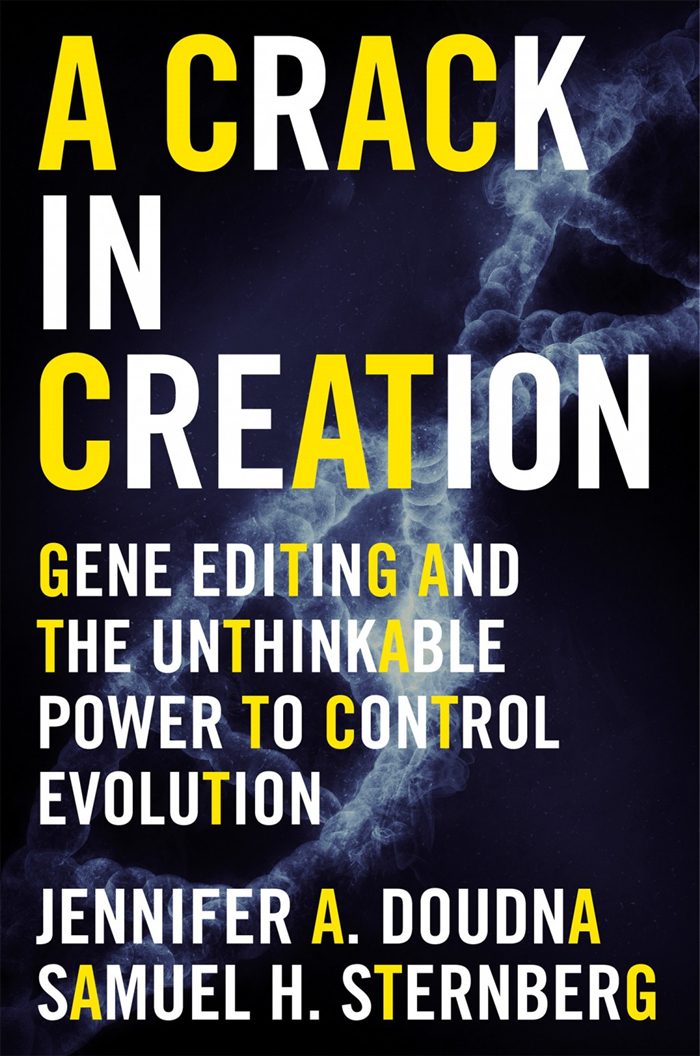
CRISPR的故事便是纯科研带来意外之喜的最好例证,它由寥寥几位充满好奇的科学家带头发起,他们并没想要改变世界。20世纪80年代晚期,科学家们在一些细菌中观察到了奇怪的DNA片段。这些DNA片段由完全相同的短序列组成,且具有回文结构的重复特性,从前往后和从后往前读都一样(如ATGTTGTAC)。这些重复的回文结构由20个字母组成的独特DNA片段分离开来,研究发现,这些片段最终来自细菌感染的病毒。人们很快便意识到,CRISPR正是细菌用来对抗高危病毒的免疫系统。
因为CRISPR帮助细菌“记住”了之前的病毒侵害,便可以为以后同一病毒的入侵做好准备。这与我们的免疫系统类似,它们也会“记住”入侵者:如果你曾经得过麻疹,就不会再得了,因为第一次的经历使免疫系统为将来做好了准备。细菌通过保存第一次侵害的病毒的DNA片段来达到这种效果。当同样的病毒再次发起侵袭,细菌将入侵者的DNA与已保存的片段进行配对,以识别重复出现的外来DNA片段。一旦入侵者被判为有害,细菌就能进行回击,比如在事先保存的相同DNA片段/入侵者DNA匹配片段的指引之下,毁灭入侵者的DNA。

杜德纳和夏彭蒂耶觉得,颠覆CRISPR系统也不无可能: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入侵病毒的DNA,通过借助感兴趣的DNA序列(比如,引起遗传性疾病的DNA序列)促使CRISPR剪断目标序列的所有DNA分子。一旦DNA被剪断,也能使用不同的序列来进行修复,包括使用不会引起疾病的相同基因。瞧!这就是基因编辑,也是一条通往基因编辑师的道路。
重写基因或许能够治愈许多基因疾病。比如说镰刀形红胞病患者的血红蛋白DNA编码中只有变异的单一“字母”。使用CRISPR在胚胎或骨髓中替换该字母并非难事,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希望治愈数百万深受这一疾病折磨的人们了。
但这只是基因编辑众多可能之一而已。从原则上来说,CRISPR可治疗任何单一或少数变异导致的疾病:不仅仅是镰刀状细胞性贫血,还有亨丁顿舞蹈症、囊肿性纤维化、肌营养不良症和色盲。我们也能通过删除艾滋病病人DNA中隐藏的HIV病毒来治愈他们。通过编辑早期胚胎,我们能够降低阿尔茨海默症和一些乳腺类癌症等与基因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我们还能改变下一代的样貌,改变他们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从理论上来说,甚至还能改变他们的身高、体重、体型和智力。这些都还未曾在人类身上做过试验,但鉴于CRISPR在人类细胞培养中表现不错,这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至于其他物种,我们既能改变猪的基因,也能改变人的基因,因而我们能在不引发免疫应答(机体对抗原的应答)的前提下将猪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我们已经通过CRISPR培育出了抗病毒的家畜,现在我们也能在农作物的DNA中编入产生杀虫素的基因,无须再依靠危险的农药了。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指出的,CRISPR让我们能够绕开或撤销进化过程,不再依赖选择性繁殖这种充满偶然性的方法。
当然,DNA编辑也引起了伦理问题,本书最后四分之一的内容讲述的正是这个方面。杜德纳担心纳粹式的人种改良学卷土重来,她甚至曾梦到希特勒要她提供CRISPR技术。或许我们只能在“细胞体”上进行基因编辑:改变那些无法传给下一代的受影响组织中的基因?或者是“种系”编辑,以能够传给后代的方式改变早期胚胎?尽管这不免让人想起人种改良的黑暗时代,事实上却是修复大多数“疾病基因”的唯一方式。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我们是应该只修复像镰形细胞贫血症这样会损害后代的基因呢?还是也可以改变那些可能致病的基因呢——比如能够引起高胆固醇和心脏疾病的基因?
事情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应对。我们是否应该编辑失聪父母的胚胎,以繁衍同样失聪的后代,借此来让他们的孩子亲身体验“聋人文化”?基因强化最大的禁忌便是——我们是否应该在样貌和智力上给后代们助力?毕竟,这只会给那些能负担得起这一技术的人提供基因优势。
最后,我们如何确保这项技术不落入生物恐怖主义者的手中?现在便宜简便的CRISPR设备在网上便有出售,使得任何人都能够编辑细菌的基因。基因编辑疾病的梦魇正在逼近。在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之前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杜德纳和夏彭蒂耶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他们在态度上的犹豫不决是这本书唯一的不足。
在伦理窘境之外,还有商业方面的困境。要获得CRISPR技术的许可证,需要花费一大笔钱。眼下,在杜德纳的雇主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利之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峰的主要工作就是将CRISPR从编辑细菌基因的工具,转化为能用于人类细胞的实验室工具。这之中存在着许多利害关系。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书中明显遗漏的问题。包括杜德纳和张峰在内,CRISPR相关的许多研究都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的,即美国纳税人。但两位科学家都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很有可能通过授权CRISPR在药物和其他方面的使用,使得自己和其所属大学大赚了一笔。因此,如果我们还重视职业道德的话,除了CRISPR技术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化,我们也得思考下科学家们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谋利的道德问题,就比如杜德纳和斯腾伯格。专利和名誉的争夺,妨碍了那些推崇进步的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而那些建立在纳税人资助研究基础上的公司,却让我们为使用这些产品付出了双倍的费用。
我们需要铭记,就在不久之前,大学里的科学家们还拒绝以此谋私利。他们无私地将X光、小儿麻痹症疫苗和互联网等发现贡献给了人民大众,科学好奇心的满足才应该是他们最看重的奖励。
(翻译:熊小平)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New gene-editing tool could cure disease.Or customize kids.Or aid bioterrorism.
最新更新时间:07/03 12:2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