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6月的一系列高校毕业典礼上,多位大学校长对毕业生们寄予了告别前最后的殷切期望: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希望学生不忘初心、抵制诱惑听从内心的召唤,创造美好人生;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提出“力当先行者”,鼓励复旦学子为中华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承担使命;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导学生“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努力生产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成果……
8月末,高校开学季将至,对于即将走入大学的新生们,人们又会抱以何种期待、做出哪般提醒?实际上,即使你进入的是顶级名校、授课的是国际大师,大学依然提供不了青年人所需的全方位的精神指引,成长为理想的自我仍需更多品质、能力与某种批判视角。国内有北大教授钱理群痛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国外有耶鲁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批评的“优秀的绵羊”。如何在大学校园中学会自律自省,实现自我教育,应是每个准大学生的必修课。
《幸福之路》:“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定是渺小的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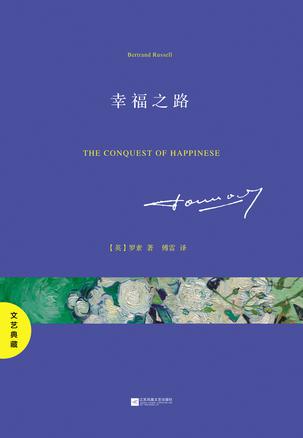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04
忍受烦闷可能是大多数高中生最熟悉的“技能”之一,但这项重要技能会随时间而减弱,尤其是当新生面对着新环境中如潮水般涌来的兴奋和刺激时。但事实上,并非大学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好玩的。
据调查显示,中国高校大学生翘课现象严重,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基础课的逃课率在25%以上,至于文史类公共课则高达50%。即使没有翘课,在课堂上玩手机、发呆、睡觉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上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此早有预见,他在随笔集《幸福之路》中提到,“忍受烦闷的能耐,对于幸福生活是必要的,是应该教给青年人的许多事情之一。”在罗素看来,烦闷的特色之一,是眼前摆着“现状”,想象里又盘旋着“另外一些更愉快的情状”,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坐立不安;而烦闷的另一要素,是一个人的官能无法专注于一事一物。

烦闷又不是命数,既然可以逃避,我们为什么非要忍受它?罗素纵观历史,发现“一切伟大的著作都含有乏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的生活都含有沉闷的努力”,所有伟大的成就都依赖坚持不懈的工作,这种精神贯注的程度使人无法应付狂欢和娱乐。作为一个年青人,如果抱有严肃的人生目标,或许就有必要甘心情愿忍受大量的烦闷;相反,如果心思散漫,纵情逸乐,头脑中很难孕育出建设性的目标。最后,罗素总结说“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定是渺小的一代”,无疑是对当年青年的当头棒喝。
《鲁迅与当代中国》:不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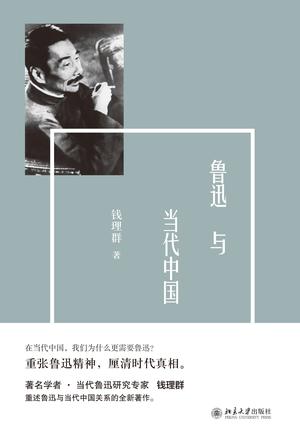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01
2015年,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撰写长文,严厉批判了北大等高校培养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和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有着惊人的世故、老到和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钱理群看来,这群人足够优秀,人格却并不健全,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关怀、悲悯和责任感,只是在名利泥潭中越陷越深,“聪明反被聪明误”。
那么,聪明的年轻人应如何避免高校教育的“精英主义范式”,如何成长为有信仰、有坚守的社会中坚力量?钱理群引导我们看向鲁迅。在《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中,钱理群认为,鲁迅对当下中国最有启发性之处在于他“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精神。鲁迅曾在《华盖集·杂感》中犀利地批判:“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上天去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执着现在”既是正视现实,敢于直面生存困境,又是永不满足现状,坚持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执着地上”要把“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切思考、一切奋斗、努力的出发点与归宿。
钱理群认为鲁迅“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更不是恩赐,而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与底层人民生命的息息相通,是他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应有之义。”而当下的青年人,缺少的正是鲁迅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脊梁”,“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文化,建立血肉联系。这是年轻的一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之根本,”《鲁迅与当代中国》如是说。
《优秀的绵羊》:大学应该创造职业还是塑造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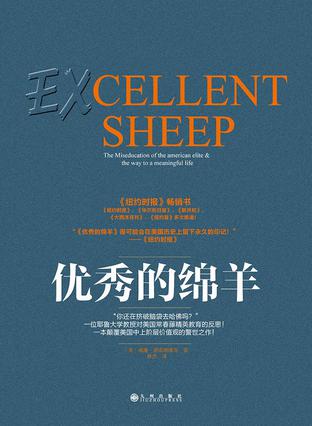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2016-04
在钱理群对中国高校精英教育提出质疑的同年,在大洋彼岸,前耶鲁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也著书强力批判了常青藤名校里“优秀的绵羊”。他指出,美国以“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正在摧毁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所谓“优秀的绵羊”,指的是精英系统培养出的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的,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的学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哈佛杂志》曾形象地描述这样一群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众多常春藤学校的学生们拼命追求完美,正如《黑天鹅》中偏执又暗黑的女主角。
然而,追求完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美国心理学会曾公布了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的报告,报告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即使是那些获奖无数,到了三四十岁时名利双收的人,“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
对此,德雷谢维奇愤怒地表示,“我们这些最好的大学已经忘记了存在的理由是塑造灵魂而不是创造职业。”精英教育首先给了学生们虚假的自我价值,诱导学生认为“成绩优秀等于绝对优秀”,而不优秀和不成功的想法让学生深感恐惧、无所适从。于是,这些被批量生产的精英们害怕冒险,轻易地接受了平庸和安全的诱惑,终其一生不知除了实现别人的期望之外,自己还可以实现些什么自我价值。
这种教育模式直接的后果是,学生们一窝蜂涌向了经济专业。德雷谢维奇在书中提到,英国文学专业令人避而远之,目前只能吸引3%的大学生;相较之下,商科超过了所有艺术和文科总和的一半,吸引了21%的大学生。此外,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是有50%的哈佛毕业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在过去的30年,我们几乎一直在呐喊金钱创造快乐,并对争取个人名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现在大学生对大学的认识就是职业发展的跳板。”
这本书虽然针对欧美名校弊病著写,但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未尝没有借鉴意义。何为精英?精英何为?亦是需要我们在校园内外长期反思的问题。
《功利教育批判》:通过人文教育学会批判、想象与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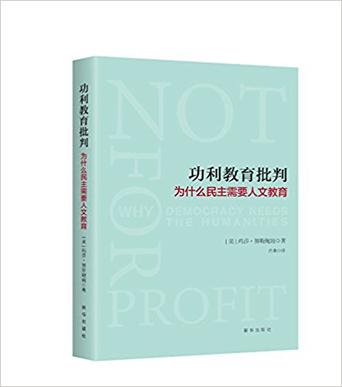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2017-5
如果说《优秀的绵羊》直指精英教育弊病,那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的《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则直接对全世界的教育体系举起了手术刀。她从根本上否定了当下流行的观点,即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在这本书里,努斯鲍姆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不重视人文教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迄今(奥巴马)一直在强调个人收入和国家收入的增长,并提出我们需要的教育应为这两个目标服务”;她揭露了当今英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商业部的一部分”,“学术研究被描述成了一种叫卖活动,却无人对这种贬损之言提出抗议”;她还指出,当今印度的大学生“只学一些为就业准备的技能,学院不鼓励学生掌握独立研究的技能”。
在努斯鲍姆看来,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三种能力:一是批判思维能力,二是想象能力,三是同情能力——这些能力才是造就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关键。能够独立思考、批判传统、理解他人苦难和成就的意义十分重要,人文教育恰恰能够唤醒年轻人的冷漠,让他们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保持清醒。教育的目的是训练思维,而不是造就绵羊般的顺从。想象能力和同情能力可谓一体两面,“是指想象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鞋子时的感受能力,是有智慧的读者阅读别人的故事的能力,是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可能产生的情感、希望和欲望的能力”。而培养这些能力同样需要人文教育的知识背景和系统训练。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对一个人而言,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努斯鲍姆正向全世界的大学生发出呼吁:在人文教育的怀抱里学会批判、学会想象、学会同情,给予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社会真正的自由。
《阅读经典》:识别知识与智慧,对愚蠢保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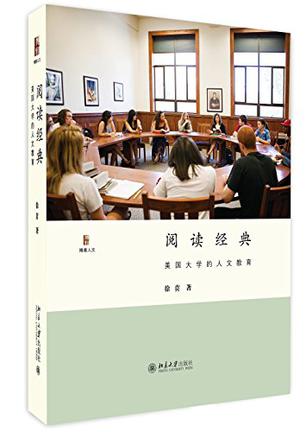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与《功利教育批判》一样,《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也是一本支持人文教育的著作。作者徐贲结合自己在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的多年经验,从一本书、一堂课讲起,分享了自己关于人文教育的思考和体验。
徐贲非常认同前耶鲁大学校长吉亚玛提(A. Bartlett Giamatti)的看法:“人文教育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而教学行动则又是人文教育的关键。”在课堂上,徐贲带领学生们从古希腊、罗马读起,包含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理性主义、18世纪启蒙思想,一直读到19、20世纪的现代经典,亚里士多德、蒙田、马基雅维利、列奥·施特劳斯等大师著作全都赫然在列。
面对这样一份艰难而广博的书单,学生应该怎样阅读呢?徐贲认为,经典阅读要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知识,二是方法。知识的习得不仅包括书本里提到的信息,还包括思考、提问、讨论和表述的能力,这些也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在方法上,徐贲指出“人文教育的阅读是教育和训练的结果,不是一个人本能自发或自然就会的”,既需要阅读方法、技巧的细致训练和反复运用,也需要阅读联想、想象和创新力的引导和培养。同时,人文阅读要有足够的多样性,戏剧、史诗、小说、宗教读物、哲学对话或论述、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和一些被归类为“科学”的著作,都应该包含其中。最重要的是,阅读经典必须面对当下,要有针对现实的问题意识。
在徐贲看来,阅读经典重要的不是掌握专业知识,而是感受人生智慧,“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愚蠢,许多有知识的人士因没有智慧而愚蠢。人文教育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不容易上当受骗。”
在《我们到底该读什么书》中,徐贲再次强调,“远离愚蠢对年轻人尤其不易,因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青年时期都是人生中愚蠢的高发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