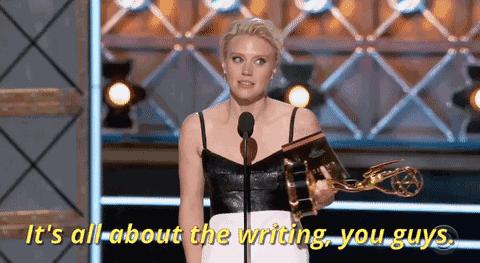

“事实上并没有两种性别。只有一个性别:女性;‘男性’不是一个性别,因为男性不是一个男性,而是普遍的。”
——维蒂格
一群男人,代词用“他们”;一群女人,代词是“她们”;但如果这一群女人中多了一个男人,那代词就变成了“他们”。
可能你会想,打住,这不过是语法规则罢了,这里的“他”明明就是中性的,而且这样用比较方便不是吗?但问题似乎并不在于方便与否,而是在于为什么为了方便表达我们选择了“他”而不是“她”或“TA”。
我们每日使用的语言,真的是中性、中立的吗?

在今天的法国,一场关于语言与性别的论战已经持续了快两个月,其“罪魁祸首”就是一种与传统语法相违背的书写方式——“含她书写”(écriture inclusive)。
什么是含她书写呢?这里应该先介绍一下法语的语法,但法语语法实在太复杂,因此这里只简要列出三点:
1, 法语里所有名词都被指派了“性别”,香蕉是阴性,菠萝是阳性,吃饭桌是阴性,书桌是阳性,“工人(ouvrier)”这样的职业和头衔也分为“男工人(ouvrier)”和“女工人(ouvrière)”;
2, 如果同时提到阴性名词和阳性名词,代词就用阳性(“他们”),这点和中文一样;
3, 有些职业和头衔因为历史上少有女性成员,在正统法语中便根本没有阴性形式,比如“教师(professeur)”、“作家(écrivain)”、“主席(président)”。
含她书写希望弥补法语中阴性的缺失和“被代表”。大体上说,它有三条约定:
1, 教师、作家这样的词也得有阴性形式,于是就有了“新词”professeure和écrivaine;
2, 提到有男有女的集体时,要同时使用阴性和阳性名词,比如说一群有男有女的教师可以写作professeur e s。
3, 不使用“男人(Homme)”或“女人(Femme)”这种词来代表全人类,这一点可以类比英文中的men和women,英文中无人区是no man’s land,法语也有“droit de l’homme(男人的权利)”来代表人权。,含她书写就建议使用“droit humain(人类的权利)”。
事实上,针对语言的性别革命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就曾鼓励使用阴性化的职业和头衔,民间和学术界对于法语中性化的呼声也未曾断绝。
在含她书写登场之前,法语中就已经出现了中性语言(langage épicène)、形容词性数的就近配合(règle de proximité)等书写方式,它们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减弱法语语法中的“阳性至上”(甚至是“复数至上”),含她书写只是它们的全新升级版。

近些年来,这类更为性别中立的书写规则已经悄然出现在了各种网站和媒体上。今年上半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同样有候选人使用过它们。
2015年的时候,法国男女平等高级委员会曾出版了一份《含她书写手册》,专门介绍这种新新书写方式。不过,这些都没引起什么波澜。
直到今年9月末,有人发现法国著名的阿提埃出版社(Hatier)在一套小学生教材中使用了含她书写,这才引起轩然大波。
最大牌的反对者莫过于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们。这个机构一大重要的职责就是规范法语,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只不过法兰西学术院历史更悠久,院士们的地位也更高,甚至被称为“不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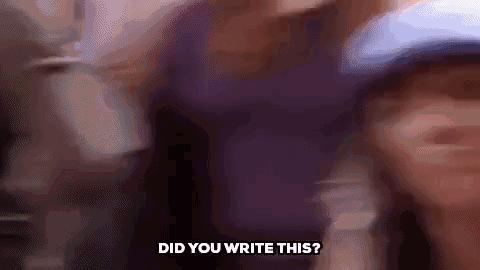
对于含她书写,“不朽者”们在10月末发表了一篇声明,指责含她书写让法语变得难以辨读,加大了学习法语的难度(好像现在挺简单似的),破坏了珍贵的书写遗产,乃至将法语置于了“致命危险”之中。
在法语的“正统性”上,几百年来学术院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变化,毕竟正是他们在17世纪让阳性至上正式被写入法语语法。

没错,法语语法并非一成不变。中世纪时,法语的规则还不是那么统一,打个比方说,一群男男女女即能写成“他们”也能写成“她们”,都是正确写法。
后来,出于政治需要,黎塞留公爵创立了法兰西学术院以统一法语语法,法语的阳性至上正是在这个时期被确定下来。法兰西学术院第一位成员德沃格拉斯男爵在1647年写到:“阳性更为高贵,故应当在每次阴性与阳性同时出现时占据主导。”
在1767年,另一位著名语法学家博泽更解释道:“由于男性较女性更为优越,所以阳性也被公认比阴性更高贵。”
让我们回到现代。除了玷污老祖宗的文化遗产、把法语变得更复杂、读者看着不顺眼之外,一些反对者还提出这种书写方式只是形式主义,对性别平等完全没有帮助。

真的完全没有帮助吗?
让我们来看看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所做的一次调查,他们将受访者分为三组,以三种不同的提问方式提出同样的一组问题,以观察含她书写对受访者的影响。他们要求受访者看到问题后写出最先想到的答案,这三种提问方式分别是:
-请列举两位著名作家(écrivains)——传统语法;
-请列举两位著名男作家(écrivains)或女作家(écrivaines)——含她书写;
-请列举两位因写作出名的人物——中性语言。
第一组受访者中只有12%列举出至少一位女性作家,第三组有16%,而第二组中有24%列举了至少一位女作家,是第一组的两倍。
答案不言而喻。一样事物如果不被命名,就不存在。但如果我们谈论它,叫出它的名字,它就从能从暗处走出来。

前些日子我在翻译一篇关于非洲的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的文章,在翻译之余,我决心用译文尝试一下含她书写。最开始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毕竟规则就那么三条摆在那儿,但后来我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比如说,文章提到非洲赌场中络绎不绝的中国赌客,读中文的时候我们便将所有赌客默认为男性,但事实上那里有没有女性呢?我不知道,我知道非洲的中国企业里有女性员工,可她们会去赌场吗?我不知道,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未被提及。
好吧,假设她们无聊时也会随着男同事去赌场玩一玩,文章另一处提到的“中国淘金者”呢?他们中会有女性脸孔吗?
我小心翼翼地在网上查了查,令我自己也吃了一惊的是,真的有一篇新闻提到了在非洲淘金的中国女性。
的确,语法规则并不难,但我却时时刻刻都在与原作者和我本身的阳性至上意识缠斗不休。在进行含她书写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就像挖矿人一样,一点一点发现这些女性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痕迹。
这样看来,虽然中文不像法语那样分为阴阳性,但从一开始我们自己就将这些职业和头衔贴上了性别的标签:赌客是男的,性工作者是女的,主席是男的,秘书是女的。在百度中搜索“博士”有7千4百万个结果,“女博士”1千6百万个,而“男博士”只有6百万个。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家维蒂格曾说,事实上并没有两种性别,只有一个性别:女性;“男性”不是一个性别,因为男性不是一个男性,而是普遍的。
法语、中文,都是如此。在人类千百年的文化史中,男性掌握了绝大部分创造和完善语言的机会,也将男性主体带进了语言和语法中。
“她”之于“他”,就像是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的那根肋骨,就像100个蓝精灵中唯一的那个蓝妹妹。“她”是女性,“她”除了女性什么也不是。
我们在塑造语言的同时,语言也在塑造我们。含她书写是对语言,对日常生活,也是人的意识的改造。可以说它是最微不足道的,也是最了不起的。
参考资料:
https://bibliobs.nouvelobs.com/actualites/20171026.OBS6579/declaration-de-l-academie-francaise-sur-l-ecriture-dite-inclusive.html
https://bibliobs.nouvelobs.com/idees/20171110.OBS7212/ecriture-inclusive-en-francais-la-langue-reste-attachee-au-phallus.html
http://www.europe1.fr/societe/le-masculin-lemporte-sur-le-feminin-une-regle-qui-na-pas-toujours-existe-3485978
http://www.leparisien.fr/societe/ecriture-inclusive-la-langue-integrait-davantage-les-femmes-il-y-a-400-ans-09-11-2017-7383555.php
https://www.actualitte.com/article/monde-edition/3-francais-sur-4-se-disent-favorables-a-l-ecriture-inclusive/85395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Fo7-Qt9LXAhVDu48KHZ0MCI8QFgguMAE&url=https%3A%2F%2Ffr.wikipedia.org%2Fwiki%2FF%25C3%25A9minisation_en_fran%25C3%25A7ais&usg=AOvVaw30h_IRcZTJFLW9MUbItTbh
https://fr.wikipedia.org/wiki/R%C3%A8gle_de_proximit%C3%A9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27-international-African-Chinese-sexworker/
注: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啖先且
翻译专业在读,关注性别问题,不想出远门,想在太阳系老老实实呆一辈子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