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科尔兰斯基很善于跟踪著名食材的流变进行写作。在《一条改变历史的鱼:鳕鱼往事》中,他讲述了鳕鱼“部落”的迁徙历史,其中涉及到的北欧渔业的兴衰、气候变化导致的洋流改变(或者相反),以及鳕鱼们做出的令人惊讶的反应,颇能开人心智。至少,当一条产自挪威的深海鳕鱼,被厨师们端上亚洲腹地某个城市酒店的餐桌时,你要知道,眼前这盘看似鲜嫩可口的佳肴,一生充满了坎坷的传奇。
同样的手法在《万用之物——盐的故事》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体现——这是科尔兰斯基的狡黠之处——由加泰罗尼亚的一块盐石切入,从中国四川到埃及尼罗河,从奥地利迪恩堡到罗马帝国,从德意志哈布斯堡到英格兰利物浦,马克·科尔兰斯基讲述了盐的悲欢。
2
许多被时间沉淀的物质,都能在历史的深处发出喃喃自语。所以,这个世界的善听者,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即便周遭沉寂无声,即便周遭喧嚣如一百万匹战马奔腾。马克·科尔兰斯基无疑是鳕鱼或盐粒家族的善听者。这可能与他早年的厨师经历有关。当鳕鱼或盐粒的声音足够大时,他所做的无非是描摹一粒盐的刺激性旅行。
在时间的印记里,细小的盐,当然不是宇宙中可有可无的尘沙。它们在时间的延宕之中凛然沉静,与铁与铜,与煤块与石油,与枯木与败叶,与被糟践污染仍被争夺的水源,一起变得冷峻坚硬。
体察一粒盐的旅行,不会让人生出时间向好的感叹。因为事涉生存。因为事涉生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各种形而上的意义开始积聚与附丽。然后,不言而喻地指向了战争。
细小的盐粒,因为晶莹而具有美学的意义。但和朴实而丑陋的生存主义相比,美学算个蛋?
3
与某些事物一样,一粒盐在旅行中也展示了困惑。
第一个困惑来自“公众之盐”。我不太喜欢这一意义上的“盐"。如果罗马史确如马克·科尔兰斯基所说,是一部拥有特权的贵族与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庶民之间进行持久斗争的历史的话,“公众之盐”无非是贵族们对于占有的态度上的让渡。哦呵,这个话题不宜继续深入。
第二个困惑来自《盐铁论》中的”盐“。显然,我对这一意义的“盐”也有情感上的抵触。当国家主义被辩论与争议时,自然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权力形态的玩偶,或者,生存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意识形态的恩赐。这种可能一旦生发,结果大约就与民生福祉相去万里。
还是说一下地理上的盐。
中国四川。小城自贡。可以从深井中提取的盐。盐是怎么找到那种与水与新鲜的蔬菜不可或离的依附的?是的泡菜。被禁锢的岁月。中国人为什么会从根性上喜欢这种坛子里的浸泡以及看起来面目全非的性状改变?被禁锢的岁月。多么深刻又酸楚的回味。
意大利。古代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将士们开疆拓土,更多只是为了扩展盐场的版图。他们在陶罐中煮沸海盐,然后再把陶罐打碎。这一点和远在东方的中国人多么不同。
文明在苏醒的一刹那,就以差异性存在。
4
在地理意义上,盐粒们似乎是自动团结起来的,它们静默地连成一片,成为井、成为矿、成为湖、成为海。
盐当然是那种很执拗的物质,具有执拗而不盲从的品格。如果有什么让它改变性味,我想,应该是糖。糖在外观和内涵上,具有和盐相互补益的特质。君子和而不同。或者,糖干脆就是盐的白粉知己。以相互温存而遁形,或以相互毒杀而消融。
历史上的人群流变,与盐粒的迁徙何其相似。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吸收盐类而拒绝糖分的灵魂才能够堪破世事。可能,这正是他们能够成为世间传说的奥秘。
圣雄甘地。“穿着乞丐衣衫的伟大灵魂”。1930年,为抗议触及印度所有种姓生活的英国暴政,与78名追随者徒步240英里来到古吉拉特的丹迪海边。

“他迈着纤细的腿,小心探索到海滩,到达有着厚厚盐壳的地点。然后,弯下腰挖起了一大块儿盐,从而违犯了英国盐法。”
“万岁,解救者!”一名朝圣者这样呼喊。
——只有我知道,在甘地们俯下身子的一刹那,盐也完成了自身的解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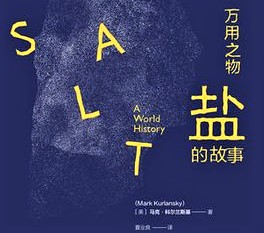
&万用之物——盐的故事/(美)马克·科尔兰斯基/著 夏业良/译 中信出版201701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