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几秒钟,WhatsApp的新消息推送通知就会点亮我(指本文作者英国电视记者、作家林齐·希尔瑟姆)的iPhone屏幕。这些消息来自一个讨论组,里面既有大马士革郊外东古塔地区的医生,也有全世界各地的记者。我几乎能实时关注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进攻的消息:“三个小时前,俄罗斯飞机在东古塔地区跟踪救护车辆,并对救护车和医院发动袭击”;“哈姆扎医生:目前为止我已经治疗了29个病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儿童”。图像资料配有阿拉伯语和英语注释:“本地居民在房子下面挖掘避难所的照片。”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国际报纸的记者利用这个讨论组确认伤亡数字,核实袭击地点。另外,广播媒体还会利用Skype在战区进行采访报道。
记者们小心翼翼地筛选社交媒体上的证词、视频和照片,与政府宣传、卫星图像等其他可用的消息来源交叉比对。这是21世纪冲突报道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被誉为首个现代战地记者,以文章《轻骑兵的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而闻名天下。在这篇报道中,他将在克里米亚的英国骑兵的进攻描绘成“战争的自豪感和荣耀的光芒与清晨阳光交相辉映”。然而,如今的战地记者与拉塞尔截然不同。
拉塞尔认为自己是“不幸部落的悲惨父母”,而蹲在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伦敦电脑前守候新闻的记者的确也应该感到不幸。2011年,在利比亚报道战事的记者可以在早上驱车前往战场,晚上平安地回到班加西的酒店。因为大部分战斗都发生在主要的沿海公路。2003年,在伊拉克报道战事的记者可以跟随长驱直入的西方军队获取第一手消息,也可以留在巴格达观察萨达姆·侯赛因最后的负隅抵抗。虽然需要其他人补充信息,但你总是能亲眼目睹很多细节。说起1939年夏末的一天,人们心中可能充满更多怀旧之情:刚刚加入《每日电讯报》不到一周的年轻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在波兰城市卡托维兹(Katowice)借走英国领事的汽车,顺利通过德军边防哨所。此时一阵狂风将德国人绑在路边的粗麻布刮起,她恰巧发现隐藏在伪装下的十个准备向波兰发动闪电战的德国装甲师。
叙利亚的情况则不相同。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禁止记者和救援人员进入,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在该国北部解决与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的长期冲突,丝毫不顾及平民的安危。显然,叙利亚政府从中学到了经验教训——他们只给极少数记者颁发签证,而且全程监控入境记者的行踪。最近,叙利亚政府试图迫使前来报道的记者签署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中写道:“如果我发表虚假报道或者教唆挑起宗派主义冲突,叙利亚新闻情报部门有权对我采取法律手段,并在我的国家或我所居住的国家对我提起诉讼。”
最初,记者通过走私者进入反政府军所占领的区域。但后来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对这个区域进行猛烈轰炸和炮击,ISIS也展开报复性活动,因此在现场的战地记者处境变得尤为危险。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列出2011年以来在叙利亚死亡的115名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2012年2月,她在霍姆斯市(Homs)的巴巴艾默区采访。叙利亚政府军利用迫击炮摧毁了反政府军的新闻中心,导致科尔文不幸身亡。同年,美国记者詹姆斯·弗雷(James Foley)被ISIS绑架。2013年,美国记者史蒂文·萨特洛夫(Steven Sotloff)也落入ISIS之手。两人随后都被杀害。从那时起,大部分外国记者只在土耳其边境地区逗留,针对叙利亚难民、士兵和走私者进行采访。2017年ISIS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外国记者偶尔也会深入反政府军占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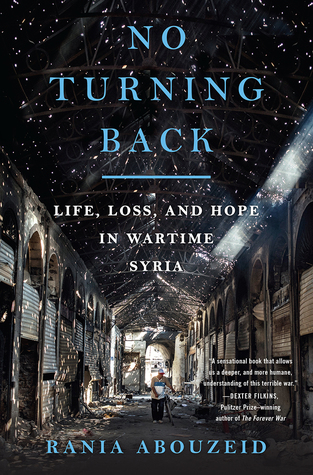
保护记者委员会列出的牺牲记者名单中,叙利亚记者的数量要比外国记者多,但他们的名字却少有人知。无名的叙利亚记者和著名的外国战地记者、幸存者以及此前的战争英雄都冒着生命危险为世界报道前线消息,但他们之间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严重影响着现代战地报道的发展。为《纽约客》和其他媒体撰写文章的黎巴嫩裔澳大利亚自由记者拉尼亚·阿布泽德(Rania Abouzeid)在《无路可退:叙利亚战火中生命、损失和希望》(No Turning Back: Life, Loss, and Hope in Wartime Syria)一书开篇就提到这个问题。她写道“这本书不是另一本记者的战地日记。我去叙利亚观察、调查、倾听——不是为了和能为自己发声的人交谈。他们不是沉默的人。这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他们的故事。”这句话可能让那些认为穿着防弹背心在战区待了一周时间并且觉得自己很厉害的电视记者(我本人就是)感到不悦。为了触及痛处,她补充道:“我自己负责设备、翻译、转录、后勤、研究和事实确认工作。”这本书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洞察力的战地记者作品,突出个体故事的同时不忘描写叙利亚边境的现状和历史。

西方白人记者本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彩的作品,但阿布泽德的身份在新闻报道采编过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她兼具记者和作家的身份与能力。七年战争冲突期间,她跟随数十位叙利亚人进行采访,像对待乐高积木一样把他们的故事整合在一起,每一个故事都与下一个故事存在联系,直到读者面前浮现出完整的故事构架。她喜欢与采访对象一起闲逛,安静地观察和倾听。经过很久之后,采访对象甚至会忘记她的存在。女性的身份作用巨大,因为人们不将她视为威胁。她的存在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比如说,她一定是亲眼目睹了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叙利亚反政府团体战士穆罕默德(Mohammed)和他妻子莎拉(Sara)的家庭生活:
祷告结束后,她的丈夫回到家并开始洗澡。他从浴室里大喊:“把指甲刀递给我!”
莎拉怒吼道:“指甲刀在哪?”.
“手榴弹边上。”他回答说。莎拉在胡桃木颜色的陈列柜里寻找着。她拿出一瓶润肤膏,开始往手上涂抹。
她说:“看看我的手!我的指甲什么时候像这样过?我感觉自己好像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在家要做各种事情,全部要靠双手完成——洗衣服、刷盘子。我以前喜欢用黄瓜敷脸,中午睡午觉,梳理头发,涂抹化妆品。现在,整个生活都变了。”
这是一场战争,但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战争。在另一个场合,阿布泽德与一户人家一同偷偷越国边境进入土耳其。虽然我们知道她在现场(“我们七个人蜷缩在走私犯的车内”),但她却从未重点强调自己所面对的威胁。她用全部文字描绘与自己同行的一家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女儿——露哈(Ruha)。露哈的名字在书中一直出现,而阿布泽德也持续跟踪她的发展,看着她从崇拜父亲(最近加入家乡萨拉奎布的反政府组织)的小女孩成长为开始质疑父亲选择的青少年。
阿布泽德很少强调自己的存在,其中有一次是土耳其边境的救援人员让她帮忙在会议中为两位英国“外交官”进行翻译。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反叛军成员穆罕默德冒充成难民,也出现在现场。英国外交官想用情报换取食物和帐篷,因此阿布泽德能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他们却不知道阿布泽德是记者。在那一瞬间,阿布泽德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另一个带有虚假身份的人。在叙利亚冲突中,欺骗和伪装可能是帮助人们生存下来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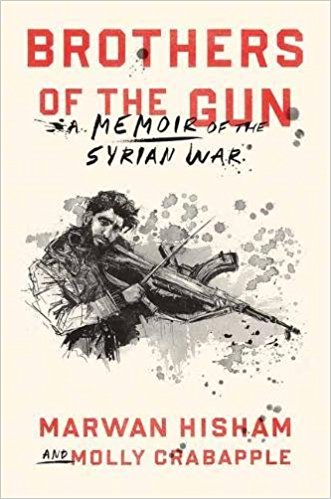
如果说阿布泽德是冒充局内人的局外人,那么马尔万·希沙姆(Marwan Hisham)就是学会用局外人也能理解的方式讲述故事的局内人。ISIS占领城市时,希沙姆正在拉卡市(Raqqa)担任英语老师。从那以后,他开始在Twitter上用英语发布动态。当然,马尔万·希沙姆并不是他的真名。这是个危险的行当,但他却一直没有被抓。他与艺术家莫莉·克莱伯艾波(Molly Crabapple)合作,共同完成了《枪支兄弟:叙利亚战争回忆录》(Brothers of the Gun: A Memoir of the Syrian War)一书。希沙姆最初与克莱伯艾波在Twitter上相遇,当时希沙姆住在拉卡,而克莱伯艾波则住在纽约。他用从朋友处要来的智能手机拍摄照片,而克莱伯艾波根据这些照片创作绘画。
他们最初的作品发表在《名利场》上。如希沙姆所言,如果被ISIS发现这种“艺术犯罪行为”,他可能会被处决。吊在路灯上的尸体、端着巨大步枪的小孩、逃离碎石遍地街头的人们……画笔渲染出的精美图片让人感到不安和忧虑。克莱伯艾波喜欢使用充满生机的颜色勾勒画面,但有时候杂志刊登的原始图片中也可见到苍白的色调。在出版的图书中,她用精心涂污的黑白插图引发读者更多思考。封面插图中有一把小提琴,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一把AK47冲锋枪。
在阿勒波(Aleppo)附近的村庄上完宗教学校后,希沙姆开始沉迷于欧洲足球和文学。他是西方读者理想的对话者。但是,他和朋友们站起来反抗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镇压的原因却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们是拉卡市的数量极少的少数派。在邻居看来,我们的价值观非常危险,堪称是西方的非伊斯兰教代理人。
草根阶级、民主、选举权尊重民主选举结果、将选举结果作为代表权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大多数叙利亚人看来,还有比这些词语更陌生的东西吗?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我们和朋友们在催泪弹中向防暴警察呼喊的价值观,真的没有普世性吗?也许它们是少数地区的风俗,是欧洲都市大学里研究出来的书面结论。也许它们虚无缥缈,像鬼魂一样脆弱。
西方读者也许会将希沙姆堪称坚守信仰的英雄,但他发现没有人能在战争面前保持纯粹。亲密的朋友背叛自己,试图为身边的堕落寻找理由。为了生存,每个人都要妥协,希沙姆也不例外。在拉卡网吧的工作让他顺利向外界传递消息,但却免不了要为前来上网的ISIS分子服务。圣战分子带着两个惊慌失措的雅兹迪女奴前来时,他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为自己在这里工作而感到愧疚。这种感觉将陪伴我终生。”穿越边境进入土耳其境内时,希沙姆帮助一对难民夫妇搬运沉重的袋子。但是被土耳其边境人员遣返后,他没有在再次偷渡前看到那对夫妇的身影。他写道:“对于富有同情心和脆弱的人来说,战争是残酷的。我做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我把他们和他们的袋子抛在了身后。”
叙利亚战争爆发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遇到危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拿起手机录像。无论是美国校园枪击案还是大马士革的游行示威,智能手机都是人们面对突发情况的第一选择。2011年,希沙姆和身处叙利亚北部地区朋友拍下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并上传到网络,让世界看到叙利亚人民的反抗行动。阿布泽德在书中提到一个住在拉斯坦镇(位于大马士革和阿勒波之间)的年轻人,他也将拍摄示威活动视频并上传作为自己反抗政府的起点。此类视频的即时性极强。在叙利亚,有时候外国记者只能靠这些视频判断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判断既有视频真实性已经成为记者们必备的技能。克里斯蒂安·特里伯特(Christiaan Triebert)和哈迪·哈提卜(Hadi Al-Khatib)在《战时新闻工作》(Journalism in Times of War)一书中的“数字夏洛克”章节中写道:“叙利亚冲突开始之后,网上的相关视频总时长比冲突爆发距今的时间还长。”他们在书中描写了一种叫反向图片搜索的验证技术。通过这种手段,你能确定据称今天拍摄于东古塔地区的视频并不是去年拍摄于费卢杰(Fallujah)的假货。

人权组织和记者使用网络工具的频率越来越高。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研发出YouTube DataViewer软件,使得用户能够确认一段视频上传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并对其完成反向图片搜索。其他组织也开发出各种定位手段。在伦敦,我工作的新闻编辑部里有一名说阿拉伯语的记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梳理各种材料,确认真实性并将成品发布到电视新闻和网络上。他从叙利亚士兵处获取信息,还与数十位活动分子和反政府组织成员保持联系,进而建立起可靠的远距离消息来源。
《战时新闻工作》中描写的记者采访并没有质疑传统的采编手段:亲眼目睹,发掘消息来源,尽可能多得倾听各方观点,像科尔文说的那样“试着在政治宣传的沙暴中发现真相”。但是,一些人对西方世界假定中的“平衡”提出质疑。叙利亚记者扎伊娜·阿瑞姆(Zaina Erhaim)曾在阿勒波进行过直播报道。她说自己和其他叙利亚新闻人已经醒悟,因为自己对阿萨德政权暴行的揭露根本无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称自己是叙利亚“新闻活动分子”。阿瑞姆写道:“大多数人不认为叙利亚新闻活动分子是真正的记者,也不认为我们是国际媒体的消息来源。”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客观”和“中立”。在叙利亚的战地报道中,“客观”的意义是什么?报道叙利亚战争时保持“客观”是否意味着对外披露战犯和他的政治宣传,允许叙利亚政府以合理的借口掩盖向平民区、学校和医院投递炸弹的行为?
大多数报道叙利亚问题的西方媒体记者都清楚,阿萨德政权犯下骇人听闻的累累暴行。但是,叙利亚的“新闻活动分子”只想向外界展示能证明自己观点的事实。炸弹爆炸和平民受伤的视频并非叙利亚政府宣传部门所说的伪造品,但“新闻活动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获得国际社会同情——国际社会的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叙利亚问题走势——他们最好只报道平民,尤其是儿童受伤的事件。此外,反政府军战士——不管是伊斯兰教主义者还是世俗派——不喜欢记者的镜头,而且他们手中握有枪支。网上的视频显示反政府军不断开火,取得节节胜利。但是,视频没有体现出反政府军内部争吵不断和作战失利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也许是真相,但并非全部真相。正因如此,大量西方读者和观众才会选择阅读他们认为观点公正的外国战地记者的报道。
最好的战地记者能深入战区,用带有怀疑色彩和距离感的眼光审视一切,帮助观众理解现在叙利亚冲突与此前发生战争的不同以及地缘政治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琳赛·帕尔默(Lindsay Palmer)在学术研究《报道的产生:911事件后的战地报道》(Becoming the Story: War Correspondents since 9/11)中指出,人们越来越关注战地记者,而非战争本身。她写道:“主流英语新闻机构常常给西方白人记者设置好定位,将他们视为闹剧中的英雄。”直到最近,美国报纸才允许记者在报到时说“我看见”,而不是“这位记者看到”或者“目击者看到”。新闻报道的个性化已经成为欧美各国的发展趋势。
帕尔默对鲍勃·伍德拉夫(Bob Woodruff)的分析很好地证明了她的观点。伍德拉夫是《ABC新闻》的记者和主持人,2006年在伊拉克随美军报道时受伤。帕尔默发现新闻工作中存在负面政治力量——在她看来,个人主义永远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值得推崇和赞赏。她尖锐地批评以伊拉克小人物为出发点的新闻报道以及“伍德拉夫公然与自己报道中的美军士兵结盟”的做法。专业性的问题姑且不谈——记者只负责讲述故事的原貌,并不添油加醋地“叙述”故事——帕尔默发现媒体鼓励西方观众和读者对记者产生共鸣,将记者视为英雄、受害者和烈士。在她看来,这种做法的危害性非常极大。
虽然这类情况在纸媒记者身上不算严重,但玛丽·科尔文在巴巴艾默区不幸身亡引发的关注远远超过叙利亚摄影师拉米·赛义德(Rami al-Sayed)的死讯。其实,赛义德在科尔文被杀前一天也死在同一个新闻中心。这件事理解起来不难:科尔文是国际知名记者,因为在斯里兰卡被政府军手榴弹炸瞎眼睛后佩戴眼罩而闻名。相比之下,赛义德只是从业时间几个月的摄影师,更像是个活跃分子,而非记者。但是在帕尔默看来,赛义德拍摄的视频“在主流英语媒体报道2011-2012年霍姆斯战争冲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赛义德和科尔文的死亡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战地记者都非常熟悉的等级制度。
帕尔默表示,非西方记者——其中很多人是自由记者——经常遭到轻视,获得的报酬也不够多。同时他们接受的训练较少,没有佩戴诸如防弹衣之类的安全设备。生活在当地的摄影师和特约记者常常感觉自己只是为西方记者做嫁衣。如果政府认为报道失实或者损害本国形象,西方记者可以载誉而归,他们却要面对政府的怒火。外国记者对情况的了解不如本地记者,但新闻知识的多少并不是编辑评判新闻优劣程度的唯一标准。电视台的高管们脑海中存在一种传统观点——记者必须与观众建立联系。因此伍德拉夫这样的明星记者才会在一场又一场冲突中出现,空降新闻现场进行报道。常看电视的观众只对部分出镜记者有信任感,用其他说阿拉伯语或者了解更多现场情况的人替代原有记者并不能立即让观众买账。常读报纸的读者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出现改变。年轻的观众不关心出镜记者是谁,也不关心主播是谁。他们喜欢从移动端收看新闻,移动端的新闻多配有字幕,而不是旁白。面对战地报道,年轻观众更喜欢当地新闻活跃分子和记者原始而引人注目的视频,或者救援者头盔摄像头拍摄的炸弹爆炸和从废墟中营救儿童的画面。总体来看,网上的观众似乎不介意视频是否由驻扎在现场的记者报道传播。因为要与电子游戏和Netflix的电视剧竞争,因此媒体需要吸引眼球的战地视频,而不是冷静的分析阐述。明星战地记者顶着炮火站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时代或许即将结束。
西方媒体裁撤大量海外机构,以此节约经费。他们不再派驻驻外记者,而是想用数字新闻报道替代。任何记者都不能忽视WhatsApp、YouTube和无数现代化传播方式的威力,因为它们能实时直播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故事。但是,“身处现场”依旧非常重要。阿拉伯裔美国记者对帕尔默表示,他们在新闻报道时具有巨大优势。这些人对自己的文化了如指掌,语言优势也能帮他们了解详情:表达同情(“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阿拉伯人,我理解你”);假装不理解阿拉伯语,希望对方能更加大胆直白地用阿拉伯语讨论;了解背景知识,比其他记者更快弄清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还理解西方观众的文化背景,也能和西方观众顺畅交流。
在未来的战地报道中,具有多国背景的记者——叙利亚裔美国人、黎巴嫩裔英国人、伊朗裔法国人、尼日利亚裔加拿大人——可能会更加谦虚低调。最初在Twitter上利用插图描绘出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后,希沙姆和克莱伯艾波展现了讲述故事新渠道的潜在威力。阿布泽德弱化了自己的勇气和能力,为的是写出使人身临其境的报道。她知道,自己所遇见和描写人物的体验才是重中之重。
霍林沃思曾经说:“我喜欢微风的味道。但你在电脑前闻不到它。”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