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处女泉》时,李安形容自己“被夺走了处子之身”;伍迪·艾伦在看了伯格曼的《野草莓》后,锁定了对他的终身痴迷,“他的电影将被证明与伟大的欧洲文学不相上下。”今天,是英格玛·伯格曼的百年诞辰。这位与费里尼、塔可夫斯基并称为“圣三位一体”的瑞典电影大师,其成就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伯格曼式”已然成为了影史上的一种标志、一支标杆。
伯格曼在电影中关注与人类情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从宗教信仰到婚姻家庭,对他而言,“电影艺术能无限接近生活的本质。”同时,他把梦视作“电影的自然状态”,以梦境的模糊性和感性特质触摸观者的情感和记忆,擅长通过运用面部特写和凝视,再现情感的每一细节,追问人自身存在的意义。
童年经历的一切对伯格曼有着重要影响。在他唯一的自传《魔灯》中,他详细书写了童年生活的细节以及童年对其成年生活与创作的影响,他在纪录片《伯格曼论电影和生活》中亦坦言:“回想我成年后所做的一切,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的童年里都有迹可循……我一直在与我的童年对话。”童年是理解他的一把钥匙:对周遭事物的感受和想象,对家庭内部不和谐的体会以及与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来自童年时期的经验在他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为了一种“伯格曼式”的印记。
在晚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伯格曼说,“我58岁那年才走出青春期。”表面来看,这似乎是说,伯格曼在58岁时才终于挣脱了少年经历的影响。但他在此后拍摄的电影——尤其是《芬尼与亚历山大》——却更详细地回溯了自己的童年,“芬尼和亚历山大都是孩提时代伯格曼的化身,”伯格曼曾这样自我评价。那么,“走出青春期”只是一句随口之言,还是表明在58岁这一节点上伯格曼的生活经历了某些转折,或是有着其他含义?对于长久沉浸在童年经验中、矛盾性地自我撕扯的伯格曼而言,“走出”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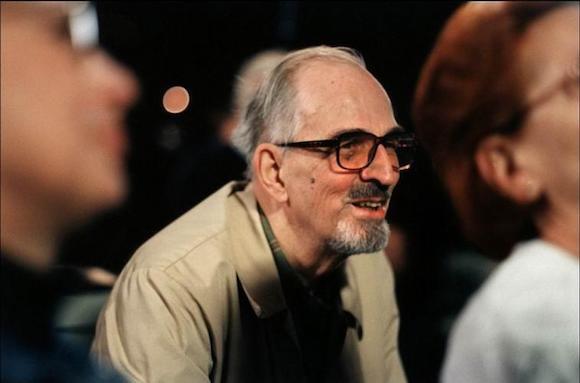
一、“伯格曼式”=创作力的枯竭?

1976年,在58岁那年,伯格曼陷入了逃税丑闻。1月,当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排练《死亡之舞》时,被警方以逃税的名义逮捕。事实是,伯格曼把与财务相关的一切交给助手们,对此毫不知情。此事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他的精神崩溃,终止手上工作,住院接受治疗。同年3月,逃税起诉被撤销,事件由罪行转为一般税务案件,伯格曼得以暂时放松。
在得知逃税起诉撤回的当晚,伯格曼彻夜难眠,产生了一个“拍一部讲述母女关系电影”的灵感,“女儿给予母亲新生”是影片的最初概念。这部电影便是2年后上映的《秋日奏鸣曲》。
在七十年代,伯格曼的创作主题由对上帝存在与艺术问题的思考,转入到了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集中描绘,如《呼喊与细语》讲述了姐妹间的自私与疏离、《婚姻生活》描述的是表面平静的婚姻生活之下,夫妻之间感情的消耗与怨恨的累积。按照伍迪·艾伦的说法,“他的痴迷从上帝的沉默,逐渐转移到试图理解彼此感受的那些痛苦灵魂之间的纠缠关系。”在这些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片中,观众最常感受到的是人与人的沟通失能。因此,对伯格曼而言,母女关系中的“新生”是与先前不同的尝试。这一电影灵感与税务案带来的冲击相关联,成为了我们理解伯格曼关于创作与生活的心灵转变的重要线索。那么,伯格曼渴望在影片中进行的尝试是否成功了?
《秋日奏鸣曲》讲述了伊娃与她的母亲夏洛特在七年分别后会面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日一夜间。母女在夜晚失眠后的对话是全戏的高潮,两人讨论彼此的关系,互相倾吐着不满、怨恨,伯格曼把这场戏形容为“揭示真相”。按照他构想之初的工作日志,这场戏不能仅仅停留在两人的矛盾上,而必须向下挖掘,“最终要让女儿带给母亲新生。”然而,故事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另一面:母女二人无法解开彼此之间关于家庭的心结。

伯格曼在《伯格曼论电影》一书中回忆说,有影评人评价《秋日奏鸣曲》“是伯格曼所完成的另一部伯格曼式的作品”,这部电影中仍然充满了伯格曼作品中的常见元素,即“熟悉的神经质主题”,包括人们在渴望被爱时所表现的紧张、沟通不畅时的焦虑,以及不被理解时的痛苦,如此等等。伯格曼感到伤心,他认为“伯格曼式”这一说法对于他本人是一句不幸的评语。这部电影于他而言是“在那段自我禁锢时期(逃税风波)结束之后,利用某夜短短几个钟头的时间构思而成”,它的灵感来源于瞬间而非长期构思,“伯格曼式”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的创作力的枯竭。
更关键的是,伯格曼在摄制之初便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在家庭内部和解的心愿,他假设自己如果能够在影片中贯彻母女和好的设想,就能避免风格的再次重复,但他同时也深知,自己在拍片时“并未真正设法去了解其中的真实情绪”,无法深入挖掘影片的内在精神。这种渴望转变却不得的无力感,是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难以注意到的,人们大多会认为,伯格曼依旧在表达他熟悉的主题。
二、走不出的童年阴影与家庭困境
除了对于电影拍摄与预想不符的困惑,在《伯格曼论电影》一书中,他还表达了自己的另一个不解:从那一晚的灵感中所诞生的,为什么是《秋日奏鸣曲》这个故事?念头产生的缘由不可回溯,但或许我们可以从母女对话——这一场伯格曼寄希望能实现“女儿给予母亲新生”的戏——入手来寻找思路。在这一幕中,母女两人在诉说时暴露出的不同立场的苦衷,与伯格曼作为儿子与父亲的双重身份暗暗相合。
两人间的对话,由伊娃开始。在酒精的作用下,伊娃控诉夏洛特作为母亲的失职:夏洛特忙于巡演无法回归家庭,使她感觉自己被忽视,而当夏洛特因背疼而回家休息时,为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以及在人前维持自己家庭的美好形象,严格地改造女儿的站姿、发型与衣着;而害怕拒绝母亲的伊娃,只能说服自己“我身上没有一处值得人爱,没有一处会被人接受”。母亲自以为是的爱使她难以面对真实的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恨意转变成了阴影一般的焦虑感。女儿的审判与母亲的辩解是交替进行的。夏洛特震惊于伊娃的恨意,为此感到恐惧和难过,但她也需要倾吐自己的苦恼。她提起自己在童年时从未学会如何去爱,“只有音乐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情感”,就算她已然衰老,在夜里醒来时,仍会好奇自己是否活过,好奇着是否“有些人对于活着这件事比他人更有天赋”,自己却只是徒劳地积累着经验和记忆。她害怕女儿对她的爱有所要求,于是坦白地告诉伊娃,“我不想当你的母亲,我想让你知道我和你一样无助……我只希望你能抱抱我”。在这些二人产生交流的对话时刻,苦恼的源头毫无例外地指向了童年的创伤。伊娃缺失母爱与行为举止被规训的童年,夏洛特对于家庭生活的逃避,似乎是伯格曼心灵中多个侧面的表达。

伯格曼在敏感多病的幼年,承受着与伊娃相近的失落。他对母亲有着强烈的依恋,“像狗一般的忠诚。”为渴望关注,他用病痛自我折磨,希望引起母亲的同情心,或佯装冷漠,只为让母亲注意到他。同时,他常因一些小事受到作为牧师的父亲的严厉惩罚,比如在尿床后被关进黑暗的橱柜,或犯错后穿着红裙向女性长辈道歉。牧师家庭必须对外开放,并时刻接受着教区公众的批评监督,为此,家庭成员不得不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父母的婚姻生活因此也充满着压抑的气氛。伯格曼曾经目睹父母之间的争斗,彼时,母亲经历着婚外恋,正准备挣脱婚姻的枷锁,父亲为此饱受折磨,最后两人在其他牧师和亲友的介入下达成和解,继续维持“秩序与安定的假象”。父母婚姻在光鲜表面下不为外人所知的难堪,成为了伯格曼对婚姻的最早印象。
或许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伯格曼成年后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亦难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经历过了五次婚姻,有数个情人,共育有九个孩子。婚姻中的出走是在他的生活与电影中反复呈现的情节。伯格曼在自传中谈及出轨时说,“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胆行为滋生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真实。”他在觉察其珍贵的同时,也感到愧疚,“一种性冲动总是缠绕着我,迫使我常常产生不忠行为。我被欲望、恐惧、极端的痛苦和良心上的内疚折磨着。”在婚姻中,伯格曼似乎总是希望能挣脱丈夫与父亲这些身份的束缚,这也导致了他与自己的子女之间情感陌生,比如在税务案发生之后,他的孩子大多认为他罪有应得。
在一些研究伯格曼的学者看来,从他的电影年表中可发现一种自传性的“生命曲线”。 在他的电影中,主人公希望与亲人和解的诉求并不少见,导演的立场却通常冷漠而疏离,但如前所述,1976年之后,或是因为逃税丑闻的打击,或是由于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开始希望在创作中实现家庭内部关系的平衡,至少在坦诚相对的心灵交流中,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共同理解。这一阶段,在伯格曼关于家庭的讲述中,不再只有被动接受爱意与惩罚的孩子,也有着不知如何面对子女要求的父母。
所以,“58岁才走出青春期”的说法不意味着解脱,而是伯格曼渴望和解的心愿日益强烈。只不过,当他希望将这种想法在影片中付诸实践时,双方对爱的诉求都是如此的热烈和互不退让,寻求和解的过程再次变成了互相伤害。
三、尾声
巧合的是,晚年的伯格曼有一段与母亲对话的梦。当时母亲已逝世,他们在梦中相遇。伯格曼表现得很脆弱,他情绪激动,追问母亲许多问题:她逝世后是否曾在梦中到访过他的工作室,并握着他的手陪伴他?爱在家里意味着什么?家人间该如何解除相互间的怨恨。避免不幸?为何哥哥、妹妹和他都带着伤痛生活,无法正常地建立人际关系?然而,母亲只是疲惫、消极地回应着,脸上写满了拒绝。两人就连在梦中的沟通都阻碍重重。梦境中的伯格曼,仍为在原生家庭中经历的挫折所苦,渴望为自己的遭遇寻求解答。
后来,他拍摄了一部以母亲的脸为主题的短片,浏览了与母亲相关的家庭相册和大量日记,并在这一过程中理解了母亲面对生活失败时的心境,以及她在日记中写下的“也许人应该竭尽所能去独自处理好一切”。伯格曼明白,他的家人的性格善良,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生活无尽的索求并忍受着负罪感的摧毁。

直至最后一部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伯格曼才在影片中借由家庭外部的力量实现了某种和解的心愿:亚历山大在继父家经历着与他相似的饱受惩罚的童年,最终由祖母救出,获得自由。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曾评价称,“我可以理解一个老人,走过这么丰满的一生,最后有一种和解的愿望:与世界和解、与记忆和解、与家族和解。”尽管她认为,“和解仅仅是一种妥协。”
这份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与和解之不可能相关的纠结,不独属于伯格曼,也不仅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它与家庭和自我之间的永恒矛盾相关。人们在家庭中完成与社会的接轨,也在家庭内部释放着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紧张,来自共同生活的安排压制着欲望,引发自我的反抗,冲突因此不可避免。伯格曼选择不去逃避这一冲突,他坚持对冲突背后的痛苦和绝望坦诚发问,主动“阻碍”着自己和解愿望的达成,以这种矛盾的姿态成就了“伯格曼式”的伟大。
参考资料: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著),张红军(译),《魔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著),韩良忆(译),《伯格曼论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
戴锦华评价部分,参考:
《戴锦华 X 王小帅:伯格曼已逝,艺术电影将何去何从?》,界面新闻,2017-08-01;
《戴锦华:我们这个时代,比伯格曼的时代要脆弱多了……》,“WeLens”微信公众号,2018-6-14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