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牧人生》的副标题是“湖区故事”,作者詹姆斯·里班克斯是牧羊人的长子,他的父亲也是牧羊人长子,家族世世代代都在英格兰湖区生活和劳作,按季节和放牧的需要来安排节奏,深深扎根于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失去并逐渐陌生的土地。
而对放牧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很多现代人正在为了离开原生家庭而努力工作,而放牧人的努力工作,则是为了将这一切传统保留下来。
正午书架节选了书中最后几个小节,内容有删节,小标题等也是正午编辑所加。
夏季牧场
1
在山地牧区的远端,我依照指示等待着。我不知道过了多少秒、多少分,或多少小时,因为完全没有时间概念。
被派到我后方的人赶着羊群朝家走,而我就这样看着他们。乔基本上清查完了溪谷,我跟他一起抄近路穿过山地牧区的远端。牧羊犬们追着一只赫德威克公羊从我们身旁跑过,我们停下来“欣赏”这一幕。
“快看呀。”
“嗯。”
“是你的羊。”
“我知道。”
“它的妈妈刚独自走过。”
“现在看来,它会赢。”
“也许。”
“等着瞧吧。”
他走在我身后,赶着羊群穿过欧石楠花地。我越过天际线,把羊群朝下赶向乔,并清查那些泥炭地。我现在是离家最远的一个。我的世界在我们脚下延伸,三种土地组成了我们的世界:草甸(或“水草地”)、沼泽开垦地和山地牧场。羊群一年中就在这三种土地上按照安排好的日程活动,这也就是一年的农活。
山地放牧本质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夏季,山地牧草丰茂,凭借这一优势,牧民们可以依靠放牧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或是卖掉羊群赚点钱。山地放牧的耕作方式也就这样在漫长的演化中留存下来。
不弄清楚一件事情过去的情况,后来又发展成什么样,就没法讲清整件事。这听起来有点像鸡和蛋的先后问题(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换成羊和羊羔)。我把我们全年工作的基础流程稍微解释一下,也许有助于理解。简单来说,我们的工作就像下面这样……
盛夏时节,我们得保证小羊健康成长,把母羊和小羊从山地牧场或沼泽开垦地赶下来剪羊毛,并为冬季准备草料。
秋季,为了秋季大市集,我们又把羊群从山地牧场或更高的地方赶下来,把小羊与它们的妈妈分开(妈妈们不久就能恢复过来),处理好多余的小羊和母羊,在“山地牧场丰收季”把它们卖掉。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里,通过向低地农民出售多余的育种母羊,并向其他育种人高价出售少量高品质的育种公羊,我们将挣得全年大部分收入。
秋末则是新繁育季的开始,我们会把公羊和母羊放在一起,其中包括刚从其他羊群引入的公羊。这时,特别留下来的小羊(为新一代羊群而保留)也会被赶到低地牧场过冬。利用秋末和冬季的时间,我们还会把富余的小公羊养肥,然后卖给屠夫。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5月至10月,利用山地丰茂的牧草资源,培育种羊,出售给其他牧民(他们十分看重山地羊生的母羊,因为这种羊在低地更健壮,更有生产力),以及养殖小公羊满足肉食需求。这些小羊的买卖可以通过一种中间交易完成,这种交易被称为“仓储式交易”。一个中间商会买下这些小羊并饲养它们。我们就是从这两种生产劳动中挣钱。
冬季的任务就是照看好最重要的那些种羊群,在适当的时候喂食,让它们熬过全年最糟糕的天气。羊群全年大部分时候都吃新鲜青草,但冬季的几个月里青草消失不见,我们就需要给它们喂干草。
冬末或早春时节,我们重点关照那些怀孕的母羊,为生产小羊做准备。
春季的工作就是围绕母羊产子展开,它们将在我们最丰美的土地(水草地)产仔,接着就是照顾成百上千只小羊。
春末或初夏,我们要给母羊和小羊做标记、接种疫苗、除虫,再把它们赶上山地牧场和沼泽开垦地,充分享用夏季茂盛的青草,同时也解放谷底的土地,使其为冬季孕育牧草。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农活从头来一遍,就像我们的先辈们之前做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农作模式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规模有所变化(牧场为了生存而进行合并,所以牧场数量有所减少),但基本工作内容并没有变。你可以带一个维京(Viking)人来我们的山地牧场,他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放牧一年的基本劳作模式。不同的山谷和牧场自有其进行每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农务进程由季节和必要条件的变换所决定,不受我们意愿控制。
有时候你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山上等其他人,就这样静静地独自等待。云雀会欢唱着飞上天际。有时候你看不见一只羊或一个人,只有远处的主路和村庄。没人真正知道这种山地集体放牧的历史有多长,也许已经有五千年之久。






2
我的脚下和四周是大片天然山地草场。
依照传统,我们这样的湖区牧场拥有公共放牧权,可以在属于某些人的领地上放牧一定数量的羊。这种公共放牧羊群的数量往往约定俗成,需要与山地牧场和冬季低地牧场的放牧能力相匹配。从古至今,这一体系都离不开规则和习俗的制约,以防过度放牧、欺骗或管理混乱。在没有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年代,能够让人们集体协作共同管理这片土地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习俗和实践两方面达成共识——让每个人都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过去还有过领地法庭,对那些做错事的人处以罚款,这种实际操作中采取的措施仍然在公权人协会中存在。
11月的时候,我们要召开牧羊人大会,从彼此的牧场找出走失的羊,否则我们就要被其他公权人惩罚。从一片公共牧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寻找一只迷路的羊,可能意味着90英里路程或更远,而且还要来回奔波。一些牧场主还在不同的公共牧场保留着股份,所以一些山地牧羊人要花大把时间在不同的山地牧场集合。一些年轻牧羊人十分擅长此道,从中获取额外收入,并为此养了很多牧羊犬。
人们对于牧羊人和牧民的生活存在一种诗意想象,认为他们过着一种天人合一、与世隔绝的生活。华兹华斯对这种想法很推崇,他根据自己的童年印象,为世人描绘了这么一幅景象:牧羊人带着他的狗独自待在山地牧场,与自然融为一体。
从个体本身而言,这有时候就是事实——我的祖父辈的人有时候就是孤身一人与羊群和自然世界为伴。但与此同时,从文化和经济上看,牧羊人并不是孤身奋战。我的祖父曾有一片被称为“足球场”的土地。在附近牧场干活的年轻人足够组成两支球队在那儿来一场比赛。而他的工作就是调配人手,让其他人为之叹服,赢得尊重。
众所周知,贝都因人之所以能够在撒哈拉沙漠来去自如,是因为他们对沙丘和沙岭了如指掌,哪怕它们随着时间缓慢移动,贝都因人也能算出沙岭的数量,并能准确地指出它们的位置,还知道如何到达想去的地方。我们的文化传承以及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安排,正是在这样类似的结构基础上发挥作用——如果你能领会其核心,就能驾驭细节。
我的祖父和父亲可以在英格兰北部任意行走,他们总是知道谁曾在某片土地放牧,在此之前又有谁来过,或是谁在邻近牧场放牧。整片土地就是由牧场、羊群和家族编织成的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我的父亲几乎不会拼写什么常用单词,但却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聪明”的一种嘲弄。我认识的一些最聪明的人都是半文盲。
我的祖父能根据放牧的地点、羊群的品种和牧羊人常去的交易市场,迅速说出在英格兰北部甚至英国其他地区公共牧场放牧的任意一个牧民的名字。他知道每个人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会在干些什么。他会说,“不要去打扰威尔逊一家(the Wilsons)……他们今天正忙着给还没剪毛的杂交小母羊梳毛(他们每年秋季要把这些漂亮的小母羊卖给低地牧场育种)”。如果你翻过山头去到他提到的那座牧场,就会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早在信用审查制度发明以前,这里的人就能迅速分辨社区新来的人是否值得信赖:只要与某个从他原来社区赶来拍卖市场或展览会的人聊上几句就行,而这人的全部家史和经历也会被广而告之。
所以,如果有人落下了偷羊的口实,可就是不得了的丑闻,流言会传遍整个山谷。最近,奔宁山脉地区一户颇受尊敬的牧民家庭就遭受了这样的磨难,许多邻居指责他们偷羊。这桩案子还没有移交法庭审理,我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会被定罪还是被判无罪,但这事显然已经在山地放牧社区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认识的一位老牧羊人也在那户人家放牧的公共牧场牧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老人家眼含热泪,他无法相信自己信任的人会剪掉羊耳朵上的标识,锯下有标识性烙印的那截羊角,然后把羊偷走。
牧羊人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诚实守则。我还记得祖父跟我说过的一件事,他的朋友私下从另一个牧民手里买了一些羊,觉得这些羊的价格相当不错。几周后,他参加了一个羊群交易会,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以极低的价钱买到了那些羊,那价格有点太低了,大概每只羊的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五英镑。他非常信任那个卖主,因此觉得这对卖主不公平。他不是个贪婪的人,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被看作一个贪婪的人。所以,他寄了一张支票给那个牧民,补上了差价,并且为此表示歉意。但卖羊的牧民后来委婉地拒绝兑现支票,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买卖双方你情我愿的交易,他们已经握手成交了。事情就此陷入僵局。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来年继续找那个牧民买羊,并多出价补上去年的差额,而祖父的朋友确实也这么做了。两人都没有动过丝毫念头想在短期内“最大化利益”,而当代城市商人很可能就会这么干。与赚快钱相比,他们都更看重自己的德行和诚实守信的声誉,所谓君子一诺胜千金。
父子之间可以用相同的名字,而姓氏则与牧场的招牌紧密联系在一起。牧场的名字与你的姓氏一样,传达给其他牧民很多有关你的信息。也许有二十个牧民有着相同的姓氏,而牧场的名字就能迅速把他们区分开来。有时候在平时的对话中,牧场的名字甚至可以取代姓氏。
最近我在酒吧里遇到一个人,他认识我的祖父。“如果你有他一半的品质,那么你将是个正直的人。”他严肃地说,然后请我喝了一杯,祖父几十年来的低调和与人为善获得了回报。人们会小心观察任何出现在社区或公共牧场的新面孔,直到他们展现出正直的品质并且循规蹈矩,警报才会解除。他们说只有在这儿待够三代的时间,你才能成为“自己人”(他们说起这些来是总是大笑,但这样的谈笑绝非虚言)。




3
我的祖父会关注日落这类“美好”事物,但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从实际功能角度加以说明,而非抽象美学角度。他对身边的景物充满激情和热爱,但他与这些景物的关系更像长久坚韧的婚姻,而不是转瞬即逝的露水情缘。他的工作把他和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丝毫不受天气或季节影响。
欣赏春季日落这样的景象对他而言富含深意,他可是熬过了六个月的风霜雨雪才赢得这样的机会,获得点评这些景物的权利。他当然认为这样的景物是美丽的,但这种美包含着实际功能性暗示——预示着冬季的结束或更好天气的到来。
一开始,祖父就教我有关传统世界观的知识,他说欧洲人称农民为“peasant”,而我们就简单地称为“farmer”。我们拥有土地。我们以前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以后也会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不时会遭受打击,但我们会坚持并获得胜利。
北欧的许多乡村社区盛行一种被称为“平等主义”的思想,人们依据工作、家畜情况和分享精神来评价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这些山谷中,历史上并没有用财富来区分农民和牧场工人,至少没有从社会地位和文化角度加以区分。贵族家庭没有也不能在这些地区真正施加影响,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农民和劳工大多数时候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在酒馆里喝酒,一起看体育比赛,过着几乎没有差别的生活。拥有土地的农民也许认为他们比那些从未拥有过自己的牧场的农民或牧场工人聪明那么一点点,但任何形式的摆架子或阶级界限都很罕见。势利眼可没有好日子过。世界太小了,其他人有大把机会可以让你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是否能获得尊重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羊群或牛群的品质,维持牧场运营的能力,或工作技能和管理土地的能力息息相关。无论男女,无论以现代眼光看是否“只是雇工”,只有优秀的牧羊人才能赢得最高尊重。成为一名牧羊人意味着可以与任何人并肩而立。



冬季牧场
4
在我看见它之前,它就看到了我——一只长着粗脖子的幼鸦。它全身漆黑,无所畏惧,满腹尸肉。渡鸦以我们的灾难为生,它们残忍、傲慢又无情,可有时候看上去又惊人地美。
如果我举起一把霰弹猎枪现身墙角,渡鸦就会飞上墙头,逃到一棵恰好在射程外的树上,发出嘲笑的嘶哑叫声“咔啦嘎”,但它此刻显然对一个只有一支圆珠笔做武器的男人不感兴趣。风掠过它的羽毛,它那长着黑灰毛的粗大脖子泛起褶皱。贪婪。狂喜。它飞起来的样子就像肚子里装着块石头,被腐肉撑得东倒西歪。
我们那些死掉的羊一点也不漂亮,因为生与死本就不美。冬季的时间都耗在羊群上了。两只老母羊因为太老而难以过冬,它们的肚子浮肿,双眼无神,就这样躺在院子里。它们旁边倒着一只腹部被打穿的小雌狐,内脏几乎都流了出来,粗糙的脸上不甘心地露出一颗尖牙。
渡鸦在牛棚的瓦楞顶上跳来跳去。那暗沉笨重身躯的每一次跳跃,都显示它已经饱餐一顿。最后它缓缓地拍着翅膀隐入暗处。
可生活却会在你只剩半口气的时候,还要送来坏消息击垮你。
其中一只已经倒下的母羊死掉了,给了我沉重一击。它是我拥有的最优秀的一只母羊,就像羊群的女统领。去年冬天,羊群在漫天风雪中陷入危险,正是它把羊群带出迷途。


5
可恶的雪。牧羊人恐惧和厌恶厚厚的积雪和狂风。大雪带来死亡,埋葬羊群,掩埋草地,让羊群的生存更加依赖于我们。因此别人的狂欢却成为我们的苦难。雪球。雪人。雪橇。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小雪无大害,我们能用干草饲喂羊群,它们也能轻松应对那种程度的寒冷。但狂风暴雪的组合是毁灭性的。暴风雪不仅能杀死羊群,也能轻易取走人的性命。如果你见过雪地清扫后倒在墙后死去的母羊,或是死在出生处的小羊羔,你绝不会再如此心无芥蒂地喜欢雪。不过,虽然我如此惧怕和厌恶雪带来的恶果,也不得不承认它的确扮靓了整个山谷。素白。寂静。残酷。它掩盖了平时所有的嘈杂,只余下溪流比往常略微低沉的如泣如诉的呜咽声。感觉到外面声音的消失,不用睁开眼我就知道雪有多深。但脑子里的闹钟还是滴答作响,提醒我必须照看和喂饱所有的羊,我的工作才算完成。


6
我出门走向风雪和鸦群,一切看上去仿佛勃鲁盖尔油画里描绘的场景。橡树和荆棘如黑珊瑚般挺立在皑皑白雪中。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必然和必需。今天我必须调整到最佳状态,应付一切意外,不然那些牲畜都会挨饿。
雪下得很大,很快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我骑着四轮摩托车出发,给母羊们运去干草,在大雪里很快变得一身白。密集的雪花盖在我的身上,无数雪花在眼前纷纷落下,仿佛鸭绒飘落。一些落在我脸上,融进我的眼窝,一片濡湿,遮住我的视线。我感觉到一片雪花轻盈地落在我的舌头上。柔软。丰盈。美味。仿佛是雪神放在我舌头上的圣餐。摩托的轮胎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轧实了路面的积雪。
山地牧场的门楣上积了三英寸厚的蓬松的雪。我要去喂的第一批羊在远处的一个峡谷里,它们的母亲和祖母教它们在那里躲避风雪。山地绵羊对于领地上空的天气变化拥有第六感。我在欧洲赤松林里找到它们,高达40英尺的树木为它们遮风挡雪。年纪最大的母羊会把它们带到这里,如果有年少的母羊试图带着大家走向险境,它会牢牢站定加以阻止。羊群会接受年长的羊的指令。它们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安全的,如果大雪持续数日,它们可以嚼生草丛的草来维持生命。这片地方就像畜棚一样安全,既没有风,又有溪流浇灌,这条溪流此时仍从山坡顺流而下雕刻着峡谷地貌。
我把救急干草扔到溪流两边,它们很快聚集到干草周围。母羊们各自从中扯出一点开始嚼起来。看到它们一只只满嘴干草,我才松了口气。这些有藏身之处,并且吃了些干草的母羊能在避难所维持很多天。我数了数,发现少了两只。但突然它俩也冲下来嚼干草。我终于如释重负。这两只年轻的母羊之前不得不扒开雪寻找更可口的草。现在它们暂无大碍,将依靠干草度过这场大风雪。
没时间在这儿欣赏美景,我还要去喂其他羊群。雪依然很大,山谷正改头换面。



7
天地白茫茫一片。远处的路上此刻悄无声息,空无一人。山谷正与世界隔绝开来。我听到正在低地干活的父亲对羊群发出的呼喊声。扫雪机很快就会出动,但可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抵达这里。他们主要在高速公路和镇上作业。我已经开始为最远处高地的羊群担忧,如果雪继续这样一直下,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到达它们那里(况且到达那里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
我要给它们带去一些干草,让它们肚子里有些好货抵御风雪。我要尽快赶到那儿。四轮摩托车在雪地里艰难前行,不时急刹、侧滑,有时候还会滑倒在路边。我驾车驶过村庄,一路经过很多在路上抛锚的汽车,人们正在努力推车好重新发动起来,他们被大雪阻断了上班的路。我驶入一条通往高地的小巷。但雪已经被冻结成冰,无法驶上山坡。我调转车头,决定走另一条需要穿过一两片田地的路。我超过正在跟我做着相同事情的邻居。他看见了我,也知道我要去哪儿,对我微微点头示意。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会救我一命,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我要去哪儿。
雪正在变厚,我必须集中精力,不然可能撞上被雪掩埋的什么东西:水槽、树枝或石头。我很快到达羊群可能的聚集地,但无法看到它们。它们一定躲在分隔草场的某堵墙后面,但前方道路积雪,无法驾车通过。我必须要找到它们。距离并不远,但在雪地负重跋涉可称得上一项壮举。
弗洛斯(编注:作者的牧羊犬)跟着我在厚厚的雪中跳跃前进,好像在踏浪而行。它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比我先到墙边。它跑到墙边的积雪上,想看看另一边有什么,又回头看看我,一副等不及的样子。我们很快找到一些母羊。它们身上披着一层雪,脸上也一片雪白。见到我时友善的黑眼睛透露出喜色,羊毛把落在它们身上的雪和身体隔离开来,避免了热量的流失。它们冲到我的腿边,开始啃食干草。我想清点数量,但这很难,因为其他母羊从四面八方破雪而来。我努力数了一下,发现有一些母羊失踪了,大约12只。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如果我在这儿待更长时间,四轮摩托车将被困在小路上,而我则有可能遭遇各种麻烦,或许就无法回去找其他羊群。就在这时,它们从一片白茫茫中现身了。
我不喜欢这场雪,它堆积得太快了。我决定把羊群带走,到较低处的庇护所去。要加快速度。我驱赶着羊穿越风雪,但它们总想往回走。为此我在衣袋外面吊了一个空麻布饲料袋,以此诱使它们跟着我走。如果能走到山坡下几百米的一处新草场,那儿就有一个庇护所。我摔了一跤,仰面倒在地上,但还是爬了起来。我艰难地在小道上穿行,雪越积越厚,令我欣慰的是,母羊们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
品质最优的那只母羊跟着我走在我踏出的“平路”上。它为我培育了很多优质的后代,提升了羊群的品质。它一直有自己的价值所在。年轻时它就被带去参展,多年后,当我带人到草场看我的羊群,它已经懂得展示自己,会骄傲地站成一尊雕像。夏季,它领着羊群从高地穿过小道下山,带着它们跳过小溪,整群羊都跟随着它跳跃而起。它精明且懂得生存之道,知道此刻羊群正被领着脱离险境。
我让弗洛斯往后退去照看其余的羊,它们排成一队跟在后面。这时我虽然在冒汗,但脚趾和手指却冻得冰凉。稍后我会再回到停四轮摩托车的地方,从另一个方向把它开下狂风肆虐的草场。
我们来到一处被雪深深掩埋的门道,积雪已经齐腰,更糟的是风还在不断把雪吹向平缓的地方。过了这个关口,母羊们就会更安全,现在不能把它们留在这条巷道上,所以我踏进几乎到我胸口的积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那只老母羊已经选择跟着我的脚步前行。其余的羊都看着它,不确定是否该跟随。但很快它的一个女儿跟了上来,它们都聚集到我开拓出来的狭窄的白色小道一端。我继续穿越积雪前行,每一步都深深陷入雪里。我踢到一块石头栽了个跟头,老母羊踩着我的双腿过去,其余80只羊也跟着这样走过去,所有羊现在都奔着目标而去。它们艰难跋涉往下走向草场,那里的积雪没那么深,我也会到那里去给它们喂干草。现在无论发生什么,羊群都能承受得住。它们在这里能避开肆虐的狂风,保证安全。
弗洛斯过来舔舔我的脸,它知道在今天这场大风雪中,我需要它。


8
我最终把四轮摩托车开出了雪地,顺利回到家。双手已经冻僵,我奔向热水龙头。房门口堆着少量积雪,我走进厨房的时候积雪跌落进来。孩子们很开心不用上学,求我带他们去坐雪橇车。我发出痛苦的呻吟。
海伦责怪我把家弄得一团糟。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打趣我太爱那只老母羊。她称其为“羊群女王”。然后,她意识到我有多冷,又开始为我忙作一团。
冬季对我而言,就是把肿得跟猪蹄一样的手指,颤抖着伸到热水龙头下解冻,忍着刺痛大声嚎叫着谁也听不清的脏话;是我乡巴佬一样的手指和镜子里充血的双眼;也是我顶风驾驶四轮摩托车时,打在我脸上的雪花或冰雹,它们形成完美的速度曲线,就像《星球大战》里轻叩油门,星星就被抛到身后。冬季还是我和父亲一起抓身体状况欠佳的老母羊时,他露在我眼前的淌着雨水的脖子。风暴来临时,母羊们会在狂风抢走它们的口粮前死死咬住干草。小羊们却在生命展开前就倒地死去。冬季意味着干草架和树木被吹倒、撕裂,彻底毁灭。
冬季就是个贱货。
但冬季也意味着晴空万里无云的好日子,那时一切风平浪静——草场变干,羊群心平气和,干草充足,它们躺在阳光下,我们也边干活边享受山谷和野生生物的美。冬季也可以很美好。
冬季的特别来自那些微小的细节。成群的大雁在霜蓝色的天空高高飞过。渡鸦在风中追逐嬉戏,就像从山上落下的一条黑丝带。狐狸在破晓时分悄悄穿过霜冻的草场。野兔瞪着水汪汪的大黑眼睛看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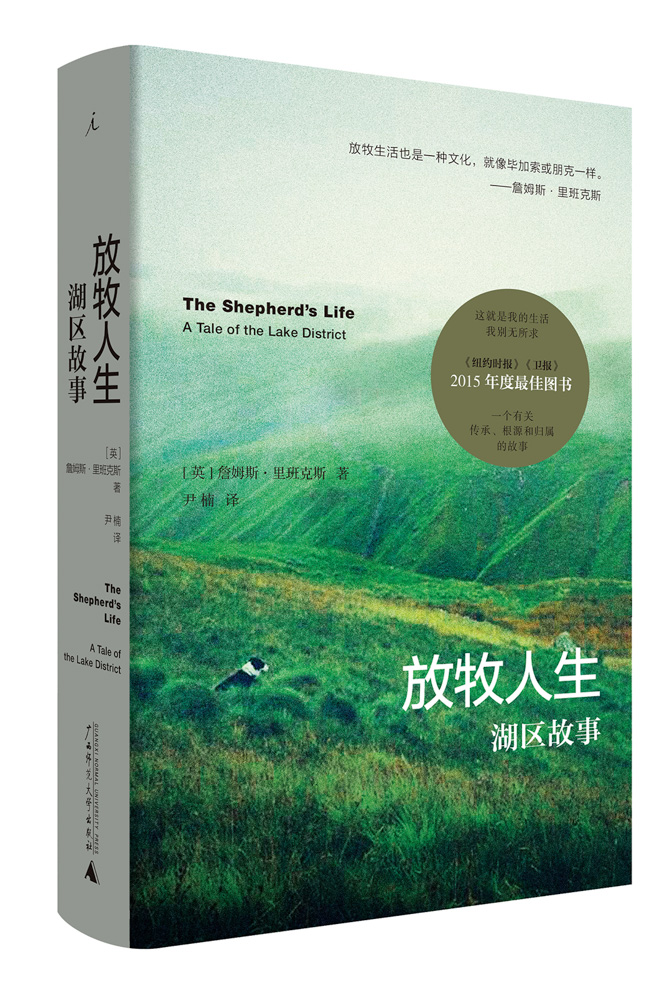
—— 完——
题图为湖区牧场全景。文中所有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放牧人生》,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