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已经习惯高铁和动车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回到工业革命时代,认真回想铁路和火车的起源,及其对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对风景的观感、旅途交谈的没落、旅行中的个人隐私和个体空间,以及铁路与社会公平等诸多问题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铁路在19世纪对人们心灵的形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推而广之,高铁、飞机、自驾旅行对我们又有着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本文选自《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第五章,有删节。
我必须把我自己装进这个流动的盒子里。我出不去,但也没什么能进来。
—— 欧仁·曼努埃尔(EugèneManuel),1881
包厢
19世纪上半叶,对于进步思想的信徒而言,铁路成了民主、国家间的和谐、和平以及进步的技术保障。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铁路都让人们靠得更近。欧洲思想中的这股思潮,在圣西门的追随者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这一代学人大约是在1825年,也就是圣西门去世那一年,登上了法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他们把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未尽的平等主义愿望,全部投射到了工业及其壮观的先锋——铁路上:对于他们而言,比起任何仅仅是形式上的政治解放,铁路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1789年以来的平等与友爱。
佩克尔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作为工业一部分的铁路,是服务于人类的解放事业的:
火车和蒸汽船上的共同旅行,以及工人们大量聚集在工厂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激发了平等与自由的感受与习惯。让所有社会阶级一起旅行,并且把他们并置在某种鲜活的马赛克里,那就是各个国家能提供的所有的财富、地位、性格、习惯、风俗、衣着方式的拼贴。铁路极大地推进了真正友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并且比起民主的民权保卫者最尊贵的训诫,更有助益于平等的感受。这样一来,为每一个人缩短不同地方分隔开的距离,也就等同于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如果佩克尔确信,火车与轮船“真正是平等、自由与文明的战车”,另一方面,他也会意识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老的特权和不平等也可能在工业的创造中重新出现,哪怕它们真正的本质就是平等与民主。
佩克尔认为铁路车厢按照等级区分开来可能会造成危害。在他写作《社会经济学》的时候,这种区分在法国还不存在,当然只是因为铁路还没有提供客运服务。到1840年代初,法国除了一条很短的线路,所谓铁道,是以描绘英国和比利时的铁道而存在的。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铁道从一开始就是分了等级的。19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者,尤其是圣西门派的工业拥趸,几乎没注意过这个事实,而只是为蒸汽机带来的无法抗拒的魅力所倾倒。
在由铁路实现的闻所未闻的能量与生产力面前,传统的社会特权似乎都已经彻底过时了,再无希望,所以完全不值得再处理。尽管佩克尔没有完全忽视不平等复活的可能性,但他还是坚信,平等会基于技术而取得最终胜利。他认为,火车上的旅客们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技术上的平等中:“这是同样的护送队、同样的力量,运送着大和小、穷人与富人;因而从最普遍的意义上,铁路上了一堂平等与友爱的课程。”
但是随着铁路历史的延续,即使在法国的火车上也显示出了阶级的分别,推翻了技术上平等的处境会给旅客带来社会平等的观念,也颠覆了圣西门派的许多其他希望。而历史也显示,佩克尔观念的核心确实蕴含了某种真相,尽管这与佩克尔的信念大为不同。不同阶级的成员都在同一辆火车上,由同样的力量推动,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带给他们社会平等,但却在他们的观念里存在过。
乘坐火车旅行,由蒸汽力量拉动,被认为是参与到了工业进程中。对于下层阶级而言,这样一种体验非常直接:在1840年代的英格兰,他们是由货运火车上的棚车车厢运输的。他们并没有被视为在接受旅客服务,而不过是货物。1844年的格莱斯顿法案(GladstoneAct)要求三、四等车厢也必须加盖,尽管这些车厢看起来更像是加了盖的棚车,而不是旅客车厢。
而特权阶层的旅行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车厢,看起来就像固定在轨道上的马车。这样的设计,不仅会让人忘掉铁路的工业起源及其本质,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抑制这些想法的努力。
包厢几乎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马车车厢,没什么变化,包厢的设计就是要让一等旅客(在稍弱一点的意义上,也包括二等旅客)放心,他们的移动还和在他们的马车里是一样的,只不过价格更便宜而且速度更快。但其效果和人们所期望的正好相反。恰恰是因为包厢与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旅行联系太密切了,充分吸收了传统旅行的精神,新的工业化运输方式就使得人们的体验更具创伤性。
中产阶级的一等车厢旅客抱怨说,他们觉得自己不像旅行者,反倒像是包裹:这就使得他们的主观体验与下层阶级的客观体验同样带有工业色彩。但是中产阶级的体验,只是就其真实发生在一个精心布置的、装备一应俱全的包厢里而言是主观的,而不是下层阶级像棚车一样的旅行空间;就现实而言同样是客观的,旅行者只是一个工业过程的对象——这个世界里的所有布置,都不能让他忘掉这一点。



旅途中交谈的终结
包厢从马车上移植到了铁路货车上就失去了部分功能。在前工业时代的旅行中还有用的东西,现在就变得多余了。马车车厢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源于它的形式,亦即座位的安排:在U形的马车车厢里,旅客彼此面对面,这样一种安排促使他们在旅途中交谈。马车作为一种旅行方式,其历史起源足以证明,对于可交流的座位形式进行分等是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观念。
简单讲几句题外话就可以澄清这一点。在中世纪,人们旅行只能靠步行或者骑马,选哪一种取决于他们的阶级。乘坐马车出行这个习俗,是在现代早期一开始,与兴起于西欧生活中去封建化、都市化过程中的其他许多实践同步出现的。维尔纳·桑巴特这样描述马车旅行的起源:
在16世纪,可能是因为路况改善了,乘坐马拉的车厢旅行,就变得更为普遍。的确,我们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在他们的“马车”里偶遇16世纪的商人们;但晚至17世纪中叶,我们就会发现针对马车旅行的抗议,因为马车旅行可能有损国家的福祉:它让人们太舒服了,也摧毁了养马业等等。到17世纪末,马车旅行最终与骑马旅行一样,被广泛接受。
根据杰克曼的讲法,马车是于17世纪初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增加的,这个地区也是欧洲都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马车的形式与座位安排,还可以追溯到另外一种专门用于城市的个体运输车辆,那就是轿子。人们可能会说,马车包括了两个完全连接在一起的轿子。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被创造出来,与中产阶级的另外一些交流惯例比如咖啡室、会所、报纸以及剧院等等是同一时期兴起的,这都意味着必须把马车视为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
马车旅行的特点,不仅包括乘客与外部世界、与穿越的景观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包括乘客之间热烈的交流了。马车的乘客都是些健谈的人,谈话为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出版的许多小说提供了素材。而铁路则终结了交谈。
一个法国人在1857年回忆说:“在马车里,花一点时间做些准备工作,认识一下同伴,谈话轻轻松松就开始了;分离的时刻,人们往往会因旅行太短而遗憾,差一点就能交上朋友了。在火车上则太不一样了......”面对面的格局曾把一种既存的对于交流的需求制度化,现在却又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因为没有理由进行这样的交流了。
铁路包厢里的座位,迫使旅客要面临一种源自尴尬而不是基于实际需要的关系。对于现代感官如何既被视觉定位、又被视觉所迷惑,格奥尔格·齐美尔给出的解释,就说到了现代运输是这种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因:
一般来说,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要通过听到他说的话来解释,相反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了。因此,一个人看见却没有听说,比起听说却没有看见,会让人更为困惑,更为犹豫不决,也更为沮丧。对于大城市的社会生态而言,这一点一定具有重要意义。比起小镇里的交通,大城市的交通会使得大量的人能够看见他人,却不能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小镇的街上我们碰到的人大多数是熟人,可以和他们寒暄几句,或者是我们一看见那些人,不只对能看见的部分,而是对他们整个人都会有个印象。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大城市里的公共交通。在19世纪公共汽车、火车和有轨电车发展起来以前,人们一次不可能和他人彼此对视好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却不和对方交谈,哪怕是被迫如此。现代的交通,越来越将人们之间主要的感觉关系化约成纯粹的视觉,这就必然为他们的一般性社会感知创造出全新的前提。
齐美尔把人们的感觉描述成困惑、犹豫不决、沮丧,其实这种感觉可以简单形容为人们在火车包厢里不得不与他人沉默以对的尴尬。我们已经看到,追求阅读就是要努力取代已然不可能的交谈。把目光集中在图书或者报纸上,人们就能避免被坐在过道对面的人注视了。这种沉默处境令人尴尬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无意识的。
在M.M.冯·韦伯1857年出版的铁路手册中,我们就能找到一则这种隐晦的暗示,作者主要是讨论对欧式包厢与美式车厢的赞成与反对。(美式标准车厢与欧式的差别在于,美式车厢座位没有被面对面地安排在包厢里,而是在一个长长的车厢之中,朝着一个方向。)韦伯坚信,美式车厢并不适合欧洲的状况。他拥护包厢系统,并且声称他特别喜爱半包厢(bâtard-coupés),半包厢“位于车厢两端,其优势在于乘客不需要和别人面对面,而且又能从包厢开在三个方向上的窗户望出去”。
对于包厢式座位布置,公开批评很少,其中一则见于1838年的一期《铁路时报》(TheRailingTimes)。一封写给编辑的信,意带讽刺地署名为“债务禁锢与旅行监禁的敌人”,提出了另一种方案:
说起铁道车厢的内部安排......我恳切地......向公众建议,在每辆列车上都能够让一些车厢装合在一起,从而使乘客能够背靠背地坐着,从一排和车厢一样长的窗户中,望向窗外的乡村,不管这样一来他们是不是能更舒适。有了这个计划,一个在南安普顿(Southampton)与布里斯托(Bristol)之间往返的人,就可以每一程各坐在车厢的一侧,然后就能看见路两侧视野里的所有村庄。很明显,这会比连续坐上三四个小时一直研究别人的面相又想找到更好的消遣,要舒服得多。
只有特权阶级才会有这种不再和别人交谈而且越来越被他的同路人搞得很尴尬的体验。三、四等车厢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分成包厢,而仍然是一个大的空间,在三、四等车厢里既不会有令人尴尬的沉默,也不会有对阅读的普遍追求。正好相反,从这些车厢里传出来的声音,在特权阶级的车厢里偶尔也能听到,正如P.D.菲舍尔在前引文中所说,“愉快的交谈和笑声会从那些坐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一路传到我那个孤立、无聊的小间里”。
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Daudet)在回忆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Daumier)的列车场景讽刺画时,用下列鲜活的速写,描绘了他对发生在无产阶级车厢里的情境的印象:“我决不会忘记坐在三等车厢里去巴黎的旅行......几个喝醉了的水手在唱歌,他们中间有一个大块头的胖农夫在睡觉,嘴巴大张着像死鱼的嘴一样,带着篮子的小老太太们,小孩儿,跳蚤,奶妈,穷人车厢里的全部用具,都带着烟斗味儿、白兰地酒味儿、大蒜香肠味儿、淋湿的稻草味儿。我想我还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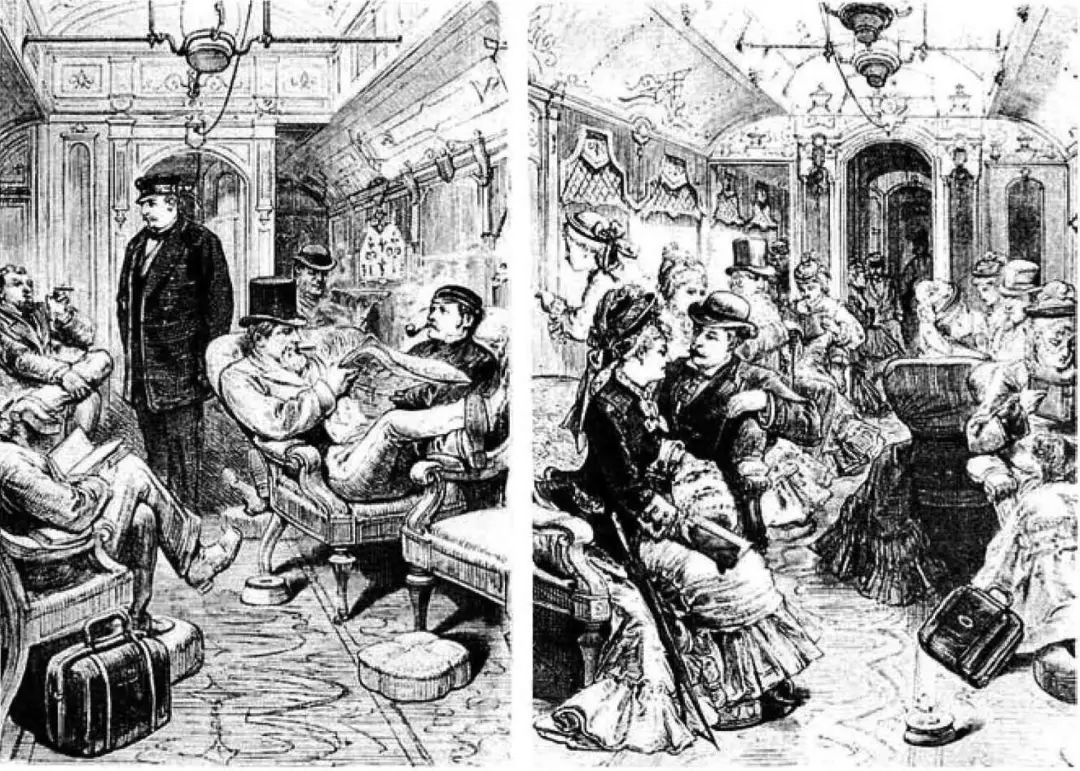
孤立
有些时候,一等车厢的旅客发现自己会从无同行旅客的场景中得到释放。一个人坐在包厢里,是一种暧昧的处境。也可以把这种孤独体验为一种满足的、安全的,以及愉快的状态。
泰纳(H.Taine)在他的《旅行手册》(Carnetdevoyage)中写道:“独自坐在包厢里,这三个小时,是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经历的最甜蜜的时光。”《旅行手册》中的另外一段话,则将这种平静的状态表达得更为具体:“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车轮努力地旋转,发出一致的噪声,就像风琴奏出的一个拉长的咆哮的音符。尘世与社会的所有想法都在我的脑中退去了。我看不见别的东西,只能看见太阳和乡村,在盛开,在欢笑;所有的植物,尽管都是绿色的,却如此多样,被轻柔的、带着温暖光线爱抚着它的雨所点亮。”
这样一种由车厢里孤立的自我以及火车强有力的机械运动带来的自我遗忘的愉悦感,如果做心理分析的解释,倒是很吸引人。弗洛伊德与卡尔·亚伯拉罕(KarlAbraham)都表明,在机械搅动与性唤醒之间存在着联系,并且铁路被称为这种唤醒最有力的动因。一旦受到压制,乘火车的乐趣就会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对火车的恐惧中”找到它的对应物,卡尔·亚伯拉罕将面对加速或者不受控制的运动时神经所体验到的恐惧,解释为对他们自己的性欲失去控制的恐惧:“这样一种恐惧与另一种害怕相连,人们害怕自己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运动中,他们无法控制。这样的病人,也同样会表现出对任何车辆移动的恐惧,只要是他们不能让自己随时停下来。”
就像旅行者们本身会像害怕出轨一样,他们对自己性欲的自主性感到害怕。在火车之旅中,对于出轨的恐惧在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火车飞驰(这是19世纪用于铁道旅行的一个典型术语)得越容易、速度越快,对于大灾难的恐惧就会越严重:我们已经引用了托马斯·克里维1829年的一个说法,铁路旅行“就是在飞,哪怕出一点小事故,我可能马上就死了,我简直没办法不去想这个问题”。
1845年德国的一篇文章说:“灵魂需要一定的限制,因为无论铁道之旅何其舒适,灵魂从来没有远离过人。”这表现了对于出轨的恐惧,对于大灾难的恐惧,对于“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车厢移动”的恐惧。
对于出轨的恐惧,事实上是一种无力的感觉,因为人们被限制在一台快速移动的机器里,又不能对它造成哪怕一点点影响。包厢的孤立将乘客封闭起来,强化了那种无助的被动感。包厢促进了机械运动令人愉快的体验,与此同时,它又以同样的程度成为了一个创伤的地点。其封闭的本质将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隐藏起来,不让外部看见:一旦旅客坐下之后,在整个旅程中,或者至少是从一个车站到下一个车站的过程中,他就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只是和他的旅伴一起。他与外部世界没有什么交流渠道,又因此存在实际的风险。
英国工程师彼得·勒康特(PeterLecount)1839年写道:“在公路上旅行,一位旅客突然发病,或者出了其他什么事,他不需要干别的,只要把头伸出马车的窗户,告诉别人他想要什么,马车就会停下来,他就能得到需要的帮助。但是铁道之旅的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在火车上,除非他碰巧坐在守车底下的座位,否则他发出声音都是徒劳。即便是他要死了,恐怕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越多,他越是努力,就越不能得到。”
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听觉上讲,包厢都完全从火车的其他部分中孤立出来,并且在整个旅行中都不能进去(直到1860年代,即便是快速列车,其包厢也只能从外面进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使得旅客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仅仅是因沉默而尴尬,变成了对于潜在相互威胁的担忧。火车包厢成了犯罪的场所——相邻包厢的乘客可能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犯罪就发生了。
这种新的危险,在19世纪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最大声的尖叫,被快速旋转的车轮的咆哮声吞没了,谋杀,甚或比谋杀更严重的犯罪,可能就会伴随着火车以60英里的速度飞驰而上演。当火车按照时刻停车或者还没到点就停车,查票员过来,可能会发现一节二等车厢变成了‘屠杀场’。我们可不是在信口开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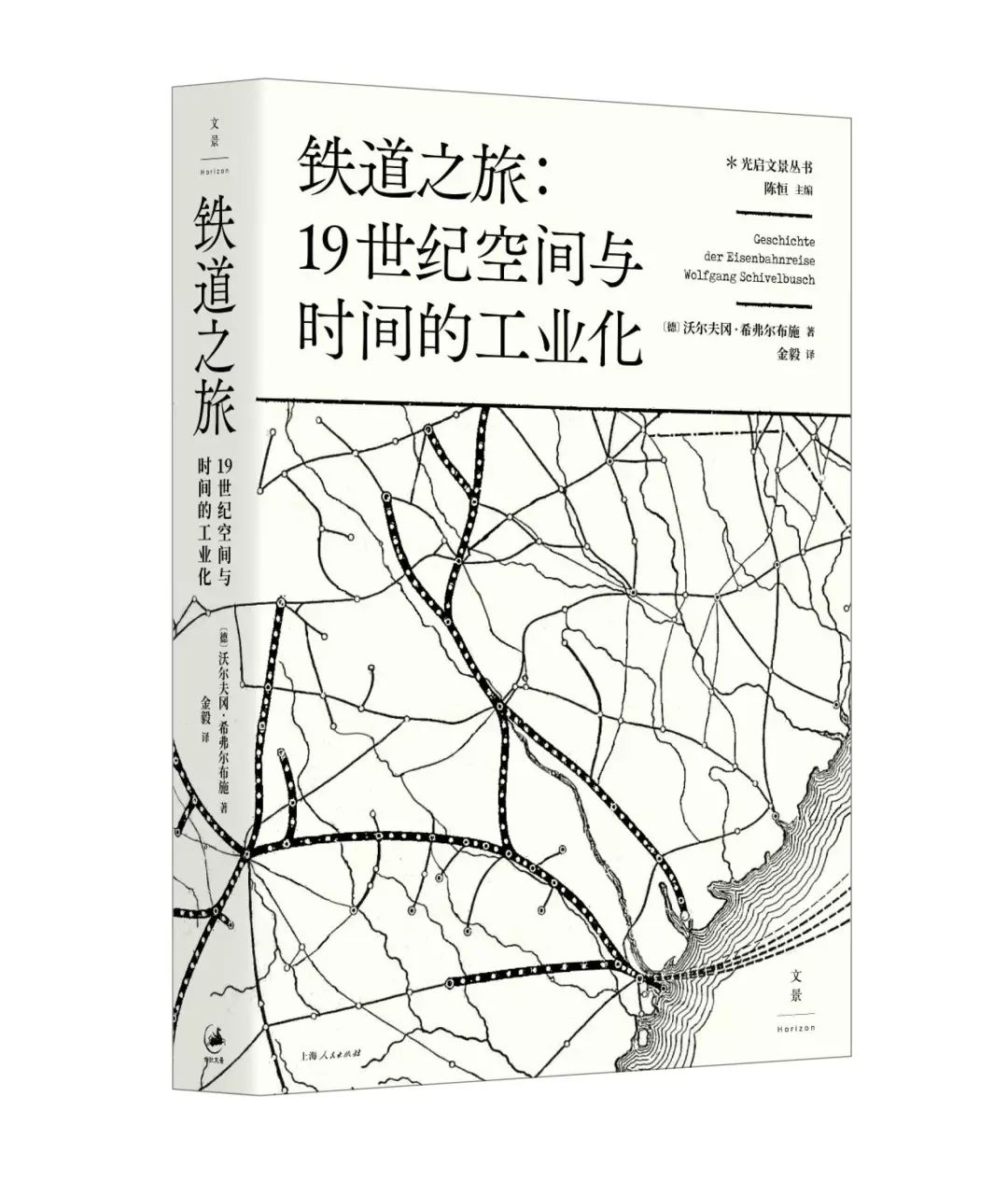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其余图片为出版社提供。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