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乌卡
1992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联合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在中国,它叫《望长城》,在日本这部纪录片叫《万里长城》,但对比了CCTV和TBS的两版,当年还不太会拍纪录片的CCTV一个劲地介绍长城雄奇伟岸和厚重历史。然而日本版本却仅用长城作为一个引子,把视角放到了长城脚下生活的河北农家,过年包饺子的热烈温馨的场景。
虽然比不了日本的版本,但那部纪录片中已经开始出现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身影和片段,成为后来中国纪录片创作变化一个有意思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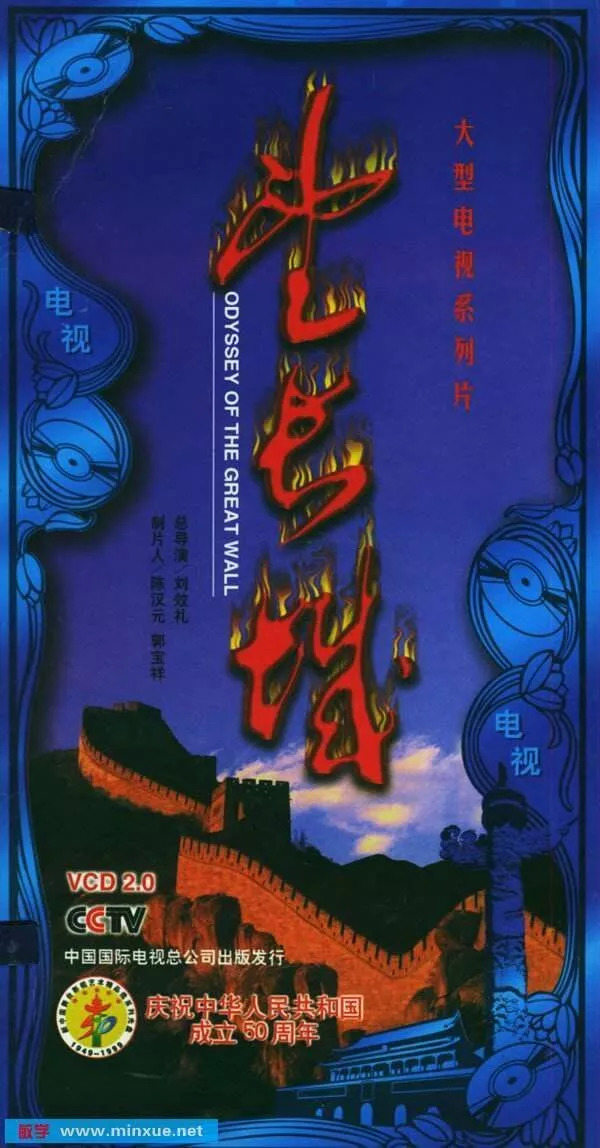
中国依旧神秘
由韩国放送公社(KBS)制作播出的《超级中国》在韩国开播后,该片收视率一度突破10%,远超一般纪录片平均约5%的收视率。部分韩国人称其为“了解中国的‘百科辞典’”。而对于纪录片制作大户的BBC而言,从《中国故事》到《中国老师来了》,再到《中国新年》等,中国题材依然吃香。
在每年五月举办的新鲜提案大会上,不少作品通过提案获得投资,或者借由赛事力量走向国际纪录片节,解锁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在纪录片制片人杰弗里·莱曼看来,中国依然是个传统的、神秘而传奇的国度,色彩瑰奇,值得探秘。前些年有《流浪北京》《归途列车》《遍地乌金》等作品深受西方世界关注,因为它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底层图景和“另类档案”;近年来一些官方制作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等也因为其制作精良和语态贴合而吸引了不少国际买方。

事实上单纯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和能表达价值观,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国产纪录片是不一样的。七年前,国家广电总局开始实施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并印发《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概也有此番背景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随着《话说长江》《望长城》《故宫》等纪录片的推出,以及一些独立纪录片在国际上频获大奖,外国人开始通过纪录片认识中国。但这个阶段远不能说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上取得了多大的效果,而是国产纪录片的创作本身经历了一次变革,从思维到形态等。
西方纪录片仍为主导
能明显看到,当今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仍然以西方纪录片为主导。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影视国际传播仍然十分脆弱,尤其是具有传播优势的纪录片更是发展滞后。
在一些展现中国的纪录片中,西方原生的纪录片往往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英国BBC在去年春节期间播出的《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示了春节的风俗、美食与喜庆气氛,颇受海外观众好评。虽然近些年国外制作播出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以往所持的批判态度有所消解,但话语权还是牢牢握在别人手里。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要大力提高国产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了6集纪录片《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西方主流媒体首次深入报道海上丝绸之路。该片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播出后,还在PBS属下的210家电视台、美国考克斯(COX)有线电视网、美国1号电视台广播网、环球加勒比地区电视网以及俄罗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地区播出。

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链条上,甚至形成了一条隐形的鄙视链。完全外国人制作的纪录片效果要好过中外合拍的,中外合拍的又要好过完全国产的。
例如获得艾美奖最佳专题纪录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后期制作奖、最佳灯光奖等6项大奖的纪录片《中国茶:东方神药》就几乎完全由美国团队拍摄完成。它是美国人试图用西方的眼光去研究茶叶的起源,渊源还有对世界的影响。它在美国主流电视台播出的同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老布什等政要都将该纪录片光盘作为个人收藏品保存。它也同时被美国佐治亚当地教育厅网络学校作为中华文化教材进行推广,成为了美国学生的文化教材。
而我们反观另一部同样题材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分别从茶的种类、历史、传播、制作等角度呈现,表达方式上也带有及其浓厚的东方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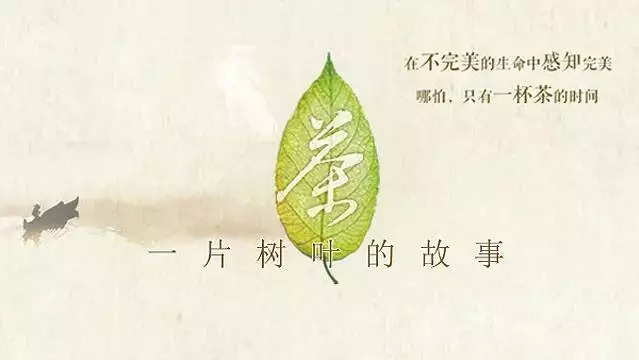
相同的题材,甚至在制作成色上不相上下,但国际传播的命运却截然相反。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传播的逻辑起点。
姿态比效果更好
另一个现状是,在中国主动传播的纪录片中,外宣型还占了多数。
例如近年涌现了一批以“一带一路”为题材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纪丝路》《一带一路》《重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丝寻梦录》等。这些纪录片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带着一种中国人自身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的文化,即使从个人和情感出发,也很难真正让外国人产生共情。
拿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一等奖的外宣纪录片《东京审判》来说,该系列纪录片共为两季,每季三集,每集48分钟。其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国家公祭日、“七七事变”纪念日等重大节点,在美国、加拿大、中国等海内外多家电视台和网站播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第一时间主动回击了日本NHK播出的同名纪实剧集《东京审判》中的错误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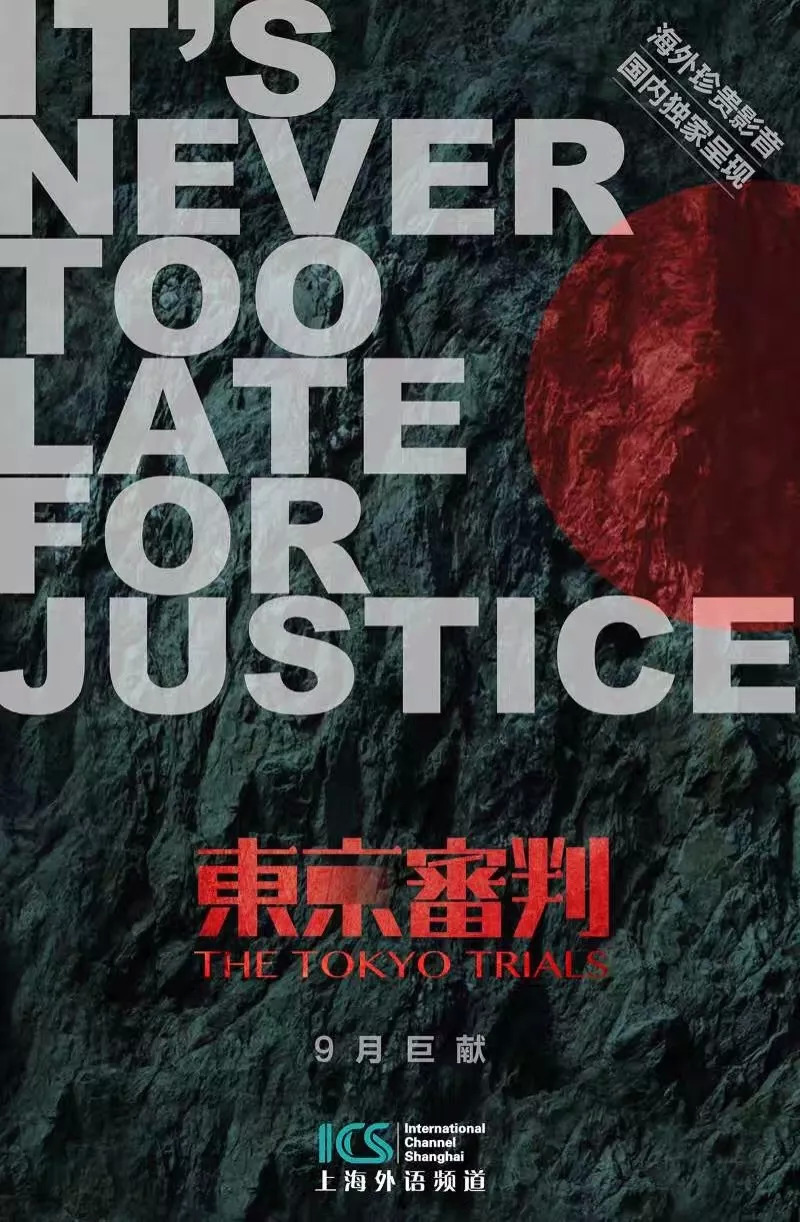
但事实上,回击的姿态可能比效果更有意义。
虽然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承载着中国的立场、价值观、国家意志,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但不同于人们容易理解的美食、旅游等软话题,像《东京审判》一样涉及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等相对枯燥难懂的领域的纪录片,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始终摆着一道纵深的沟壑。
事先设定论证结果,单纯的口诛笔伐是经不起学术推敲的,这样的电视作品也必然难长存于世。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粟屋宪太郎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对东京审判的研究,逐渐摆脱立场先行的办法,强调投入到史料里去。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专业研究还不到十年,这对主创团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有学者提到,要真正从“宣传中国”变成“传播中国”任重道远。“提高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力,在国际社会中发出正确的‘中国声音’,在传播的维度上,纪录片还是要善于谋求各国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及情感上的 ‘最大公约数’,借助人类共通的表达方式,提供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贴近不同观众的文化背景,增强富有亲和力的分享感,减少高高在上的凌厉态势。”
纵使国际受众身处的文化和国情不同,国际传播也很难“走出去”。但国产纪录片的创作者已经开始寻能够让中外观众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
“成功的纪录片都能或多或少为世界带来改变,但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做到的。” 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布鲁斯·考利说。怎么做?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的过程需要耐心,还需要每一位制作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