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清关于儿童领养的三个基本而复杂的事实:其一,每一次收养背后都有着巨大的损失。其原因可能是死亡、抛弃,或者是出于爱而放弃自己的亲人。这个被放弃的孩子已然承受了失去爸爸妈妈的痛苦;其二,从人口构成来看,需要有爱家庭的儿童和希望收养孩子的成人不成比例,想要领养孩子的家庭种族比例失调,大部分都是白人,而期待进入新家庭的孩子们就不是了。因此在这个领养过程中,组建多种族家庭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结果;其三,长时间以来,美国文化一直纠结于种族和身份问题。
结合以上三点,你不仅能开始理解为什么收养一个孩子会面临这么多挑战,同时也能看到美国文化中黑暗的一面,黑暗到就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都要嗤之以鼻。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小女儿的种种遭遇,就是美国儿童收养故事的一部分。
我是个福音派基督徒,年轻的时候,我的灵魂一直被圣经中的两个章节来回拉扯。一是《雅各书》对“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各书1:27);第二个段落来自《加拉太书》,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以上译文采用和合本圣经)因此,我和妻子不仅觉得收养孩子是我们的使命,同时也相信种族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么一个真挚信主的家庭团结在一起的阻碍。
因此,在2010年的夏天,我们飞到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去把最小的女儿内奥米·孔吉特·弗伦奇(Naomi Konjit Frenc)接到身边。和每一个被领养儿童的命运一样,她的故事也是以巨大的损失开篇的。一个未婚妈妈产下了这个女儿,然后把她交给了外公外婆,从此从女孩的生命中消失了。这对老人不过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拼了一把老骨头也只能勉强糊口。后来外公也离开了人世,内奥米和外婆开始忍饥挨饿,相依为命。内奥米2岁的时候,体重才刚过12.5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又被抛弃了——这一次爱她的外婆把被交给了一个领养机构,因为这个老妪实在养不活她了。
想想她承受过多大的创伤吧!内奥米只是一个刚学步的孩子,已经经历了死亡、饥饿和抛弃,过不了多久,她还要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这时候一个美国家庭出现了,把她抱起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她就飞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了一片一无所知的崭新土地上,和完全不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们看到内奥米的第一眼,整颗心都被爱占满了。但任何一个领养家庭的经验都能告诉你,爱不能抚平所有创伤,有些伤害会伴随终身。

我们给内奥米讲过她自己的故事,那时的场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就在田纳西州中部的一家披萨店里,我们抱在一起,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给父母的忠告:永远不要在餐馆里和孩子讨论难以启齿和严肃的东西)。这个晚上并不好过,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了,从此以后,面对那段不堪的过去,我们可以更加开诚布公。事实上,令人惊喜的是,那次谈话过后,内奥米对自己出生的国家更加好奇了,而且以此为豪,这就像是揭开了一块神秘的面纱,这个女孩从中解放出来,从此能够更加自由地拥抱自己的传统。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爱着对方,克服过去丧失亲人的创伤带来的阵阵苦痛。这么一个小女孩失去了亲生母亲和外婆之后,是怎么接受一个新妈妈并且对她产生依恋的?一个父亲又是怎么和这样一个小女孩建立联系的?要知道,她还没来得及学会开口说话,生命中唯一亲近的男人就已经去世了。除此之外,她童年时期的严重营养不良会造成发育成长障碍,就算恢复了健康和元气,小时候的问题也会一直伴随着她好一段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不容易,但依然有更大的挑战摆在许多家庭的面前。我们每天都提醒着自己,主已经给与了我们这一家无限的恩典。内奥米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而且兄弟姐妹都十分喜欢她;她会去教堂,也在上学,教会的弟兄姊妹和老师学生都竭力帮助她茁壮成长;她的爸妈工作还过得去,物质匮乏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
但在这个小圈子之外,还徘徊着令人不安的现实,而且有时这些不速之客也会径直闯入我们的生活。总有些人恨我们这种家庭,不希望它存在于社会上。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们连我们这种抚养着黑人小孩的白人父母都厌恶,关于种族身份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随之而来,白人家庭对其他种族孩子的爱会不会是一种“伤害”?甚至有时候人们会怀疑,收养儿童的父母是不是真心爱着自己的孩子们,有的人认为领养孩子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勋章”,好让这些父母到处显摆,向世界宣告自己有多么开明。
在收养内奥米之前,我们当然也明白,美国政治上反对跨种族收养的大有人在。1972年,美国黑人社会工作者全国协会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表态,称让白人家庭收养黑人孩子,就是在进行“种族灭绝”。但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到了21世纪,美国许多教堂都全情投入到了一场“收养运动”中,拯救迷途的灵魂,许多家庭继续在国内收养孩子,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把目光放到了海外。截至2004年,美国的国际收养达到了最高点,一共从海外带回了22844个孩子。他们之中许多人还有着特殊的需求,许多孩子和自己新父母的种族并不一致。

我们在2010年收养了内奥米,就在这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尔·杰森(Michael Gerson)写了一篇文章,为不计其数的收养家庭说出了心里话:“这是美国最高尚的事,我们关爱着其他土地上被抛弃的孩子。”那么他怎么看待多种族家庭呢?杰森在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国际收养并没有损害任何一种文化,而是指导着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校里单薄、富有争议的文化多元主义不同,在跨种族家庭里,你能看到感情具有超越种族差异的力量。”这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乐观主义精神,其中包含着我们的希望,希望兑现《加拉太书》中的承诺,并借此改变我们深爱的这个国家。
然而紧随其后的,就是激烈的反对声音。在国外,许多人声称文化帝国主义会损伤孩子对出生国家的民族自豪感,还有小部分人不断用骇人的虐待、剥削儿童的案例来挖苦、抹黑美国家庭。在国内呢,身份认同政治和对基督徒收养运动的公开敌视态度则引起了左翼对跨种族家庭的猛烈攻击——不过左派的攻势很快就被右派种族主义者迎头赶上,甚至在右派面前相形见绌了。
第一波打击来自奥巴马时期的美国税务局。美国对领养家庭进行财政支持,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抵免,而在2010和2011纳税年度,美国的税收抵免由不退款免变为了可退款的税收抵免。税务局也对此作出了回应,对领养家庭展开了大规模的审计工作,其范围之广十分惊人,在2011年,68%申请了收养税收抵免的家庭都接受了审计,而在201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69%。
我家也接受了这次拉网式调查。这时候我们家刚添了一名新成员,在帮她融入新家庭的同时,还要翻箱倒柜找出领养凭证,向税务局证明我们真的收养了这个孩子,我们申报了这么多抚养费,但每一笔都是切切实实花在她身上的,我们并没有欺骗政府。不只是我们,成千上万的家庭面前也摆着相同的任务,而且他们的收据往往更复杂,亦或许其收养行为的记录用的是他们看不懂的语言。2011年10月,政府会计办公室的一篇官方报告指出,税务局“没有找到任何收养税收抵免欺诈案例,没有任何一个申请税收抵押的家庭被移交犯罪调查部门。”
接下来,在2013年,作家兼记者凯瑟琳·乔伊斯(Kathryn Joyce)就美国的福音派基督教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儿童捕手:拯救、贩运、以及领养的新福音书》(The Child Catchers: Rescue, Trafficking, and the New Gospel of Adoption)。书中对福音基督教徒们收养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乔伊斯坚称整个领养行业充斥着腐败,而福音派基督徒被一种不详的“孤儿热”完完全全控制住了,他们的唯一动力就是给这些孤儿们传福音。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占据了大量新闻版面。随后,作者乔伊斯还在《纽约时报》的周日书评栏目和《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发表了文章,NPR的谈话节目《Fresh Air》也请到了她进行采访。
于是我们很快便发现,如果你是个白人爸爸或妈妈,领养了一个黑人孩子,就等于把自己放到众目睽睽之下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狠狠地批评你一番,因为你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相信自己能抚养好这个孩子。有时候这些批评十分直接,几乎是人身攻击,我们的情况是,大多数批评都指向了我的妻子。面对博客和推特上充满火药味的评论是一回事,在公众场合承受怒气冲冲、对人不对事的人身攻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惊呆了,我们彼此也讨论着投向我们的敌意:看看那些左派做了什么,看看他们是怎么说这个有爱的家庭的;看看在他们眼中虔诚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
在此之后,大概是2015年的夏天吧,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个转变。攻击我们家庭的声音中,左派的势力似乎没那么强大了,所谓另类右翼(alt-right)的攻势则越来越猛,这个另类右翼是一股受到特朗普支持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他们痛恨多种族家庭,鄙视跨国领养。他们把跨种族收养成为“你的家庭被另一个种族绿了(race-cucking)”,或者“养虎为患”。如果你被这些人盯上了,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人正紧咬着我们不放。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们的运动,还有部分原因是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我拒绝把票投给唐纳德·特朗普,于是他们就盯上了我们,蓄意复仇。
他们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内奥米的照片,她当时才7岁,然后用Photoshop把她放进一间毒气室里,特朗普手边就有一个按钮,掌握着我女儿的生死;他们还把她的照片P在了奴隶的棉花田里。这些人翻出了我妻子的博客,在评论区贴满了触目惊心的照片,照片中的非洲妇女不是已经咽气,就是奄奄一息。这些右派甚至让我怀念起被左派追着骂的日子——起码这些进步主义批评家们不会诅咒我的女儿去死啊。
我们的例子比较极端,主要是因为我们两夫妇都是作家,而且常常会写一些涉及公众的、有争议性的政治评论文。不是每一个收养家庭都会像我们一样,被政府审查、遭受左派右派的混合双打,看着自己的孩子走上种族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我们家的经历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领养家庭,但许多家庭确实也被外界的憎恨与无知困扰着。
白人父母正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之箭一根根射向他们的黑人孩子。键盘侠在社交媒体上大骂,这些家长不过是通过收养孩子来作秀,有些人则苦口婆心,教导这些父母说,有些事他们天生就无能为力,不能满足有色人种孩子的需求。指向我们家的憎恶更加来势汹汹,也许是因为我俩的身份,但这种憎恶之情是真实的,这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情绪总会找到法子侵入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们把内奥米带回美国的那年以来,海外领养就在不断减少。从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每年跨国领养的数量减少了72%,有一个原因显而易见:破碎的美国文化正在伤害着别的国家以及国内的众多家庭,同时,人们对领养的态度也正在改变。2010年,在我们启程去埃塞俄比亚之前,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难掩欣喜和期待,“你们该有多高兴啊!”他们眉飞色舞,反应就像面对所有即将做父母的夫妇一样。然而从那以后,我眼看着这种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你准备好了吗?”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急着给这些父母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未来潜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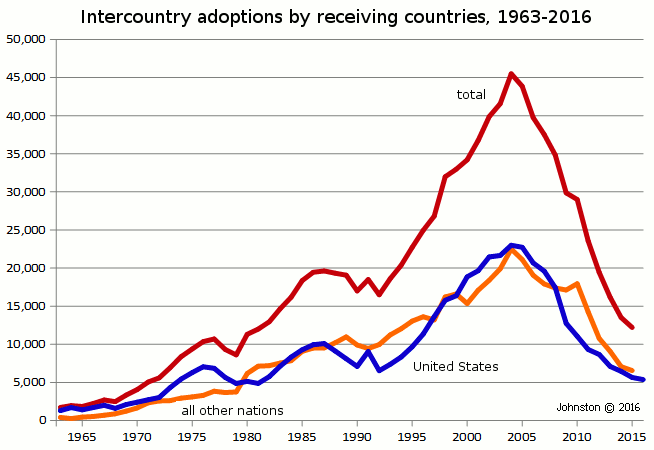
对我们家来说,我们能给女儿遮风挡雨,有一天她会明白的。以后我们还会向她坦白另一件事——这一次绝不会在披萨店说了——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再次相拥哭泣,只因为内奥米美丽的肤色,就有那么多仇恨正指向她,妄图折损她美丽的灵魂。我们会尽自己所能保护她的心灵,抵御那些企图“策反”孩子造成亲人反目的人,抵御那些声称父母的爱立不住脚,他们的信仰不过是压迫的来源,而不是生命和希望的种子。
我们爱女儿胜过爱生命。但2010年的理想主义已经消解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这一家折射的正是未来的趋势;现在我知道我们有多天真;现在我们恍然大悟,加拉太的承诺——我们都能“成为一”——在天国里是真实的,但在美国并不适用。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