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德里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当他们的财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遭滥用污染自然与环境、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无论富人、中产阶级、拾荒者,还是罪犯,无人能置外于这场毁坏与创造的矛盾。
本文选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第十三章,有删节。
资本深渊中的经济难民
文|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战士精神里没有太多空间用来关心弱者,这没什么好惊讶的。生活就是战争,这对那些不能战斗的人来说真是太糟糕了。
正在蓬勃壮大的布尔乔亚群体是构建这本书的主题。尽管他们只是德里的少数群体,但他们的很多财富实际上来自他们身处的一片贫穷海洋。从德里东南边界延伸出去的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大片土地,那里有三亿人口年平均收入为500美元。这些人不仅贫穷,而且在政治上还处于弱势,生活越来越糟糕。因此,他们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建筑、采矿和制造)廉价和几乎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印度的财富。
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差,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赶上印度经济的繁荣,而正是因为印度的繁荣。印度经济繁荣的部分推动力来自企业对农村的占领,大量的投资与穷困的农业和部落社群的利益相背,把印度农村变成了一片动荡混乱的战场。商业扩张需要土地,而印度大多数土地在小农手里,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在尼赫鲁时代十分稳固。由于多数农民每人只拥有一两公顷土地,而且大多数人不愿意出卖,既要合法又要达到企业创办要求获得成百上千公顷的连片土地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市场自由化后,人们见证了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其中涉及数百万公顷的农村土地。
有时候,获取土地的任务是由所谓的土地黑手党完成的。那些年里,许多巨大的财富由“土地整合人”取得。这些人中,有些使用黑社会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有些利用政治机构的人脉,不仅专横地重新分配土地,还非法使用国家资源(比如警察)来执行这些命令。但在很多情况下,对土地的夺取是由国家根据1894年的《土地征收法》(Land Acquisition Act)中的条款来实施的,这部法令由大英帝国颁布,目的是将殖民者从土地的历史所有者那里征用土地的行为合法化。印度本土精英在自己国家里引发的暴怒和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者在其他国家引发的暴怒极其相似。土地根据专制法律规定被收回,之前土地的赖以生存者只得到很少的补偿,有些甚至没有补偿。随后,土地被出售给企业,价格往往是原来的十倍,这些企业使用土地的方式显然摧毁了当地的生计。他们能很方便地雇佣土地原来的所有者作为建筑工人、矿工和工厂工人,因为这些人现在一贫如洗。
抗议自己的土地被强行征用以建造特别经济开发区或汽车工厂的农民们有时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直接被开枪射杀。但是如此大规模且具有破坏性的巨变不可能不遭遇抵抗。全国随时随地都有上百起抗议游行,都是针对征地的。最让政治集团头疼的是,一支毛派武装团体横扫了这个国家受破坏最严重的农村地区,而且在很多地方夺取了控制权。到2006年,武装团体在东部比哈尔邦、恰尔肯德邦(Jharkhand)、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到处组织起来,据说占领了印度五分之一的森林。总理曼莫汉·辛格当年宣布这些组织是“我们国家从未面临过的最大安全挑战”,这一说法让城市精英们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自己是和数亿身处困境的农民、猎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神话中才有的生物分享着这个国家。
他们没有卷入这场战争,大部分人依然保持着幸福的无知状态,但这场战争却是暴力而影响重大的。在矿产丰富的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政府出售土地的矿产租赁权,在这些土地上,有大量人口以打猎和采集为生。为了把这些人赶走,邦政府动用了民兵组织“和平行动”(Salwa Judum,意为“净化狩猎”)。和平行动是一个由主流政党扶植的武装运动,政府期望其能够消耗并击败在那几年绝望的日子里威胁国家的叛乱团体。在新政治任务的促动下,这个组织行为狂暴,掠夺焚烧村庄,强奸屠杀,并把部落人口赶进监狱。有几十万村民为了躲避袭击而逃走,因此把矛盾和对资源的竞争带到了别的地方。
然而,那些从土地斗争中成功逃走的农村社区也发现,靠以前的谋生手段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由于他们依赖降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雨量,很多农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平衡盈亏。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使天平不可逆地偏向了亏损的那一边。
其中部分原因是生态条件的改变,尤其是水。不断扩张的城市发现自身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这就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取水,逐渐抽干了方圆数百公里村庄和农业的用水。在农村建起的新工厂需要大量可预知的供水——毕竟有些工厂生产的是汽水,甚至瓶装水——只有当国家能够确保无论雨季还是旱季都能供水时,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才会进行投资。在水源不稳定的地方,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但市场自由化也改变了农业经济,为农民带来了新的收入选择,虽然这也使他们承担了更高的风险。总之,许多农民向前迈入了这样的新选择,因为20世纪60年代引入的高强度农业,即“绿色革命”已经耗尽了土地肥力,迫使他们去探索新作物和新化肥。与此同时,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希望印度农民为加工食品提供原材料,这给他们带来了新收入和新生活方式的机遇。许多农民因此选择不再种植粮食,而是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香料或鲜花,来追求更高的回报。但这使他们成了一个在财务上非常脆弱的群体,严重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例如,食品成了他们不得不购买的东西,而食品价格在那些年里一路飙升——这种赌博有时会在一无所有中收场。
另外,1991年后印度历届政府签署了各种国际贸易协定,承诺接受和执行外国公司对使用其产品的要求,其中包括保护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发布的新一代专利种子。农民大量定购这些产品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条件太差,而这些种子被视作解决方案。但根据许可证的规定,农民每个季节都必须从生产商那里购买这些种子,其中许多种子被设计成无法繁殖的,使农民不能按照传统做法为下一个季节的种植留种。这些种子还常常被设计成要配合特定的化肥和杀虫剂产品一起使用,这样不仅需要大量的现金支出,还需要许多培训,而培训却经常是缺失的。在环境背景已经变得更加严峻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使用新型化学品耗尽他们的土地,并进入了一种很难应对的债务螺旋。他们往往和当地放高利贷的人牵扯在一起(这种情况正如在许多其他事情上,穷人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和富人同样的资源)。
所有这些,对农民来说是致命的。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每年约有一万五千名印度农民自杀。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鉴于受印度农村危机影响的人数众多,情况的轻微恶化就足以释放出大量的难民潮,而这些难民自然而然地涌向城市。199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之间,德里人口增加了七百万,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他们是已经备受推崇的现代化戏码中的定型角色:因为土地被开挖采矿而支离破碎的部落,无法再用自己的土地喂饱自己的绝望农民,以及因为新工厂的出现而被淘汰的刺绣师、窑匠和木雕师——而他们正是古老传承的最后一代。
这些人中,有的最终成为破坏他们生活的那些富人的保护者和生活保障者——因为德里的富裕家庭非常需要仆人。事实上,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能够轻易买到廉价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经常雇用司机,而一个女佣大清早到家里来打扫地板上前一天积累的灰尘也是必备的。富裕一些的家庭永远有保安坐在家门外的塑料椅子上。对于这种不用做事的工作,主要的资质要求就是他们还活着,还没死掉。
劳工的前呼后拥让富人们觉得自己更加尊贵,而且这也为他们的“得体”标示出绝对的界限。对于富人来说,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是不正常或不恰当的,这种想法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构造。比如说,没地方停车对他们来说不是困扰,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开车——司机把他们放到餐厅门口,然后去兜圈,直到他们出来。每件普通的任务——从寄一封信到买一张火车票,都需要在人群中经历冗长的推挤,这样的事实没有受到中产阶级的谴责,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做过这些事。一般来说,这个城市的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们会按铃叫一个佣人来找车钥匙,或是叫一个服务生端起就在面前的红酒瓶,为他们把酒倒进杯子里。
雇佣劳动力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许多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洗盘子、洗衣服、给孩子做饭——对印度的中产阶级来说是陌生的,其结果就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常常能在其他方面更有生产力。然而他们和家里佣人的关系却往往离奇地充满戾气。如果你听到中产阶级抱怨他们的女佣,你会产生体谅他们的感觉,因为你觉得这些妇女的作用不是在房子里进行必要的劳动,而是弄丢钥匙、偷窃珠宝、打破碟子、浪费电、弄坏衣服、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教孩子坏习惯、让水果腐烂,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们会一整天不来工作,从而摧毁其他每个人的生活。原因是(按照她们的说法):她们病了,或者孩子被野狗咬了,或者因为碰到积水里带电的电线触电了,或者她们的贫民窟正在被拆毁,或者丈夫死了,或者姐妹要在某个很远的村庄结婚,或者某些其他同等荒谬的故事。这一类由女佣造成的痛苦是中产阶级谈话的主要内容,其程度会让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特权的人似乎为穷人的背信弃义投入了那么多东西。这些中产阶级把他们生活中的每件错误都归咎于他们的女佣,似乎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毕竟几代人以前,很多德里的有产阶级自己本身就是难民。现在,他们看着这些新移民的眼睛,这些为他们做饭、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似乎会让他们想起那些宁愿不再记得的暴力和不愉快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的推论是:在中产阶级心里,佣人们配不上他们的薪水。佣人的薪水不是他们对中产阶级家庭贡献的回报,而是对无能者的慈善捐赠。中产阶级喜欢把自己看成不被重视的恩人,他们并非把穷人看作生产引擎,而是当成一群仰赖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虫。正是他们——中产阶级,为经济贡献了真正的价值,他们决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仅限于自己和同类人群享受。即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他们仍然会愤怒地反对给为他们服务的人加薪。当你搬到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社群,老居民们(其中一些是百万富翁)会告诉你,收垃圾的人每月会问你要100卢比,但你只能给他50卢比。“否则对我们所有人的收费都会上涨。”在要花费3000卢比的晚餐上,人们不断讨论着一个女佣的闲话,因为她要求把2000卢比的月工资提高到3000卢比。
抱怨这些事情的人应该知道工薪阶层的房租上涨速度和其他人一样快,他们肯定知道食物价格每年上涨幅度高达12%,但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仍然被视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近乎偏执地认为自己在被穷人“掠夺”。他们把上门卖蔬菜的小贩描述为“小偷”,而众所周知,人力车夫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载你一程”。印度的繁荣属于中产阶级——这是他们的时刻,他们会为之疯狂战斗。 在一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400美元的国家,平均收入的轻微变动对于极少数(比如年收入为6万美元)的家庭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九成的人从印度崛起的中产阶级中被逐出,他们对于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要求是非法的。经济自由化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一条反复出现的口号——“记住穷人!”仿佛是为了回应这条口号,现在似乎是时候要忘记它了。
然而,穷人对中产阶级财富的新积累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印度农村的灾难不仅创造出了唾手可得的家庭佣人,也为建筑公司和工厂主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为工厂主创造了财富,同时这些人也为有专业人才工作的管理咨询公司和广告公司提供了劳动力。他们通过对采矿和建筑公司的投资创造出可喜的股票市场回报,还为有车阶级建造了道路和住宅。但是,再一次,天平牢牢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因为愿意劳动的人绝对数量庞大,雇主从来不必担心上哪儿找下一批工人,所以他们几乎不用付钱就能要求工人进行任何强度的劳动。工厂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全年无休的情况很常见。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到每天4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人有养老金或保险。印度工厂现在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增加了工人劳动的强度,但对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自由化给整个体系带来了额外收入,那么这些收入通常是被承包商而不是被工人拿走了。
事实上,经济自由化后的十年里,厂主对工人的谈判力量发起了侵略性攻击。最初,德里工厂约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雇工,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享有更高的工资,还有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并受到各种法律保护。许多工人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新压力,这种情况对工厂所有者来说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他们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常常是大批量开除。到了2000年,七到八成的工人是临时工,相应地,他们的法律和经济状况也更加不稳定。工人个体无法对自己的情况提出申诉,因为有一大堆人等着取代他们的位置,而大规模抗议会遭到严厉的处置,经常伴随着警棍和催泪瓦斯。警察似乎总是毫无疑义地站在工厂那边,哪怕抗议的起因是由于工人死亡或管理层离奇和带有虐待性质的暴力。
与中国不同(那里很多工人吃住在宿舍,然后由班车送到工厂),印度雇主对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设施投资很少。工人只有临时工棚,而且往往没有活水可用,因此工人很难实现对自身最低限度的保护——包括维持健康,以及在几小时后回到工作岗位之前能获得足够的休息。不用说,工厂生产出了大量的“人类边角料”——生病了不再能工作的人;年满三十五岁,年纪太大的人;那些在机器上失去了手指和手,因此除了在街上乞求,别的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但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况对雇主来说也不方便,因为他们的工人和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不打招呼,说走就走。他们会突然就回比哈尔邦去了,因为有传闻说当地的就业前景有所改善;他们会请一个星期的假去参加某个宗教节日;或者他们只是换到隔壁的工厂,因为那家厂主为完成紧急订单,临时开出更高的工资。为西方大连锁店供货的纺织品制造商通常有六十至九十天的生产和交付时间,否则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在之前提到的劳动条件下,要确保一切都按时完成,这才是个大问题。但雇主似乎认为他们的工人是外星人,是不服从到骨子里的生命,不相信与他们之间有达成任何和解的可能性。他们与神秘莫测的工人心灵的唯一接合点就是金钱,所以这是他们施加压力的地方。在一些工厂中,工人每月拿的是最低工资,约6000卢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勤奖”——如果他们有一天没有上工,甚至哪怕是因为得病,这笔钱也会被扣掉。但即使是这样的措施也无法完全保障工厂这个机械化、可预测的空间里不会出现人力资源的剧烈动荡。这些工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边缘,受各种紧急情况所困扰——这牵涉到他们在这个国家偏远地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和中国不同,这里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是男性)。即使财务上的损失和这些紧急情况一样严重,通常他们也不可能在所有醒着的时间里每天都来上班。
21世纪印度穷人的情况当然和当地动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以及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缺乏同情心。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在这里工作的穷人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他们还属于世界。到21世纪初,事实上,可以说全球经济的很大部分正在亚洲农村的绝望中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那么多制造业转移到了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原因正在于这些地方运作的制度(尽管运作方式不同)。“正常的”资产阶级生活,无论在德里还是纽约,都需要大量参与其中的劳动,而这只有当劳动力保持在非常廉价的水平时才有可能。最终作用于印度劳动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印度富人的阶级藐视,而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并对人类劳动充满了无限渴求。亚洲农村生活的死亡影响了上亿人,并成为一个绝望的水库,供这个逻辑取水。
一位具有不同寻常自我批判精神的纺织厂主对此有自己的观察,她思考了这个自己在其中扮演节点角色的系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有个性的资本家。你可以自己决定想要创造怎样的风气。现在,你是不是个‘好人’没关系。完全无所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心,但仍然照做不误。整个系统以绝望为食,而我们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当被问及如何解决农村问题时,一名国大党财政部长说,他要让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消失。他说,现在八成五的印度人需要住到城市里。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七成也就是超过七亿的人口还住在农村——仿佛他金口一开,百分比就会神话般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这些数字反映的事实是,城市精英已经丢掉了想象农村的能力,并由此丢弃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同胞,他们只是希望这些人消失掉。一派田园风情的广告牌为叫“普罗旺斯”的地产项目和类似的印度乡村做广告,就像有这么多空着的“生存空间”等待着中产阶级搬入似的。但城市居民不再理解的是,农业可以支持的人远远多于工业,而且如果农业遭到破坏,印度将面临暴力危机。21世纪早期印度劳动力的廉价源于一个事实,即巨大的过剩,这意味着劳动力不仅易于获取,同时根据“过剩”的定义,也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被使用。大量印度穷人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他们只是被剩下了。就像巴尔斯瓦的居民,他们和主流经济的狂热只维持着最微弱的联系,并被抛到了一个充满倦怠和衰败的荒谬的平行宇宙中。
“我们正在为自己累积巨大的问题,”一名大型私募股票基金的所有者说,“人们谈论印度的‘人口红利’,指的是最近的高出生率可能带来的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口的优势。但我无法这样看问题。我们每年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市场上没有可以给他们做的工作。唯一能吸收这个量级劳动力的是电子和纺织品制造行业,但是所需的行业规模和我们现有的规模不相称。
“我们的IT行业很发达,但印度的IT和BPO行业一共只雇佣了两百万人。零售和餐馆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那只能再增加四百万到五百万个岗位。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子和纺织制造业能为一亿人提供岗位。印度没有完全掌握这样的行业,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为年轻人提供工作。这是个巨大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对印度这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更多具有历史意识的观察者回想起欧洲工业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农村生活,当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新贫困人口浪潮。同样,这些人口也远远超过了监狱、救济所或基础设施项目用工需求所能容纳的数量。对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切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之后历经数个世代才能愈合,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们是大量剩余的“下层”,无望获得更好的命运。但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欧洲拥有一种21世纪亚洲所没有的惊人可能性,那就是“新世界”。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尤其是北美对欧洲的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化造成了大量人口无家可归和失业,而这些国家扮演了安全阀的角色。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约七千万人离开欧洲前往“新世界”,这个数字是工业化初期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大约一亿三千万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当然,在同一时期,数以千万计的“新世界”原住民被同时发生的战争和疾病消灭了。)
21世纪的情况则不同。印度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是接近四亿人了,很显然,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这么多的多余人口。要如何使他们融入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且不用涉及种族灭绝或世界大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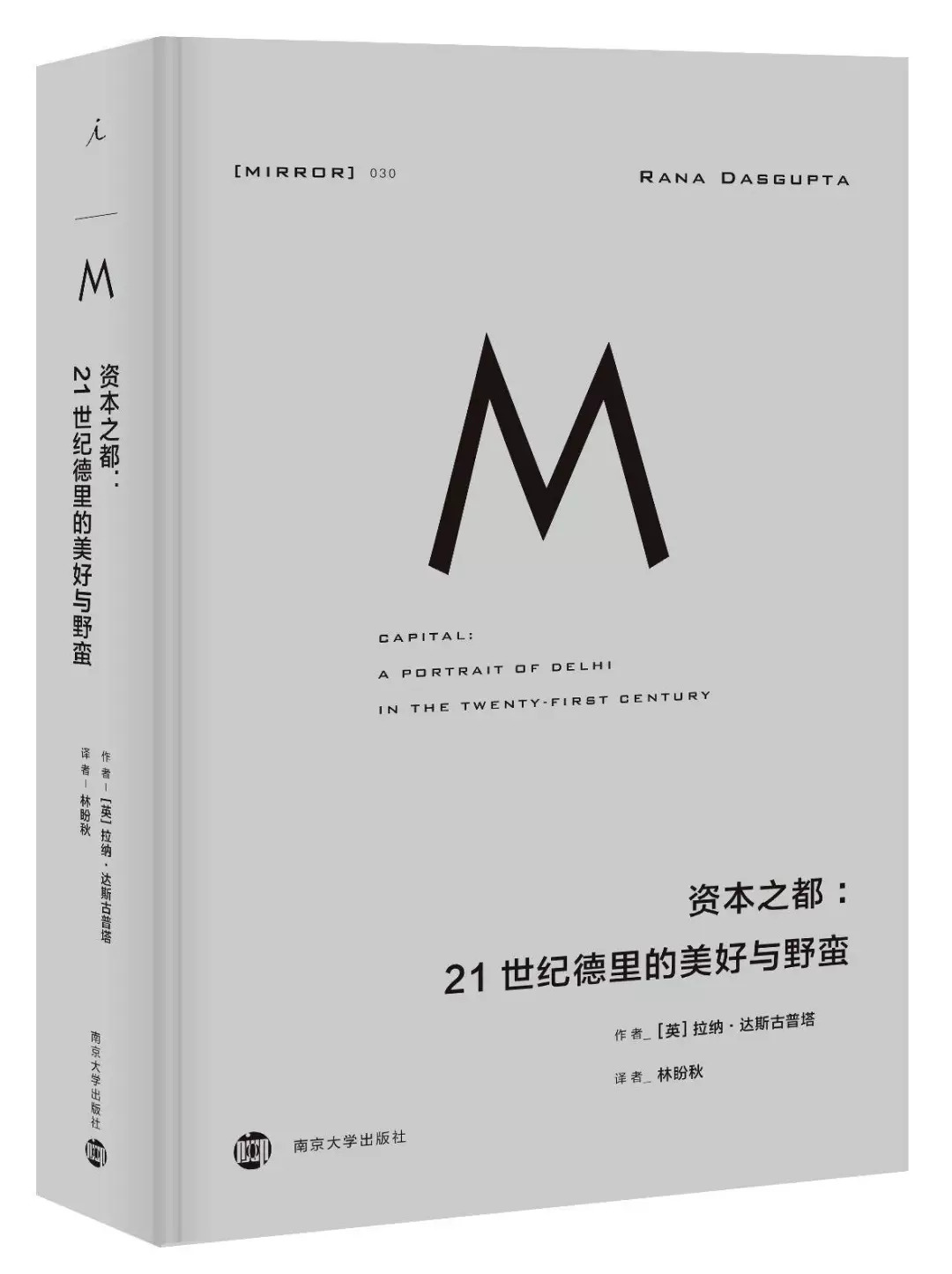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2017年4月27日,印度德里,街头流浪者。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理想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