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10月21日,三位学者、作家在正午酒馆聊了聊波拉尼奥。从他的小说《智利之夜》谈起,讲到了很多重要的文学话题。今天我们刊发活动的记录。
波拉尼奥:最后一代拥有神话的拉丁美洲人
对谈|范晔x孔亚雷x 哈维尔·费尔南德斯
一
主持:感谢亲爱的读者们,我们跟波拉尼奥又一次相聚在这里了。今天是因为《智利之夜》,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范晔老师,孔亚雷老师,另外一位是来自西班牙大使馆的教育参赞哈维尔,他是一位波拉尼奥的研究专家,博士论文写的是美国叙事文学对波拉尼奥的影响。
今天他们三位从《智利之夜》起头,来讲一讲波拉尼奥,希望大家有一个温馨美好的夜晚。
孔亚雷:今天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刚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现在正在实现,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水换成啤酒,我觉得谈论波拉尼奥,非常适合用啤酒来谈论。哈维尔刚刚说,最好用龙舌兰酒,我说这个对我来说太重了,太强烈了,怕影响我的发挥,所以啤酒就可以了。
我们先喝一点,敬波拉尼奥。真的,为自己爱的作家站台是非常幸福的,波拉尼奥真的是影响了我们很多人。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影响你判断这个世界的方式,你看完他/她以后,对人生的处理方式会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样的作家已经有很多,比如说最古老的托尔斯泰。我一直在重读托尔斯泰,我每次搞活动,都要推荐托尔斯泰,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活着,不读托尔斯泰,就跟没做过爱和没有喝过冰啤酒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也可以把波拉尼奥加上。
哈维尔写了一本著作,讲波拉尼奥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我读了所有波拉尼奥的英文译本,还有很多美国作家对波拉尼奥的评价,我就发现,自从波拉尼奥出来以后,很多英语文学的大小作家,整个文风完全受到了波拉尼奥的影响。我刚才跟哈维尔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一个作家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然后他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反过来又去影响那个国家的文学,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妙的。
范晔: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格外的放松,因为我旁边这两位都是真正的波拉尼奥的专家,或者说粉丝级的,孔亚雷兄读的波拉尼奥比我多很多,哈维尔更是这方面的专家。刚才切磋过了,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段位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今天特别放松。
《智利之夜》出来,其实还真的挺高兴的。因为我们称之为波拉尼奥宇宙的很重要的一个星群,又拼上了一块。波拉尼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像是一块钻石一样,有很多的侧面,所以《智利之夜》出来,我们可以多看到他的一个侧面。
我想说两句《智利之夜》里面的鸟类问题——稍微有点剧透,但我想了一下,问题不大,因为波拉尼奥的作品是特别不怕剧透的,哪怕我给你复述一遍,你都完全可以去看,而且你会发现我复述的,跟你看的还不一样。《智利之夜》提到一段很有意思,大家可能也知道,这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神父,他受了一个神秘的委托,去欧洲考察,考察什么呢?考察欧洲的神父是怎么养猎鹰来猎杀鸽子的,为什么神父要猎杀鸽子呢?就是防止鸽子排的粪便对古建筑造成损害,所以很多神父都要养猎鹰。
这是一个神秘的委托,而且委托他的人也很有意思。这两个人的名字,西文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游戏,你稍微把单词的顺序调整一点,就能看得很明白,一个是“仇恨”,一个是“恐怖”或者“恐惧”,这在西方文学的传统里面,古老的《天路历程》就是这种,把抽象的概念人格化,我路上看见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善良”。这里波拉尼奥多少带点戏仿,运用了这么一个手法。
后面还有一个委托,两个委托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平行关系。为什么呢?后面一个任务更有意思,是这两个神秘的人物又请他去教智利军事政变后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教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一个任务是神父教导猎鹰捕捉白鸽,第二个任务是神父教导军人对付他的敌人,就是对付持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实际上将军、独裁者跟猎鹰在类比链里,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如果你觉得这个太牵强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个梦,就是当这个神父将要回到智利的时候,他梦见整个天空全是黑色的猎鹰,所有的猎鹰都从欧洲飞向美洲,然后他回到智利以后,很快就发生军事政变。
当然这是猎鹰可能的一个阐释方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猎鹰还可能是一个文学评论者。我们一般把波拉尼奥当做小说家,如果大家对他了解更多的话,也会把他当做一个诗人,他也喜欢把自己当做诗人。但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另一面,就是波拉尼奥其实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但他的方式不是写那种所谓的学术文章一样的文学评论,他是在用小说来做文学评论,他用小说写他自己短短的拉美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他有的时候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建造出一个文学谱系,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先行者,他会把一些大家忽略的作家、诗人,重新挖掘出来,而对一些大家都非常崇拜、赋予光环的人,有意摆出一个蔑视、冷落的姿态。所以波拉尼奥实际上就是有这样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色。
这里面的猎鹰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我个人感觉也是一个镜像。书里面已经露出这样的蛛丝马迹,比如他谈到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就说“他有猎鹰一样的眼光”。像波拉尼奥这样的人来说,这些比喻都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的,都是有意给大家留出一些可能的解读的线头的。但波拉尼奥也有这个问题,他是里面好多密码式的东西,他的密码不是一对一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密码只有一个解读,波拉尼奥的密码不是这样,可能有很多种解读,他永远有一个不断变换,不断生成之中的密码本。
我觉得我说得可以了,现在赶紧让真正的专家哈维尔谈一下。

二
哈维尔: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好,接下来我会用英文说,之后还会用西语朗读一些片断。
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出版商世纪文景公司,以及在场的两位老师,接下来我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要读《智利之夜》这本小说。首先我觉得《智利之夜》这本小说是一个很好进入波拉尼奥文学世界的点,通过阅读这本小说,你可以更好的探寻波拉尼奥的文学密码,文学世界。关于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评论界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些评论家就喜欢长篇,有的评论家喜欢短篇,长篇有两本,是《2666》和《荒野侦探》,短篇的是《智利之夜》和《护身符》还有《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评论界将这三本短篇小说集评价为The cicle of Chile,意思是这三部作品之间的内在有许多关联,有一些角色分别出现在这三部小说之中,这是波拉尼奥玩的文字游戏。虽然这本小说只有150页(编者注:此处指西语版,中文版为227页),但里面有很多他对于世界文学,包括一些著名作家作品的评论,你可以看到他在邀请你进入他的世界。
接下来我会提出一些问题给两位老师,首先就是你如何看待自我身份在这本小说中的作用?我们在书中看到一个在病床上的老人,还有一个年轻的角色,这位老人对这位年轻人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无理,对我这么多意见?”这个年轻人也一直出现在这个老人的回忆之中,两位老师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孔亚雷:我先来简单地讲一下,一个美国评论家曾经说,波拉尼奥的作品分成三部分,一个是超级长篇,像《2666》这样,一个是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还有一个就是短篇小说也非常棒。他这三个文体都处理得非常棒,对短篇小说,对超长篇,对小长篇,对文体本身都做出了某种拓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很多作家对评论家说,波拉尼奥的一个短篇小说会拥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能量、容量。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他的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它像一个密度非常大的小黑洞,同时因为它篇幅很短,又很轻盈,这是波拉尼奥非常迷人的文学风格。一方面密度非常坚实,没有那些废话,内容非常丰富,像个黑洞一样,容纳了所有的东西,同时非常的轻盈,像羽毛一样。
刚刚哈维尔说的自我的问题,如果在他的三个文体里面挑一个代表作,比如超长篇,我们挑《2666》,短篇小说,在我来说肯定是挑《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如果是一个小型长篇,我就挑《智利之夜》。在波拉尼奥的文学里面,他有一个秘密的核心,就是自我的问题,你会发现,波拉尼奥几乎90%的主人公,不是作家就是诗人,即使这个神父,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这不是偶然的,感觉所有的人物都有波拉尼奥自身的影子在闪耀。
我觉得它的核心,在《2666》里面非常明显,就是一个文学抵抗世界之路。你会觉得,用小说,用文学来抵抗这个世界,是很可笑的,不是吗?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笑的,就像一个人打一个风车,这场战斗是必败的。我觉得这是波拉尼奥非常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场战斗必败,但是我们必须打这场战斗,就好像必死论,我们必须好好活着,我们更加要好好活着。
而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完美之处在于什么?主人公不是作家,他是神父和文学评论家,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混合体。哈维尔告诉我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就是智利确实有这样一个人,他既是神父,又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这就更加神秘了,更加奇妙了。你想想,这两种身份融合在一个人身上,神父,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文学又是另外一种宗教,我甚至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暗喻,就是对波拉尼奥来说,文学就是他的宗教。所有他的作品都体现出这一点,他对文学,不是以一种造作的处理方式,他是一种革命者的方式,就像《荒野侦探》一样,他用非常狂野的方式,运用文学作为武器。你看他的写作方式,那种长句的运用,那种近乎游戏的写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点。
包括刚才范晔说的,这个书里其实有四个平行的有趣的故事,一个是他跟另外一个有名的评论家的交往,一个就是鸽子,一个是他的马克思课,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了在当年的智利有个文学沙龙,但是这个文学沙龙的房子,居然是折磨革命志士的地方。你想象一下,我们正在高谈阔论,喝着威士忌,谈论着文学,就在这个地下室,有一个地下党烈士正在被折磨,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折磨至死。这里有一种非常悲伤的东西,就是文学有时候显得那么无用。包括鸽子,也非常的讽刺,你想,鸽子本来是教堂的一个象征,象征和平,象征美好,随着鸽子屎成了破坏教堂的东西,需要猎鹰来保卫,这就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吗?我觉得这里面充满了这种对比和讽刺。波拉尼奥编织着一个非常迷人的黑洞,通过他那种绵延不绝的语言方式,通过那个结构——他非常神奇,分为两个段落,最后一段只有一句,前面全部是一段,非常波拉尼奥式的。
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意思,我再听听范晔有什么看法。
范晔:我顺着亚雷兄再说一下,还不是自我的问题,就是文学里面恶的问题,其实这是个大问题,一会儿我想听听哈维尔怎么说说文学与恶的关系,其实这是波拉尼奥核心的主题之一,它里面不光是一个文学对抗恶,很多时候,文学会和邪恶共谋,或者说共同在场,比如说《美洲纳粹文学》,纳粹可能也有好文学,但是它在伦理上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波拉尼奥非常迷恋的一个问题。
孔亚雷:因为我觉得他不需要回答。
范晔:是的,他是不需要回答。但我觉得有时候我感觉也像一个深渊一样,这个问题都不敢多想。我们今天前置性地把文学想成一个本质上是善的东西,但它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个恶还不是说我为了自己装点生活,做出一个背叛的姿态,追求一点恶,不是那种东西,这个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还不是个人的,是建制性的。这个我先别说了,因为我也功课做得不够好,可以听听哈维尔怎么说。
我回答一下刚才说的自我身份的问题,其实具体到这个小说,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设定,就是一个“衰老的年轻人”,从头到尾不断出现,这个衰老的年轻人不断地指责我们独白的主人公,主人公从头到尾实际上也在回应他,但到最后,他透露出一个消息,说好像那个年轻人就是他。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年轻人是他的第二自我,或者说是他良心的一个化身。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衰老的年轻人,也可能是波拉尼奥。因为在里面有一个细节,他说50年代末的时候,衰老的年轻人大概五六岁,这正好是波拉尼奥的年纪。这个我觉得不算是闲笔,因为这种作家不会有这种闲笔,所以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控诉他的人是波拉尼奥这一代年轻人,新一代的拉丁美洲人对上一代人,提出的控诉。
原来我翻诗集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波拉尼奥在作品里面,常常会出现自己的身影,或者是化身。在叙事文学里面,他会用笔名或者是符号,比如说《荒野侦探》里的贝拉诺,在短篇小说里面,他干脆就用字母B出现,但是在诗歌里,他就用自己的名字“罗贝托·波拉尼奥如何如何”,“波拉尼奥如何如何”。可能诗歌对他来说是更私密的文本,自传性更强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生前诗集都已经整理好了,目录都已经排好了,但就是没有出版,也有可能他觉得“这是我非常私密的东西,将来就留给我儿子、女儿看”,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会想起一句俗话,说“你要想看一个人的自传,就去看他给别人做的传”。我的学生说,波拉尼奥其实是一个传记作家,他不停地为这些被遗忘的人作传。他特别热爱那些被遗忘的,或者说边缘人,特别是作家,还有诗人。对他来说,诗人最重要,因为他对诗人有他自己独特的定义。所以他在为这些被遗忘的人来作传,不管是《荒野侦探》也好,《2666》,其它的短篇也好,诗歌也好,为无数的诗人作传。有些是真有其人的,把他们从历史的深渊,被遗忘的深渊挖掘出来,有些是他创作出来的。在拉美文学史上,这也是有传统的,鲁文·达里奥,尼加拉瓜的大诗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文本,我们可以翻译成《奇人传》或者《异人传》,还有博尔赫斯,有一个中文的译本叫《恶棍列传》。我们可以找出这么一条谱系出来。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他为这些奇人、异人、被遗忘的诗人作传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塑造一个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自己,为自己来找到一种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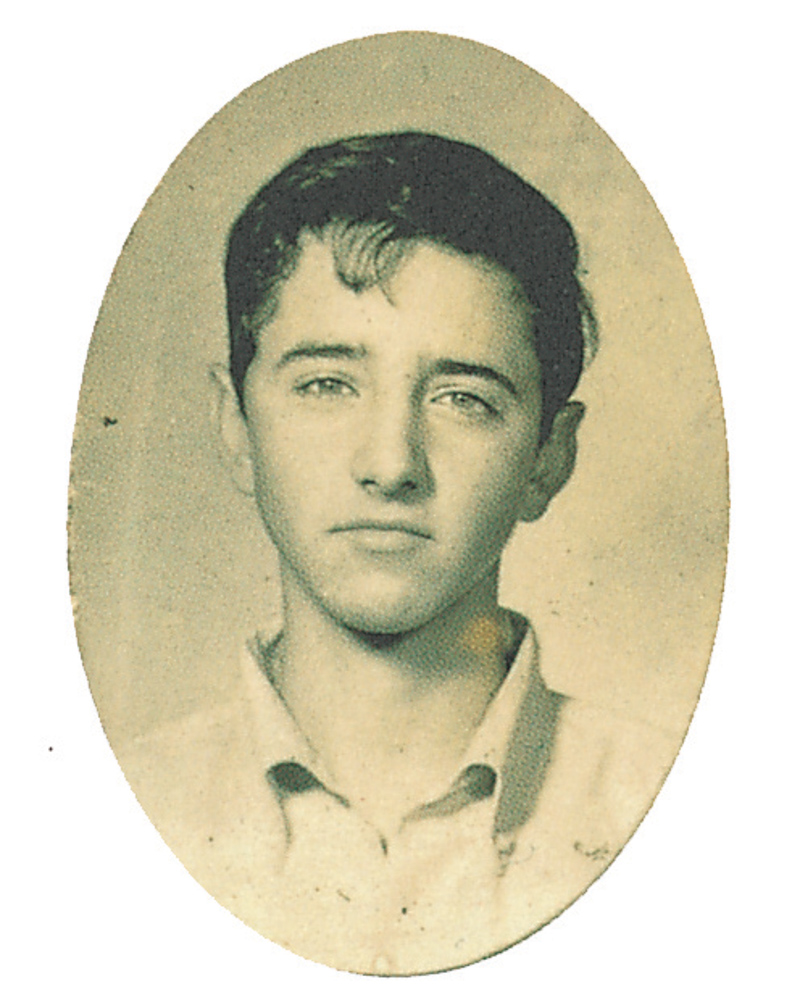

三
哈维尔:两位老师都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点,我们在三个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病床上的老人,脑海中有个年轻人一直拷问着他。这其实跟波拉尼奥的成长有关系,他成长在暴君独裁的国度一样,这是他们那代人必须经历的。其实所有波拉尼奥的小说,内在都是有关联的。在某本小说的开头,他说我们拉美人无法逃避暴力和独裁。这本书成书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晚期,刚才范晔老师也谈到了绝对的恶,你现在回想一下,那个年代拍出来的电影,《沉默的羔羊》,94年的连环杀人案的电影,其实“恶”是那十年最重要的主角。波拉尼奥非常善于写恶的题材,他也非常善于谈论恶,谈论同理心的缺失,谈论人性的自私之处。我们就看到这本书中,主角从一个喜爱文学的爱好者,慢慢变成一个文学评论家,再慢慢慢慢演化成一个孤独老人的故事。
刚才孔亚雷老师讲到波拉尼奥的内核,谈论用文学如何抵抗,接下来我也会讲我的一些观点。
我们看到波拉尼奥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写出了小说中不少震撼人的段落,可能窗外正在军事政变,但屋内的人只是保持静止而已,以这样的方式收尾,就好像波拉尼奥用一把尖刀直插历史的深处一样。我们也在他的写作中读到一些令我们愉悦之处,但是这个愉悦后来想起时,有点伤感。
波拉尼奥用这个小说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相信叙述者的话。其实他没有说的那些东西,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
孔亚雷:有没有人跟哈维尔先生不一样?我现在有个想法,想读波拉尼奥的一些句子,波拉尼奥是很少用比喻的,但他一旦用起来,那个比喻就雷霆万钧,非常厉害。
一个是他描述一次派对,他说那个女伯爵带着他穿过好多间大厅,他们就像是绽放的神秘玫瑰一般,第一朵向第二朵绽开花瓣,而后者又向下一朵绽开,然后一直到时间的尽头。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描写。刚才我跟哈维尔也在聊,就是电影对波拉尼奥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大卫·林奇,对波拉尼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里面那种莫名的悬疑感,大卫·林奇通过音乐和画面表现,我觉得波拉尼奥更牛,他用简单的文字就可以塑造出大卫·林奇要用那么多手段才能堆叠出的悬疑感。
然后我又想说,波拉尼奥的很多小说,真的像玫瑰一样,一瓣接着一瓣,一直到时间的尽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其实波拉尼奥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是他是很酷的浪漫,不是那种很纯情的浪漫,有点像北京痞子这种浪漫,很迷人。“玫瑰”也是一个很好的意象,记得《2666》里的一个片段,我一直就记得一个片断,主人公和他的爱人住在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爱人半夜突然消失了,他半夜起来找他的爱人,半夜的雪光照亮天空的星光,终于找到了。他问他的爱人,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那个爱人已经有点半疯了,就说,你看看天上的星光。他们突然意识到星光就是来自过去的光,它是几万年前的光。这其实也是一个暗喻,波拉尼奥的文学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在读来自过去的光。
所以我觉得波拉尼奥是一个很浪漫的诗人,但是他的浪漫又很特别,这从下一个句子就可以发现,这句子非常酷,“这样不好,喜欢是好事儿,被感动是不好的”。大家记住,他是很浪漫,但他不是那种很滥情的,很天真烂漫的那种。“被感动是不好的”,这可以作为波拉尼奥那种很冷酷的、带有一种嬉皮风格、狂野的写作风格最好的概括,他拒绝被感动。我觉得这个话很酷。
还有一句很奇妙。说到政治,这又是波拉尼奥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很政治的作家,当时回到智利,差一点就死在智利,他的小说里一直对政治有很深的讨论。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总结波拉尼奥的政治观,“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将重新分享权力,右派、中间派、左派都是出自一家,道德上的问题有一些,美学上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波拉尼奥的政治观,什么左派、右派、中间派,都是一派,美学上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这是典型的波拉尼奥的反讽。
最后一点我想读的就是刚才我说到他说到,一个女人在开文学沙龙,地下室在折磨革命家,这个女人被揭穿了之后,他们有一段对话,这个女人说,“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不仅仅是在智利,还包括在阿根廷、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乌拉圭、西班牙、法国跟德国,绿色的英国,以及热情奔放的意大利,文学就是如此的创作,至少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丢入垃圾堆里,我们才称其为文学”。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特,其实呼应了刚才范晔讲的,文学本身也带着某种恶,似乎这也是波拉尼奥非常重要的核心。充满了讽刺,但我们就是这样创作文学,我们也可以将“在中国”也加进去。
但是我又想表达一个观点,我想跟范晔说,文学中必须有恶,因为我觉得所有活着的东西,它都有恶。经常有一个对信仰的质问:既然你说有上帝,有万能的善,那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恶?这个问题好像很致命,但其实不堪一击,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回答,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就有恶,因为一旦你拥有自由意志,就意味着你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做恶事,就好像一个活人,必然会生病的,只有死人不会生病。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文学里必然存在恶,因为文学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东西,尤其是好的文学。所以我觉得这是波拉尼奥特别重要的一点,当然他没有给具体的答案,因为好的小说都是不给答案的,但是他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运用自由意志,去抵抗这个恶。



四
哈维尔:感谢这个活动,让我发现跟我一样读文学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大家的想法是共通的。我发现大家提的问题其实都很相似。其实好多研究波拉尼奥的那些人,就成为了《2666》中,评论阿琴波尔迪的那些人。
波拉尼奥作品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探讨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文学的作用。文学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学习的人,一直追求的人,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看到《智利之夜》和《遥远的星辰》中,有一些角色其实是共通的,谈到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2666》中那些艺术家,那些读书的人,那些残害女性的人,其实残害女性在《2666》中是恶的化身。
我们看波拉尼奥自己的经历,就可以想到,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所有倾注于文学,会发生什么?他15岁辍学,在当时的智利是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我相信在中国也不太可能。一个作家,能投身于文学之中,去找到一些真理,这就是我们喜爱波拉尼奥的原因吧。
范晔:我补充一点,刚才哈维尔读了几段西班牙语,他读的是《智利之夜》里面的,主人公给皮诺切特教马克思主义,顺便他们也聊天,当然聊天的时候,他还是诚惶诚恐的。哈维尔刚才念的,是皮诺切特说的话,他说阿连德不阅读,也不写作,你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烈士,但是你很难说他还是个知识分子,所以皮诺切特说“他不是一代知识分子,除非存在既不阅读,也不学习的知识分子”。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没毛病,还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么一个定义呢,也完全适用于法西斯式的,纳粹式的,比如《遥远的星辰》里面那位诗人,他其实也阅读,也写作,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恶的象征,因为他杀女人。波拉尼奥的书里面,只要杀女人,就是罪恶的,杀人不是恶,但是如果杀女人就绝对是恶的,不管是《遥远的星辰》里面,还是《2666》里面,杀的全都是姑娘,所以他就说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帮他补充一下。
孔亚雷:我有个观点,觉得伟大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一个作家认为男人比女人优秀很多,我对这个作家就表示怀疑。显然波拉尼奥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如果这个世界由女人来统治,回到母系氏族,它肯定会好很多,各种问题都会少很多,就像波拉尼奥说的,“杀人可能没问题,但如果杀女人,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接下来是不是留一点时间给下面的观众。因为有时候你问一个问题,会激起更多的回复。我们在这儿讲,会陷入对波拉尼奥的崇拜和迷恋之中不可自拔。
五
提问:三位老师好,刚才三位老师也提到,波拉尼奥展示世界的恶,以及文学的恶,他提出了文学上的解决之道,我们可以使用幽默,可以使用反讽,可以去理解这种恶。那你们认为波拉尼奥在作品里有没有暗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去解决现实的恶?就像刚才孔老师提出的,他认为左派、右派以及中间派,他们都是一伙的,那么有没有一种他认为的,良善的、可行的政治,在波拉尼奥看来,是可以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的?谢谢。
范晔:我先说两句,一会儿哈维尔说。
波拉尼奥不是政治家,他也不能给出什么一揽子方案,但是如果你硬要找出希望之光的话,就在他的孩子身上。波拉尼奥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信心,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比如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我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然后呢,在现实生活中,他有时候也会表现出这一点。比如他有一个墨西哥的朋友,他们俩老打电话,波拉尼奥特别喜欢半夜给人打电话,而且你必须得接,你不接,他就不高兴。有一次他打电话,这个墨西哥朋友没有及时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很小,他要照顾。波拉尼奥过两天又给他打过去了,说怎么回事?我这么着急的事找你,你怎么不接电话?也不给我打过来?其实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墨西哥迷恋的一个影星去世了,就这么一个事儿,波拉尼奥觉得特别重要,赶紧要告诉他。这个墨西哥的朋友跟他解释说我在照顾我女儿。波拉尼奥说,对,太对了,你做得太对了,你一定要记住,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你照顾你女儿,这件事是天下头一号的最重要的事儿。他对孩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信念。
还有一次,他一个朋友说,我写了一个小说,你帮我看看,他就说,你这小说里有没有孩子死的,有孩子死的,我可不看。就是这种,当时《2666》没写,大家后来就吐槽,你的《2666》死了多少孩子。他的诗集里有几首诗,不算什么好诗,但是我很感动,就是他写给他儿子的诗,有点像遗嘱一样,大概意思就是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我的书,也把我的书托付给我的儿子。他发明的词叫“互相保护”,他说这就像一个黑帮的口号一样,我的儿子要保护我的书,我的书将来也要保护我的儿子。所以他对孩子,是寄予一种未来的开放的可能性。他看到人生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战斗,写作和文学都是必然失败的,因为你的对手跟你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你还是要做。你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我们硬要找这个希望的话,我的感觉是,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也可以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就是孩子身上,或者说孩子所代表的未来的开放性上。

哈维尔:刚才范晔老师提到的诗非常好,波拉尼奥写作中有一些幽默之处,但是其实真正的幽默是不那么好笑的。波拉尼奥的幽默并不是那种让你笑到流泪或者捧腹大笑那种幽默,是有点伤感的幽默,但是这种幽默让你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你是谁,就像中世纪有一些幽默诗人,他们是唯一能用幽默来向君主阐释真理的人,《2666》中,不管诗句多糟,都有一个警察在用蹩脚的笑话讲这些非常烂的笑话,烂梗,其实它们并不好笑,但它们让你从另一个方式接触到了一些真实。
提问:像波拉尼奥这样一个能量巨大的作者,包括他年轻的时候搞革命,他的作品里面呈现的恶,是否就来自他的经验深处,是否他自身经验里,就携带了这个恶,所以他才反映在自己的文本里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恶的深层问题。
孔亚雷:我觉得波拉尼奥不是你说的那样,你所说的恶,我们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是一个活人,你不是一个死人,你身上就会有恶。就像文学,如果它生动,如果它打动人,它有生命力,它也必然带着恶。这个恶我觉得是天生的。
当然你说的有一点很好,就是波拉尼奥的经历,当然这个有争论,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文体的需要,就是40岁之前,他革命过,吸毒、生病,各种事情,写诗,但他40岁之后,什么也没做,他就是需要收入,短短的十年时间,他写了无数的,非常惊人数量的作品,所以你说的能量巨大,确实,在写作上他确实富有极大的能量,我感觉他真是用生命在写作。很显然,他就是死在《2666》上,他如果不写《2666》,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快死,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写。
而且由此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只有非常善良的人,和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用生命去写作,真的是这样,村上春树也写过一句话,他说“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去写作的,这个事情太不划算了,这个回报太微妙了,”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所有大作家都是天真的人,成名完全是一种意外,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全身心去写自己的作品。我一直在讲,我为什么不相信那个网络小说,一天写一万字的人,因为很简单,因为你以一个血肉之躯,你要写一个能够存活万年的小说,你不付出你的灵魂,怎么可能呢?你把它当成生意来做,这么玩玩,怎么可能?现在很多人还在用文学,我很聪明,我写一篇小说,卖个十几万的版权,电视,那个根本就不是文学,很快就被时间抛弃。
范晔:我感觉你提问里的“恶”,指的是个人品德上的过失或什么,但波拉尼奥那种恶是更大的东西,像一个巨大的怪兽,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你摆脱不了的东西。不管是《遥远的星辰》也好,还是《智利之夜》也好,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吞噬了一代人的梦想的,一个怪兽一般的阴影,而不是说个人生活的挫折什么的。
我觉得还要了解波拉尼奥的一点,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代拥有神话的拉丁美洲人。他是经历过古巴革命,曾经有过更宏大的理想,比如说他们对阿连德政府,这样一个民选政府的理想的寄托,他们愿意为这样一个民选政府来抛洒青春热血,它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你看他在墨西哥过一种好象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但这不是一种自我感觉的东西,它跟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或者像亚雷说的,他从来不是说让文学来换取些什么,在波拉尼奥这里,文学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他追寻的目的所在。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老用一个比喻,就是我的写作是把我的生命都摆在桌上,把一切都押上,我知道肯定要输的,但我还是要把一切都押上。
你看他很多时候都在写他的一代,不能说为一代人代言吧,但是他很有意识的,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群体,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人。我随便举个例子,你读一下《护身符》的最后,他说无数的拉丁美洲青年,唱着歌走向深渊,他说这歌声就是他们的护身符。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与恶的一种必败的抗争,但它是一个更大尺度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小我的感伤性的,或者说今天被资本消费的这种“诗和远方”。他所面临的困境,黑暗的压力,也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个人生活的挫折,或者是一时的成功,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未必合适。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知道这个书原来的书名叫《屎风暴》,刚才翻了一下,发现它其实是这本书最后一句话,翻译成“一场可恶的头脑风暴就爆发了”,完全没有体现出“屎”的字眼,想问一下出版商是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因为如果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可能这个书的销量会翻倍。
范晔:他原来是起这名字,但是他的朋友,包括出版人,都劝他,说换一个名字,他后来选的这个,其实应该是《智利夜曲》,但具体有什么细节,我们可以听哈维尔说一下。
哈维尔:关于《屎风暴》有一个很著名的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一个轶闻,说波拉尼奥非常想把这个书取名为《屎风暴》,你都能想象波拉尼奥躺在床上跟他的情人谈论这个书名的绝妙之处的时候,他的西班牙出版人劝他,说你怎样写都行,就是不要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最后就放弃了,这个事情在出版圈流传了很久。
范晔: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瞎猜的,没有什么根据,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对《百年孤独》的戏仿,因为《百年孤独》也有一个“暴风”,是“抹去一切的暴风”。而且波拉尼奥对这种屎、粪便很感兴趣,他的《2666》里面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人,最后巨人就像屎做的雕塑一样,塌了。他很喜欢这种。
他也说马尔克斯著名的短篇《上校无人来信》的最后一个词,你看中文里还有两个字,西班牙文里就一个词,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要联想到前面跟那鸽子还是有关系,他为什么要杀鸽子?因为那个鸽子的屎会污染这些建筑,所以你想,等于是某种程度上,他在暗示所有的前面做的那些用猎鹰捕鸽子的事情注定是徒劳的,最后一个屎的风暴要卷起来,不是一只鸽子,两只鸽子的问题,是有一个风暴要卷起来,一切都会归于这个屎的风暴。
主持:刚才有一位读者提到名字,翻译成《智利夜曲》很准确,但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叫《智利之夜》也可以,所以我们跟译者商量,还是《智利之夜》。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精彩的发言,也感谢各位读者,作为出版社,波拉尼奥的书我们继续在出,希望每年都有一个机会跟大家相聚,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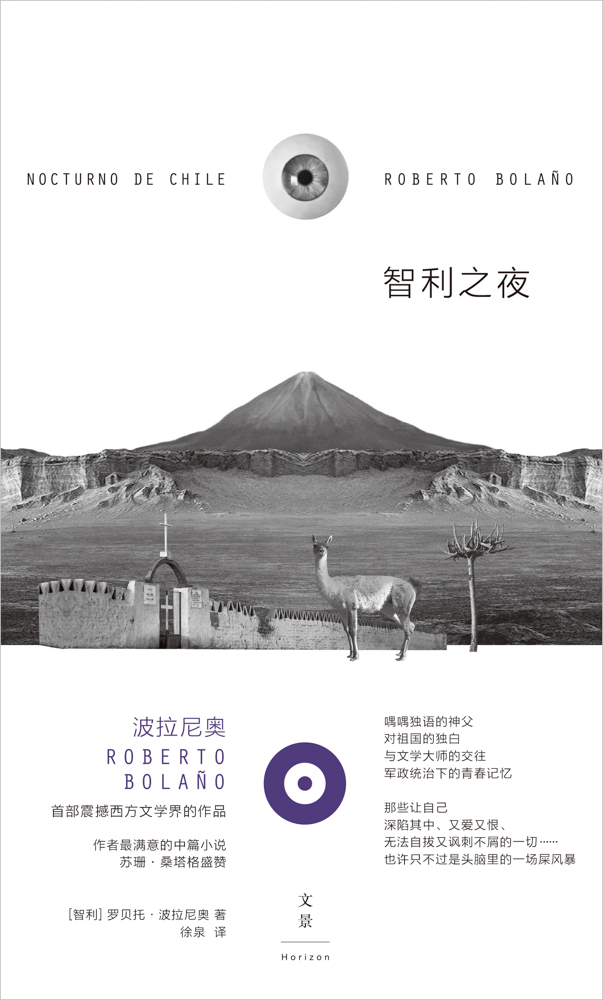
—— 完——
题图为波拉尼奥,由出版社提供。文中现场图片由摄影师橙子拍摄。
范晔,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译有《致未来的诗人》《百年孤独》《万火归一》等西语文学作品数种,最新译作为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另有随笔集《诗人的迟缓》。
哈维尔·费尔南德斯(Javier Fernández),西班牙使馆教育参赞,波拉尼奥的研究者与粉丝,博士论文主题为波拉尼奥作品中美国叙事风格的影响。今年企鹅兰登推出了漫画版《遥远的星辰》,由哈维尔与画家范妮·马林(Fanny Marín)共同创作。
孔亚雷,小说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等,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莱昂纳德·科恩诗文集《渴望之书》,杰夫·戴尔《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等。2013年获第四届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提名奖。他住在莫干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