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翻译|蔡希苑 吴厚平
现在离我放弃以“超自然传奇”之主题讨论好坏社会的内容的博士论文已近四十年,我发现自己竟然也创作了三部乌托邦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
可我当年究竟为何会做这样一件可谓“离经叛道”之事——弃现实主义小说不顾,而拥反乌托邦入怀呢?是我甘于自贬身价么?要知道时至今日,一些“文学”作家还因为创作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而遭受非议呢。人心难解,但我还是权且回忆一下当年我自以为义不容辞的事情吧。
首先,谈谈《使女的故事》。是什么让我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呢?于此之前我创作的小说全都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乌托邦小说是一种冒险,但也是一种挑战和诱惑。因为一旦仔细研究并大量阅读了某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在不知不觉间产生跃跃欲试、模仿创作的想法。
经过前期试笔,1984 年春,在柏林,我开始正式写这本书。期间,通过一个由西柏林管理的旨在鼓励外国艺术家访问的项目,我获得了一个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研究员职位。当时这座城市正处于柏林墙的包围之中,因此可以理解,西柏林居民都有一种幽闭恐惧心理。那段时间里,我们访问了东柏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获得了在极权主义政权下生活的第一手生活体验资料,虽说这极权主义本该是乌托邦。回到多伦多之后,我写成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1985 年春,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市,该书结稿。期间我还在当地被聘为艺术硕士的教授。塔斯卡卢萨和亚拉巴马让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生活气息——民主,又有许多社会习俗和观念的限制。(“不要骑自行车。”我被告知,“人们会觉得你是共产主义者,把你挤下马路。”)
创作《使女的故事》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受,好似在河冰上滑行——摇摇晃晃却欣喜兴奋。这块冰多薄? 我能行多远? 我会遇到多少困难? 如果我掉进河里,水里等着我的是什么? 这些都与作家有关,与文章结构、写作手法有关。
而其中最大的,有关每一个完成的章节的,每一位作家都会自问的问题是:有人会相信它吗?(我指的不是表面意义上的相信,小说就是虚构的。从扉页开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所指的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文字叙述真实可信,让读者心甘情愿地跟着情节热闹。)
这些作家的问题是其他更普遍的问题的反应。“已经解放了的”现代西方女性脚下的冰到底有多厚呢?她们能走多远?会遭遇多少麻烦?一旦跌倒等待她们的是什么?或者更进一步。假设你打算让极权主义者统治美国,你会怎么做?要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挂什么样的旗?在民众宣布放弃他们千辛万苦争来的公民自由,交换“安全”之前应该让这个政府解决多少社会不安定问题?并且,既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极权主义政府一直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控制生育——不是限制生育就是强制生育,再不然就详加规定谁可以和谁结婚,谁可以有孩子——这样的主题该怎样为女性演绎?
服装又当如何呢?正反乌托邦对衣服一直都很感兴趣:要么让它变得比我们现在穿得少(维多利亚时期的风尚),要么让它比我们现在穿得多。对服装的关注通常也以女性为中心: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异,服装的变换全然不过是用衣服把女人身体的某些部位遮了露,露了遮。(也许只为使事情有趣些,让你一会儿看见暴露处,一会儿又看不见,即便这部位本身是变来变去的。那么,过去纤细的脚踝如此诱人,那性感的部位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
我创作《使女的故事》的原则十分简单:不写有史以来人类从未曾做的事,也不写人类在某时、某地不可能找到工具去完成的事。要知道甚至集体绞刑也是有例可循的:早年英格兰就有集体绞刑,而现在某些国家还有集体被石头砸死的刑罚。如果回溯历史,据说迈那得斯们(酒神巴克斯的女信众)在酒神节上会变得疯狂,并在癫狂中徒手将人肢解(倘若人人参与,则人人无责)。至于文学上的先例,眼前就有一个,左拉的《萌芽》便是。其中有一段情节描写了镇上被店主蹂躏的采煤女工们,将店主生生扯碎,并将其生殖器挂在长竿上穿镇游行。另一个略加节制润色但依旧骇人的先例出自雪莉· 杰克逊的一篇短小精悍的故事《摸彩》。(我十几岁时就读过这个故事了,那时它才问世不久,读得我不寒而栗。)
至于《使女的故事》中女子所穿的罩袍,人们的理解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天主教的服饰(修女的衣服的样子),也有人认为是穆斯林的服饰(蒙住全身的长袍)。事实上,这些衣服在设计时,根本不针对任何宗教,它们的灵感来自我儿时看到的水槽清洁剂的包装盒上荷兰老清洁工的形象,样式老旧而已。若是让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女子来看,绝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不寻常,因为那时女人都要戴女帽,遮面纱,盖住容颜以遮挡陌生男子偷窥的目光。
我为这本小说写序时引了三段话。第一段引文来自《圣经》的《创世记》(30,1–3)。雅各布的两位妻子各自利用女奴,让其成为替自己生孩子的工具。引用这一段本是为了要读者在引用各自相去甚远的文字记载时警惕每一个词固有的危险。第二段引文来自乔纳森· 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它让我们警觉一个事实:一本正经又极尽挖苦的述说,比如斯威夫特建议可通过销售并享用爱尔兰婴儿肉的方式消灭爱尔兰的贫穷,是不能当作济世良方的。第三段,“在沙漠中不会有这样的标识:不许吃石头。”乃是斯威夫特的格言,它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人类真相:我们从不禁止别人本来就不打算做的事,因为所有的禁令都建立在对欲望的否定之上。
《使女的故事》1985 年秋在加拿大出版,1986 年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在英国,第一批读者只把它当作奇闻漫谈而不是警示,他们早就经历了奥利弗· 克伦威尔治下的清教徒共和国,不惧怕那种场景再次上演。在加拿大,人们都以加拿大人特有的焦虑的方式追问:“会发生在加拿大吗?”而在美国,玛丽· 麦卡锡在《纽约时报》撰文对此书痛加贬斥,认为它不但缺乏想象力,而且它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她心目中的像现实的美国这般安全的社会里。
然而,在西海岸,这个对地震的震颤最敏感,脱口秀上交换台灿烂如拉斯维加斯的耀眼灯火的地方,有人在威尼斯海岸的防波堤上留下潦草的字迹:“使女的故事已经在这里发生了!”
其实,既非已经在这里发生,非刚好就在这里发生,也不会马上在这里发生。九十年代时,我一度以为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如今我又疑惑了。近年来,美国社会朝着建设一个取代原有机构、反民主的、高压的政府的必要条件迈进了许多。《使女的故事》出版后约五年,苏联解体,西方民众弹冠相庆,涌上街头,疯狂购物。各路权威专家纷纷宣告历史的终结。看起来,《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之间的竞争,即“用恐吓手段控制”与“用条件制约和消费的方式控制”间的竞争,以后者完胜而告终。《使女的故事》所描写的世界也理所当然地退去了。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美国因两次泥潭深陷的战争与经济衰退变得脆弱,似乎正在失去对自由民主的基本前提的信心。“9 · 11”之后,爱国者法案连咳嗽都未闻一声就通过了,而在英国,公众居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从前无法想象的政府监督。
不言而喻,敌对的政府会在组织及方法中映照出彼此。当克隆成为大势,每个人都想要一个。美国的原子弹激起苏联同样的欲望。那个时候,苏联是一个庞大、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政府,而美国其实也别无二致。既然现有组织形式遭到铁石心肠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拼命反抗,美国又将采用什么政权组织形式呢?它会以同样的宗教狂热制定规则吗?二者差异是否只会是教派的不同?在它的胜利中是否会有更多的镇压要素?会不会回到它的源头形式——清教徒神权政体,在除了服装之外的一切事情中,给我们一个现实的《使女的故事》?
我已说过反乌托邦中总含有一丁点儿乌托邦,反之亦然。那么在反乌托邦《使女的故事》中那一丁点儿的乌托邦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在过去中——这过去正是我们的现在;另一个则出现在未来,写在书末故事主体之外的编后记中:它描写了基列国(《使女的故事》中的专制共和国)最终消亡的未来,人们只能在学术会议和学术研究的主题中找到基列国。窃以为,这正是乌托邦死亡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它们去不了天堂,而是成为论文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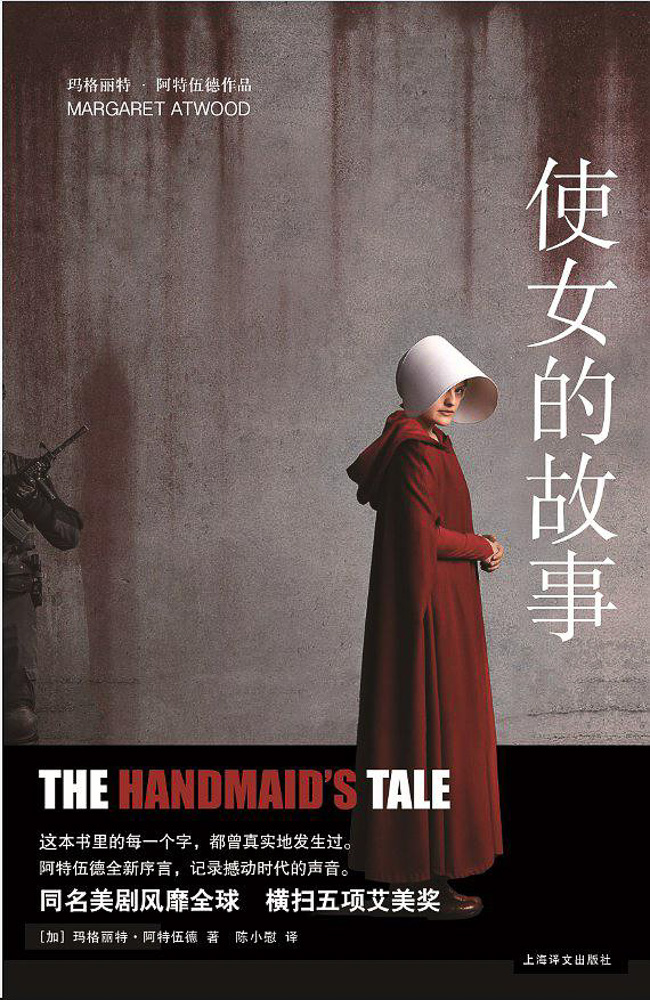


* * *
《使女的故事》写成之后大约十八年间,我一直没有进行正反乌托邦的小说创作。直到2003 年,才写了一部《羚羊与秧鸡》。《羚羊与秧鸡》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人类几乎灭绝,而在这之前,人类分作两个阵营——技术专家论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一如既往,书中也有一丁点儿乌托邦的意图,那是一群用基因工程改造过的人——这改造能让他们永远不会染上全部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疾病。他们是设计师。然而,每一位参与了这一设计的人——我们现在正做着设计这件事——都不得不问:在这些改造版的人无法继续被当作人类对待之前,人类在改造这一领域究竟还能行多远?人类所有的属性中核心部分有哪些?人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如今,既然我们自己成了工匠,我们又该大刀阔斧地砍去这一作品的哪些部分?
这些设计师都有些附属物件和能力,若能拥有这些,我自己倒蛮乐意的。比如内植式昆虫杀虫剂,自动防晒霜,像兔子一样的树叶消化能力。此外,他们还拥有一些算得上是进步的特性,尽管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会喜欢它们。比方说:季节性交配。也就是在交配季,身体的某些部位像狒狒在发情季身体的某个部位会变色一样。从此不再有示爱遭拒和约会强奸。再比方,他们不会阅读,因此也绝对不会被有害的思想荼毒。
书中还有其他经过基因改造的生物。比如:诺伯斯鸡(Chickie Nobs),也即一群被整改过的鸡,全身可以长出许多腿、翅膀和鸡胸,但是不长鸡头。只身子顶端有一个营养饲入口——彻底解决了动物权益工作者的麻烦。如他们的创作者所言,“无脑则无痛”。(自《羚羊与秧鸡》出版之后,诺伯斯鸡的解决方案更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实验室人造肉已成为现实,尽管它可能还未被灌进香肠。)
它的姊妹篇《洪水之年》2009 年出版,最初的书名是“上帝的园丁”。英国出版商欣然接受这标题,而美国与加拿大的出版商却十分抵触,理由是读者会以为这是一本极右主义的宣传册,意在展示一直以来“上帝”一词是如何被彻头彻尾地劫持的。当时还有其他许多书名以供选择,包括“蛇的智慧”,虽受加拿大出版商的喜爱但是美国出版商却认为听着像嬉皮士的“新世纪”(New Age)邪典。而“艾登绝壁”(Edencliff)这名字在英国人听来像伯恩茅斯的老人院。
总有些书,名字一目了然,比如,《可以吃的女人》,但也有些很难确定,《洪水之年》便属后者。
《洪水之年》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羚羊与秧鸡》中的世界。鉴于吉米/ 雪人,《羚羊与秧鸡》的主角,成长在一个隔绝的特许飞地。《洪水之年》则发生在这块飞地之外,在社会的最底层。它的前灾难情节在社区展开——社区保安队——如今与社会自治机构融合了——甚至懒得巡逻,将整个社区留给犯罪团伙与无法无天的暴力分子的地方。即便如此,这样的反乌托邦中甚至也蕴含了一点乌托邦——“上帝的园丁”,一个小型的环保主义教派,相信所有造物者有其神圣性。社区居民在贫民窟的屋顶上种菜,唱圣歌赞美神圣的自然,对一切高科技通信设备都敬而远之,比如手机、电脑,因为它们可被用来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一点倒是真的)。
《洪水之年》与《羚羊与秧鸡》写于同一时间,无所谓续集前传,更像是出自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甚至有时候,也被人们描述成“启示录”。在真正的“启示录”中,地球上的一切都覆灭了。而这两本书中,灭绝的只有一样——人类,或者说绝大部分人都灭绝了。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不是“反乌托邦”,因为反乌托邦需要更多的人——人多了才能组成一个社会。这些如飘零叶的“漏网之人”,也有神话学的先祖:许多神话都描述了仅余一人幸存下来的灭世大洪水(希腊神话中有丢卡利翁,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乌塔那兹匹姆),当然也有好几个人活下来的,比如诺亚和他的家人。那么在《羚羊和秧鸡》和《洪水之年》中仅存下的那几个人是否对那一小部分接受了基因改造的、内心平和、两性和谐、并且本来是要取代他们的“新人类”造成了“反乌托邦”的威胁呢?事实上,无论什么书,不是作者而是读者才享有对它最后的发言权,因此,这一问题就留给读者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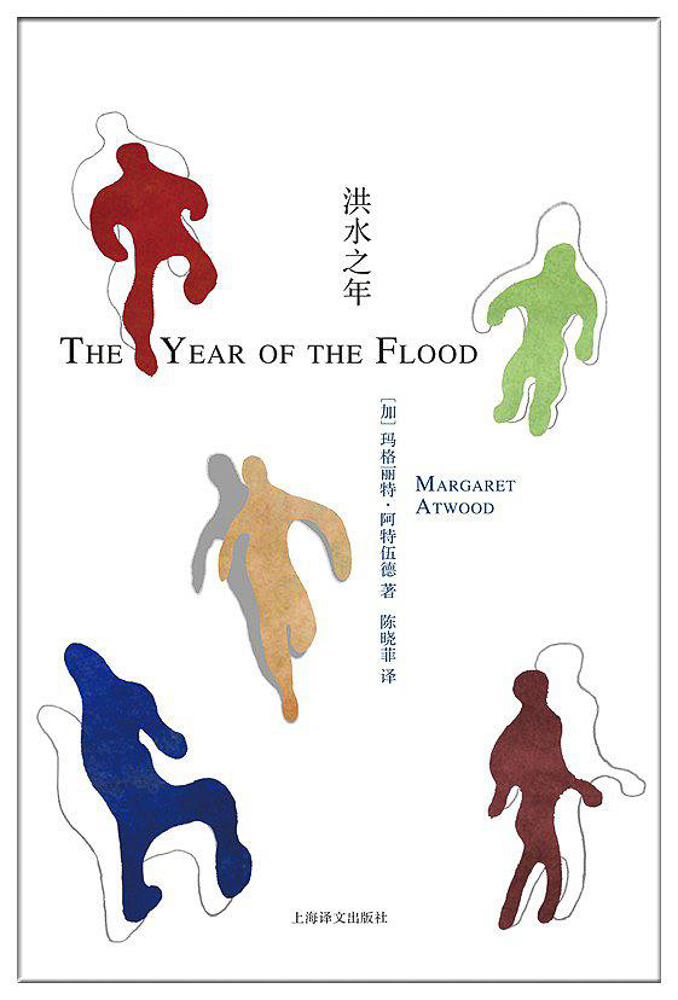
* * *
人们不止一次问我,创作这两部书以及书中世界的“灵感”从何而来。可以肯定,小说虽不同,但理由总相似——家族故事、剪报和个人经历。于《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也一样。我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后果的担忧可追溯至1972年,当时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已准确地预测了今时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2001 年春我开始创作《羚羊与秧鸡》时,没有将这些担忧写作篇首故事,但它们却一直萦绕心头。创作《使女的故事》的同时,我积累了满满几文件夹的研究资料。诚然,两本书都存在一些哈克贝利· 费恩会说成是“夸大其词”的内容,却也不是彻底的无稽之谈。
因此,尽管我可以说创作灵感源自这篇或那篇科学论文、报纸或杂志故事,这件或那件真事,但它们全不是我讲故事的动力。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未竟的事业、由不停自省的人提出的问题——我们究竟把这个星球搞得多糟糕?我们能让自己从糟糕的星球中脱身吗?若在现实中进行物种范围的自我拯救会是什么样?甚至还有“乌托邦思想都去哪儿了?”它从未消失过,因为人类是一个对此太过神往的物种。对人类来说,“好”有个永远的双胞胎兄弟“坏”,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孪生兄弟,它的名字叫“更好”。
让我自觉有趣的是将《羚羊与秧鸡》中乌托邦的促进因素置于人的身体之内,而不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大众洗脑或灵魂工程项目。秧鸡们由内而外地行止端庄,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体系的规定、政府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恐吓,而是因为他们从来就被设计成这样。他们没有选择反面的可能。这似乎也正是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的终极目标:通过基因工程,我们可以剔除自身的遗传性疾病,让丑陋的外形、精神的疾患从此遁迹,长生不老,诸如此类,谁知道呢?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或者说这是我们一直被灌输的理念。然而,在各种完美无瑕的乌托邦版完美人体和大脑中掩藏的那一点点反乌托邦又是什么呢?就让时间来揭晓答案吧。
纵观古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未有过快乐的故事。美好的企盼总是一次次被击得粉碎。最好的意愿常常踏上通往地狱的道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要尝试修正自己的错误,矫正被灾难扭曲的事业,清除掉道德败坏的恶臭,减轻生活中的种种苦痛呢?当然不是。假如我们不维护修理,对实际状况做一点提升,所有的事情都会迅速地一落千丈。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改善,并且这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让事情都尽善尽美,尤其不可妄求人类自身的完美,因为这条道只通向巨大的坟墓。
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缺憾,也无法摆脱这样的自我,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样的自我。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在准备通往正反乌托邦的道路上所必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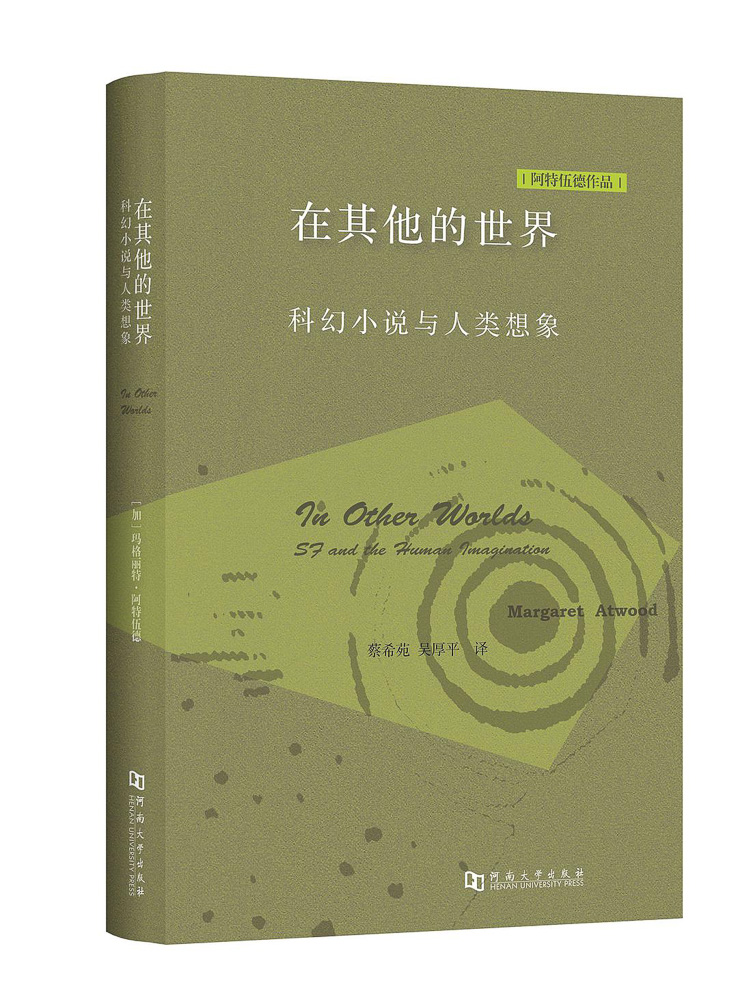
—— 完——
题图:《使女的故事》同名美剧剧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 Atwood,1939—)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早年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度过,1962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迄今已在全球35个国家出版。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她的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雷米欧.蒙德罗奖;《盲刺客》曾获2000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