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要说服巴黎并不容易,但这是一个大胆而明智的决定,”11月28日,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Olaf Scholz)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演讲,呼吁法国让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以欧盟席位取而代之。
“欧盟应以一个共同的声音出现在安理会上,作为回报,欧盟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应当由法国人永远担任。”他说。
几天前的11月25日,欧盟27国刚刚一致通过英国“脱欧”协议草案。一旦英国脱离欧盟,法国将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仅剩的一个欧盟国家。
自然,肖尔茨的提议被法国人断然拒绝。法国驻美大使阿罗德(Gérard Araud)次日即在推特上表示:“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尽管肖尔茨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德国官方立场,其演讲也仅仅是“柏林未来基金会”组织的系列演讲之一,但德国人一直热衷于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德国统一后的入常执念

今年6月8日,德国以184票赞成、4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当选2019/202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也将是德国第七次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不过,德国人对此显然并不满足(编者注:联合国安理会中10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两年,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不能连选连任)。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解散,解体后的五个联邦州分别公投并宣布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后签订的《二加四条约》不仅标志着德国终于获得了完全主权,也宣告了德国谋划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开始。
就在两德统一之后仅仅五个月,时任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就提出了欧洲共同席位的想法,但是由于当时欧盟都未正式建立,勃兰特的想法更多被外界认为是一种理念而非政治主张。但德国人却开始将这个理念付诸行动,一年后,时任外长金克尔(Klaus Kinkel)于1992年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表示了德国希望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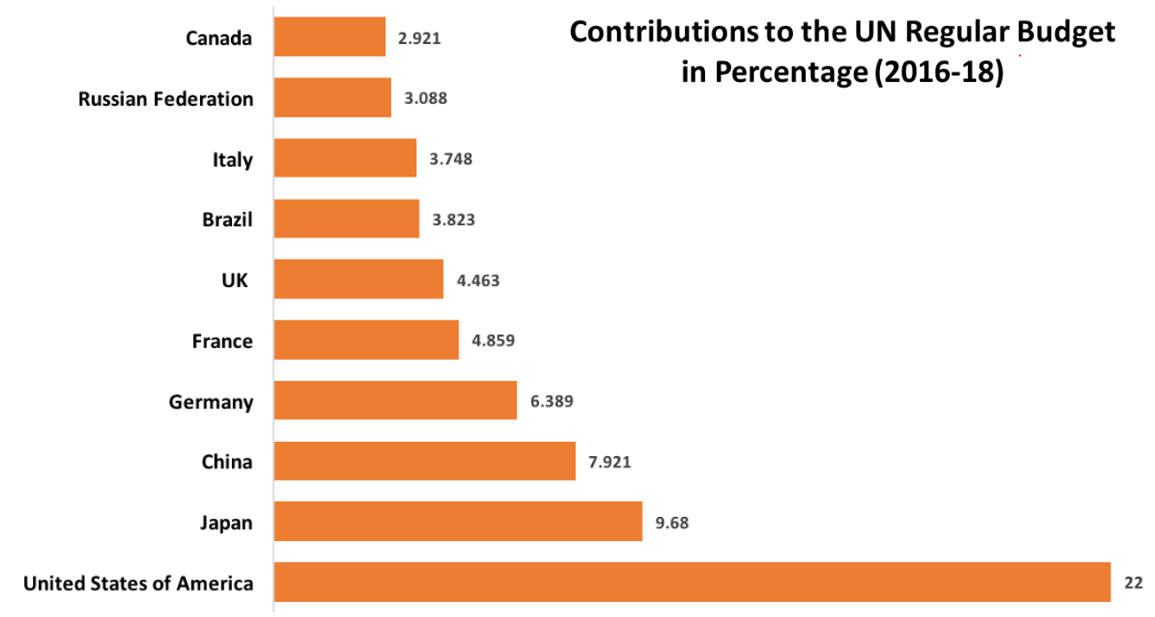
经过四年的准备后,借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由头,德国团结其他区域大国于1997年正式提出了“拉扎利计划”(Razali Plan),建议安理会新增五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由于美国和意大利的坚决反对,该提案最终甚至都未付诸表决,但“拉扎利计划”却构成了其后20年间几乎所有安理会改革方案的参照模板。
2003年,美国和英国绕过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彰显出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得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为了更迅速有力地推动联合国改革,德国与日本、印度、巴西组成了“四国集团”,决意以“捆绑、共进退”的方式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
四处碰壁与联合国改革
2005年3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终提出了数套改革方案,内容大体上都是“拉扎利计划”的变种版本。但和“拉扎利计划”一样,由于非洲国家联盟坚持新增常任理事国必须拥有否决权,以及“咖啡俱乐部”(UFC,又称“团结谋共识”运动)成员国的坚决反对,改革方案同样没有付诸表决。自此之后,德国通过联合国改革以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计划几乎一直处于无限期搁置的状态。
“咖啡俱乐部”成员国的心态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最具有代表性。
在两德统一之前,意大利一直是联合国改革和要求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积极分子,其底气主要源于其在冷战时作为欧洲继英法后第三大国身份。两德统一之后,意大利国力被重新统一的德国拉开差距,由于担心在欧洲被彻底边缘化,意大利摇身一变成了联合国改革最大的反对者。西班牙则以庞大西语世界的代表自居,加之西班牙语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西班牙对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一直心向往之。四国集团倘若成功入常,联合国安理会继续改革的动力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大大减小,这对两国而言并非好消息。
除了来自咖啡俱乐部的阻力,即便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层面,德国入常的夙愿也不乏反对者。由于德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背叛”,美国自2003年起宣布只支持日本单独入常;而英法两国出于对德国入常后将带来自身地位下滑的担忧,一直以来对德国入常的问题也不甚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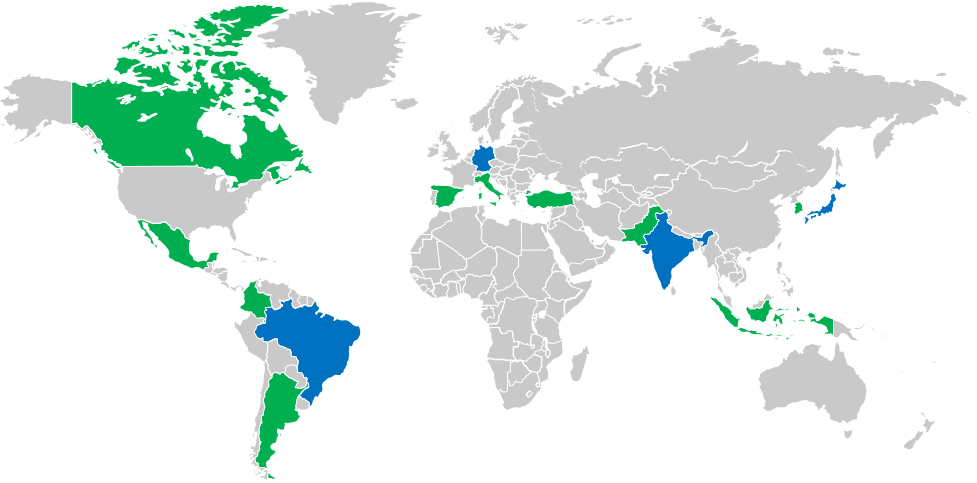
面对来自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咖啡俱乐部的压力,德国给出的方案依然是欧盟共同席位以及四国集团。
欧盟共同席位的提议代表了欧洲共同政治、经济、文化集合体的诉求,很快得到了欧盟机构的积极反馈,更是获得了意大利的鼎力支持。早在1990年,意大利外长就提议将英法的两个席位以欧洲各国轮流坐庄代替;2007年意大利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更是积极宣传欧盟共同席位的理念。德国自从近年来也公开赞同欧盟共同席位后,英法两国出于对丢失其独立席位的担忧,都不再反对德国入常。在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之后,法国受到的来自德意两国的压力必然会加大。此次肖尔茨的发言也更被视为德国对于法国的一种敲打,目的在于提醒法国对于支持德国入常的承诺,以及暗示法国在安理会上也应当反映德国和欧盟的政治诉求。
四国集团的提议尽管在推进集体入常上毫无建树,但是在扩大非常任理事国职权以及改革非常任理事国选举等问题上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自从非常任理事国确定依据地区选举产生以来,四国就成为了非常任理事国的常客。新千年来,德国和日本都已三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四国集团一次又一次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施加压力,也使得废除“非常任理事国不得连任”、延长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的提议摆上了议事日程。对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事实性垄断,是四国集团在可预计的未来可能达成的目标。
积极外交“欧洲担当”
在寻求入常问题上的四处碰壁,并不代表德国人的努力就此结束,毕竟安理会在当前各大冲突地区的作用微乎其微。在经历了欧债危机、中国的大国崛起以及特朗普上台之后,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德国外交政策也渐渐从矜持克制变为积极主动。
一句疑似来自多年前基辛格的讽刺依然回响在耳边:“要打电话给欧洲?打给谁?先给我欧洲的电话号码。”尽管基辛格后来说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但《纽约时报》已经给出过答案:打给柏林。持有同样观点还有俄罗斯的普京,俄乌在刻赤海峡再起冲突后,普京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拨往柏林,希望默克尔还能管住“不听话”的乌克兰人。这其中的缘由恐怕不仅仅在于默克尔的俄语说得流利。
“被打断了脊梁的日耳曼人”、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曾经是战后一代德国人的标签,德国人重拾民族自信的历史似乎和德国足球的成功巧合地吻合。1954年的伯尔尼奇迹让德国人第一次抬起头,并吹响了莱茵奇迹的序曲;被1990年激发的民族热情在几个月后击碎了东德高层仍意图保留两德并立的梦想。时间来到2014年,除了在南美大陆上羞辱了巴西足球队,这一年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拐点。
该年年初,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现已为德国总统)就在议会表示,德国要施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国际争端中发挥影响力。在之后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更是把德国曾奉行的外交克制视为道德上的懦夫行为。
不久之后,德国联邦议会就通过了首次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援助武器以抗击“伊斯兰国”(ISIS)的决议,这也是德国战后首次向战乱地区直接提供军事援助。
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更是成为德国新外交政策最好的试金石。德国选择迅速介入乌克兰局势,在美国要求给予乌克兰武器援助以及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德国选择了对自己、对欧洲最有利的解决方案。德国不仅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更是拒绝做出让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承诺,甚至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犹豫不决、瞻前顾后。
在排除了军事干预的选项后,默克尔迅速利用“魏玛三角”(即德国、法国、波兰三国合作机制)的平台,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和俄乌双方展开谈判以解决克里米亚问题。而在乌东地区爆发战事之后,德国又以波兰等东欧国家难以保持中立立场为由,抛下波兰,单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起向普京施压,并最终促成两次《明斯克协议》。

尽管《明斯克协议》被部分批评人士称为翻版的《慕尼黑协议》,并在很大程度上逼迫乌克兰接受了丢失克里米亚的客观事实,但该协议也的确避免了乌克兰内战的无限制升级以及可能出现的难民潮。此外,在签订该协议的过程中,德法两国成功地将华盛顿方面排除在外——毕竟,欧洲大国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带给欧洲的负面冲击,远远甚于美国。
纵横捭阖的“第六常”
除了在乌克兰问题上积极的外交斡旋,近年来,几乎在所有热点或冲突地区都能看到德国人的身影。在叙利亚问题上,德国出于控制难民的考量,一直以来都明确拒绝加入美英法的空袭部队;在处理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问题上,德国又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动欧盟接纳超过100万难民。
而在伊朗核问题方面,借助P5+1集团(即联合国五常加德国),德国俨然扮演了“第六常”的角色;在特朗普宣布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之后,德法两国依然立挺伊朗,除了在今年8月以欧盟名义向伊朗提供1800万欧元援助以及新建SPV支付系统以绕过美国SWIFT之外,德国人还允许伊朗在法兰克福设立欧洲伊朗商业银行,并实际由德意志银行进行日常管理。今年7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制裁,德黑兰方面提取了欧洲伊朗商业银行帐户上的3.8亿欧元,柏林也最终顶住华盛顿的压力予以放行。
“中间路线的实用主义”是近年来德国外交政策的最好标签。相比于英国仍会象征性地派遣军舰至南中国海“护航”,德国对于亚太地区几乎从不发表意见。实用主义这一点还尤其体现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害案上。相比于特朗普和马克龙拒绝对沙特采取任何行动,柏林第一个站出来宣布对沙特进行武器禁售并占领舆论和道德制高点。但军火交易的搁置可能并不会影响两国商界的经贸往来,在缺席10月23日的沙特投资大会,并推迟签署据信200亿美元的订单后,11月26日,西门子集团CEO凯飒到访利雅得。
12月2日,G20峰会闭幕,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启程回国继续为促成脱欧协议斡旋;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需要收拾“黄马甲”的烂摊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为中美贸易谈判做准备;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到柏林后要处理的,则是来自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派兵请求。
不过,纵然德国在外交领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但国内反对派的声音以及孱弱的联邦国防军都是制约德国进一步有所作为的重要因素。即便摘掉了“政治侏儒”的帽子,德意志第四帝国也永远不会出现,只是,愈发自信的日耳曼人或许终将以新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本文作者钱伯彦、陈英为界面新闻德国特约撰稿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