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新闻对社会和民主至关重要。”马克·扎克伯格5月向一群编辑和媒体主管声称。《卫报》及其姐妹报纸《观察家报》3月时曾报道过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该分析机构与唐纳德·特朗普有染——对目标用户投放定制化政治广告一事。曝光内容令人毫不意外,无非是脸书对其平台的多方面监管失败。在国会就案情作证后,扎克伯格又在帕罗奥图(Palo Alto)召开新闻发布会,摆出一副坚信报道可以揭露幕后真相的样子。与此同时,他却对确保脸书能做到这一点的具体方法只字不提。
持续十年的动荡令羸弱的传统媒体难以抵御政治攻击,被迫作出道德妥协,且日渐被新形式的数字媒体超越。富有深度且多方求证的报道眼下要对付社交媒体上各种混淆视听的钓鱼、玩梗、机器人、喷子、党棍写手以及假新闻。鉴于脸书、谷歌和亚马逊逐渐称霸广告业——出版物的昔日靠山——地方新闻也日趋式微。媒体从业人员目前不仅要重新审视其业务路线,还须考虑是否要让新闻去适应一个它在其中几乎只能沦为配角的媒体世界。如何服务公共利益,是眼下最为紧迫的问题。
在新作《突发新闻:论新闻业的重建及其在当下之必要》(Breaking News: The Remaking of Journalism and Why it Matters Now)中,阿兰·拉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认为这不亚于一场自由民主的潜在危机。开放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可靠信息的易得性(access to trustworthy information),而互联网也承诺要继续推进其民主化。但如今的信息品质良莠不齐且源头多不可靠,令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随之而来的困惑几乎快要颠覆我们的世界观,且让兴风作浪者有机可乘。“在现代历史中,我们堪称首次,”拉斯布里奇写道,“面对缺乏可靠新闻的社会何以存续这一问题——至少就以往对此问题的理解而言。”
他对紧迫性心知肚明:拉斯布里奇曾担任《卫报》主编,与该报一同见证了它从一家英国普通报纸成长为全球进步新闻标杆的艰苦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其间的一切难关。拉斯布里奇领衔的《卫报》对把握新闻业在眼下世界中的机遇与局限不无启发。他准确预见了数字媒体对新声音的解放及其对以往支撑新闻采集的诸多商业模式的冲击。未见分晓的只是诸如《卫报》这类机构还能存活多久——及其公民使命与商业利益的冲突将会达到何种程度。
拉斯布里奇1976年从《剑桥晚间新闻》(Cambridge Evening News)起家,其职业生涯与整个媒体业界几乎同呼吸共命运。这家有40年历史的报纸在当地垄断了如今所称的“内容”分发之类的东西。职场、汽车以及其它一切如今能在“克雷格清单”(Craigslist,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1995年建立于美国加州,创始人为克雷格·纽马克——译注)上找到的项目,该报都一应俱全,且读者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它;广告商是媒体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这部赚钱机器中,记者与受众间的信息交换是垂直的,由记者下发。“我们有一批印刷机,”拉斯布里奇解释说,“对手则没有。”读者的建议和批评多以口头或信件形式呈现给编者,新闻机构就此有了无可匹敌的权力,决定着何者值得舆论关注。“大部分新闻……出自预定,”拉斯布里奇写道,“各编辑室的新闻编辑桌上都有一本A4尺寸的日志,里面标记着每一个即将成立的理事会或委员会,同时还有相应的新闻、消防、急救、水务和公用设施管委会。”成品不受如今许多媒体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影响,它主要是重述一天里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非对其进行解读或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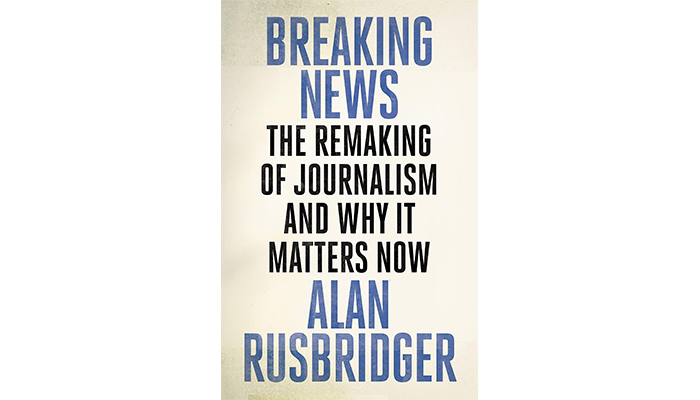
为了对一些重大利益展开拷问,许多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成果经常花费不菲,较高的利润率确保了他们的报酬。当电影《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将《华盛顿邮报》介入水门事件誉为调查报道的典范时,拉斯布里奇还是个新手记者。在他看来,新闻并无电影赋予的这种英雄主义色彩,但他也深信新闻乃是一条“不无瑕疵的,具有尝试性、迭代性以及交互性的迈向真相之路”。在任职于《剑桥晚间新闻》期间,他的报道对政府官员多有抨击,即便他们对其它的报道而言可能是不无价值的联络人或信息源。拉斯布里奇还记得某位导师对此关系有个话糙理不糙的看法:“你得定期踢一踢他们的蛋蛋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他们对我们的需要甚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
电视新闻的扩张逐渐对报纸形成了压力,后者不得不在其日常排程中加入更多背景性、分析性及生活方式类报道。但来自广告业巨头的收入仍足以补贴其开支。在美国,鉴于利润的驱动,收购独立机构到成立股票上市的联合大企业这一连锁式并购过程可谓屡见不鲜:譬如甘尼特公司、论坛出版公司、麦克拉奇报业以及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都遵循此路径。这一变化牵涉到摆脱地方性这一关键性战略决策,企业领袖为实现季度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在盈余处于高位时也偶尔会裁员。于数字革命的前沿谨慎试水的同时,优秀的新闻编辑室却因短视而无力维系下去。
互联网的兴起令印刷广告很快过时,许多出版物的盈利随之大跌,但母公司仍以盲目削减成本乃至于大规模裁员来应对。2007年以来,仅在美国一地就有数以万计的记者失业——堪比一个贸易集团破产的失业人数。在这段时间里,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网络上,尤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频率越来越高。在公众最需要记者的时候,这一代记者却没落了。
拉斯布里奇对数字新闻的谋划没有落入传统企业治理方案的条条框框。在他1995年刚当上主编的时候,《卫报》的所有者仍是斯科特基金会(Scott Trust),这一保护伞组织由诸多先期加入的业主构成,透过其它企业来支持其开销巨大的进步新闻事业。2007年至2014年间,该基金会将股份售予盈利颇丰的汽车杂志《汽车贸易》(Auto Trader),为《卫报》换取到估值达10亿美元的注资。
透过这一增强财政灵活性的措施,《卫报》得以在数字世界中继续其征途。许多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对手仅仅是敷衍性地把自家的纸媒内容照搬到网站上,《卫报》则试图以全新的报道形式和鼓励积极参与来开发其读者群资源,同时也推出了诸如窃听门之类的调查报道。新闻机构的受众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板和博客上发布信息。“新闻界200多年以来都是单方面对读者推送信息,”拉斯布里奇写道,“如今……活生生的读者群体——有时可达数千人——即时回应着你告诉他们的一切。”
拉斯布里奇试图以他所称的“开放新闻”(open journalism)来推进上述模式——报道要积极鼓励受众参与,其过程要突出透明性,要从外部源头为读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这套哲学对“9·11”事件后深觉被媒体误导的美国自由派而言尤其有吸引力,而《卫报》也借机扩张其全球读者群,以至于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形成了挑战。虽然海量数字受众的购买力一时难以确定,但拉斯布里奇以及其它许多人都相信广告商将会如以前那样逐渐跟上节奏。
这种强调尽可能扩大受众范围的思路,促使新闻机构开始尽力去容纳更广泛的主题和诉求。其推论则是,较之于报道市镇政府或地方文化,报道全国政治和好莱坞新闻将会带来更多读者。数字领域的新秀如BuzzFeed等就持有如下理念:其内容是专为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而量身打造的,以便资助更具实质性的新闻并保持对读者免费。许多报刊杂志公司也追随该理念,追求短期的点击率,但这经常会稀释其对自家核心社群的注意力。
早在1996年,《卫报》就曾考虑过向数字读者收取内容费用,但拉斯布里奇以如下理由长期拒绝实行:“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积极探索21世纪新闻业运作的最佳途径,不宜过快地回到19世纪支付模式的温室当中(况且它如今还未必适用)。”设置付费门槛,通常意味着仅对少量精英人群提供高品质新闻,这会让新闻难以为公共利益服务。“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生意在濒临破产前无时不刻地追求盈利,”拉斯布里奇写道,“那也只是理论上如此。”

《卫报》进军美国的举措——在《卫报》美国版(Guardian US)于2011年正式上马时达到高潮——与媒体界在各战线忍痛收兵的态势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它是2010年与维基解密合作披露绝密电报、揭开国家间外交黑幕的五大全球新闻机构之一。几年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也曝出一系列文件,揭露了美国政府的全球监听机构。斯诺登因这次曝光而在2014年与《华盛顿邮报》一并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Pulitzer Prize for Public Service)。
在拉斯布里奇心目中,斯诺登揭秘一事“证明了……制度性力量和媒体的独立何以如此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耗资巨大的法庭辩护及其它机构内(in-house)针对政府干预的防线,诸如此类故事便无从上演。而这也需要心思缜密的记者来判断哪些信息关乎公共利益,在新闻机构所面对的“公众”因互联网而变得日趋碎片化的时代尤其如此。
且不论其新闻理念收获了多少肯定,《卫报》每年还是要烧掉上千万美元的资金。虽然广告收入的增长足以弥补其开支,但许多公司如今更倾向于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投放广告,以便有针对地培育其潜在用户群体。对其卸任主编前夕的财政困难,拉斯布里奇的刻画难免有轻描淡写之嫌:“我2015年5月退职时,商业委员会宣称对公司的现况基本满意。”但日益严重的亏损也令他们不得不在日常的资金之外另觅生财之道,这要求继任主编凯瑟琳·维娜(Katharine Viner)必须设法将成本削减20%,包括对迅猛发展中的《卫报》驻美国分部动刀。
《卫报》坚守开放新闻理想的方式,是在吸引部分读者付费的同时,不强制排斥非付费读者。维娜上个月宣布,过去三年来全球有100万名读者自愿资助《卫报》。结束于6月的年度财报显示,其中有过半的人一直以来都在付费,仅在美国一地就有7万余人。该部分收入目前基本稳定,盈利略有提升,维娜希望明年春季时能确保收支平衡。然而,这艘以进步新闻旗舰自居的大船如今得以存续,也不过是因为眼下全球的自由民主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其愿景与时代需要恰好合拍,从而赶上了此刻的新闻复兴热潮而已。
在许多别的地方,一个新闻日趋式微的世界也在步步逼近。许多数字出版商仍需仰赖脸书、谷歌及其它科技企业来维系浏览量,虽然这些公司的算法没少为它们产出假新闻。在硅谷把持在线和按需(on-demand)视频服务的同时,随着电视用户的超龄,有线和广播新闻极可能面临类似的清算时刻。为避免撞死南墙这一结局,少数精英级美国出版物开设了付费专区:譬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它大牌或热门媒体。此外,中等档次的媒体——地方报纸及其它曾有重要贡献的新闻机构——极可能会继续衰败。这一两极化格局在某些方面已与拉斯布里奇所担忧的赢家通吃的废托邦媒体世界高度类似。
就所有制、愿景及其运作模式来看,《卫报》在诸多英语媒体中仍然独树一帜。以此观之,“突发新闻”不过是结构性问题的反映,而非其解决之道。在全书结束处,拉斯布里奇表现出悲观的态度并将拯救新闻业的重任寄予了科技巨头。“眼下的问题是,新闻业如何在这个跨国公司无处不在的时代存续下去:这帮享受免税且没有根基的家伙比我们的母亲还要懂我们,”拉斯布里奇写道,“它们究竟会支撑起一群独立、专业且富有批判性的新闻人和新闻业——姑且朝最好的方向想——并确保其能从一而终地履行必要的公共服务,还是会毁掉它们呢?”
要回答此问题,脸书及其它硅谷巨头们不仅要承认自家决策有编辑性质(editorial),还应为公共利益负起某种形式的责任。他们当然也可以扑灭新闻的最后一丝希望。在那个世界里,与完全没有社群相比,有封闭性社群也许已经值得庆幸。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