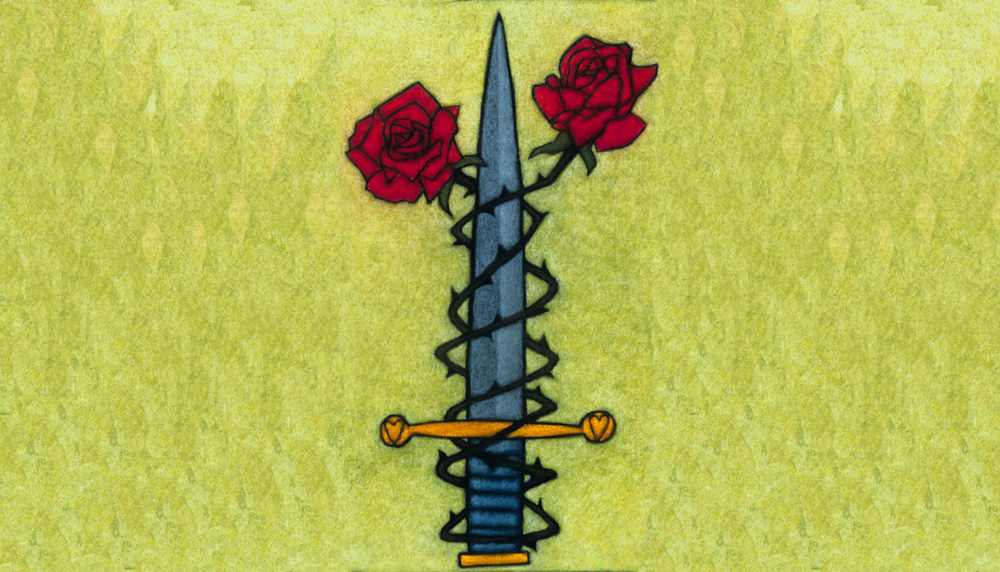文| 海伦娜·肯尼迪
翻译:刘溜
1
几乎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时代,都会出现一个女恶魔,作为女性这一性别堕落的象征。这个美杜莎集中了多种变态之处:性方面放荡、肮脏、色情,还可能是双性恋;对美好、高贵的品质一无所知——这些品质通常属于男人和孩子;说谎、欺骗、操纵并腐化。一个聪明而强大的女人。一个比任何男人都致命得多的女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女人。
人类灵魂的堕落,导致了极度残忍的罪行,它激起一种古老的渴望,即惩罚那些造成了伤害的人们,这种伤害不仅加诸个人,也使得家庭伤痕累累,沉入无尽哀悼。一直以来,人们很容易把女性罪犯视为受害者,其中很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确是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女权主义者在平权运动中,也很容易否认女性具有残酷和邪恶的能力。然而,的确存在这样的女性,她们犯下了和男人一样可怕的罪行。她们碰巧是特例。
一般来说,在恶魔的万神殿里,男性比女性更多,但那些非主流的杀人犯更有可能被神化。以一位叫做米拉·亨德利(Myra Hindly) 的女性罪犯为例,她的入狱不只是简单的惩罚,它象征了一种恐惧——我们害怕回到更原始的过去。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今天,亨德利这样的女人成为一个容器,社会向其中倾注了自身黑暗的秘密。就像战犯一样,这样一个“女恶魔”提示了令人恐惧的可能性。
亨德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女性中非人性的化身。不过,如果你问50岁以下的人,她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只是模糊地知道有孩子被杀了,以及这个案子带有虐待和性的意味。
很难说清人类灵魂的堕落腐化,在伊恩·布雷迪(Ian Brady)和亨德利犯下的罪行中,起了什么作用,律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案件的侦查始于1965年10月,当时亨德利的姐夫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告诉曼彻斯特警方,他看到布雷迪残忍地杀害了一名17岁的青年。警方立即赶到布雷迪和亨德利的住处,发现这个男孩已经被斧头砍死了。
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份名单,其中包括两年前失踪的12岁男孩约翰·基尔布赖德(John Kilbride)。警方意识到,他们可能在处理一项复杂的案子。为了寻找有关基尔布赖德的下落,他们搜遍了这处房子,发现了拍摄于附近沼泽地的照片。搜寻沙德伍兹沼泽(Saddleworth Moor)时,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孩子莱斯利·安·唐尼(Lesley Ann Downey)的尸体,她于前一年失踪。
史密斯还回忆说,他曾看到布雷迪从房子里搬走了两个手提箱。警方在中央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找到了箱子。几天后,基尔布赖德的尸体也在沼泽地被找到。
箱子里是有关性变态的书籍、短棒、唐尼的裸照,以及录有她的尖叫声的录音带。布雷迪和亨德利的声音很清晰,他们在告诫小女孩,叫她闭嘴并配合。小女孩受到了威胁,并被告知,将把某个东西塞进嘴里。这盒录音带后来在法庭上播放,它是定罪的关键,比任何证据都重要。
1965年,审判在切斯特(Chester)进行,控方和布雷迪都将亨德利描述为他忠实的副手。媒体将她形容为他的性奴隶。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她不是主犯,虽然她的行为如此罪恶,如此骇人听闻。主审法官芬顿·阿特金森(Fenton Atkinson)表示,她也许能够改过自新。他说:“我认为布雷迪邪恶得难以置信,无法救赎了,但是亨德利离开布雷迪之后,我感觉不太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亨德利到了舞台中央。布雷迪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在一家惩教机构服刑,直到2016年去世。这条疯狗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不管他曾经做过多大的恶,据说,最后都成了一个悲惨、错乱的样本。
亨德利不是这样。在2002年11月去世之前,她一直在寻求假释。这一点引发了对她的质疑。1974年,我代理了亨德利的案子,当时她承认了一项罪名:她与一名监狱看守密谋越狱。看守名叫帕特·凯恩斯(Pat Cairns),曾是修女,她爱上了亨德利。她们的恋情持续了三年,在媒体上掀起了报道淫乱女同性恋的狂潮。媒体付费采访那些出狱的犯人,让她们讲述据传发生在霍洛韦监狱(Holloway prison)的性幽会。就这样,他们进一步推断了亨德利的变态。
1994年,亨德利发表了一份声明,请求宽恕:“经过三十年的服刑,我想我已经还清了对社会欠下的债,也赎清了自己的罪行。我请求人们以现在的我,而不是过去的我来评判我。”
1998年,她表明自己曾被布雷迪虐待,后者曾威胁说,如果她不参与谋杀的话,他就杀了她的姐姐、母亲和祖母。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假释,但接连几任内政大臣都驳回了,他们清楚,那样做会引起公愤。当她死于癌症的时候,仍然在监狱里。


2
残忍的罪行挑战了我们对基本美德的信念,如果没有可以理解的动机,比如嫉妒、贪婪或对某种挑衅的回应,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们。
我们对无法归类、道德上也无法接受的行为深感不安。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归为疯癫所致,这样我们就不必对付邪恶这个麻烦的概念了。疯癫,尽管难以捉摸,但是对那些无法解释的行为,它是一个安全的标签。不过对于这个标签的使用,又很矛盾。如果有人以残忍的方式杀了人,公众希望他们被判为杀人犯,而不是疯子;他们希望在罪行的严重程度确认之后,进行精神鉴定,而不是此前。公众的谴责情绪必须通过仪式来宣泄。
疯癫无法解释,却又要寻找解释,同时人们又不愿让疯癫成为借口,这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们问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对另一个人、天真的孩子作出那种事?”,我们希望有人帮我们理解这种行为。
蓄意犯罪,有时无法解释的。虽然比较罕见,但确实有一些犯罪行为没有动机,也没有精神疾病的迹象。
有人反对“邪恶”这个概念,但大多数人接受它,并希望惩罚作恶的人。如果谋杀牵涉到性,我们会更加反感,如果牵涉到儿童,我们就更加无法理解这种罪行了。
当一个女人有意做出残忍之事,我们会感觉不适,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女性是养育者、照顾者。俗语说,那些犯罪的女人要么疯了,要么坏,要么不幸(women who commit crime are mad, bad or sad)。坏女人可能很少,但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就不会得到宽恕了。人们很难相信,为什么有人、尤其是女人,会袖手旁观,并允许有人进行折磨、拷打,不过,要记住,在集中营里,很多女人是这么做的,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斯兰国,女人们也正在这么做。男人恐怖,女人则邪恶。
1986年,沼泽谋杀案重启了,因为布雷迪向记者说,他还杀害了另外两名年轻人。随后警方在监狱里对他进行审讯,布雷迪拒绝提供帮助,但亨德利承认两名年轻人被害了。她说,承认如此重大的罪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她希望这一切能够平息下来,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受害者的家人。
亨德利清楚地解释她为什么会参与谋杀(并非借口),她当时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受控于一个复杂、有经验的男人。这一解释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因为这些话太有条理了。
除了亨德利中年时显露出的性格和意志力,很难看到别的。无论是最初的案件,还是后来的两起谋杀,她的认罪都太晚了,很难被视为真正的悔悟,更像她为获释而精心策划的行为。媒体披露了她在狱中的女同性恋生活,在一个对同性恋(更不用说对重刑犯了)怀有深刻敌意的时代,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憎恶之火。
3
女连环杀手极少,这里我说的是指那些接连杀害陌生人的人。因此1993年,当护士贝弗利·艾莉特(Beverley Allitt)因杀害婴儿和幼儿受审时,公众震惊了。她被诊断为患有代理孟乔森症候群(Munchausen’s syndrome by proxy),即女性利用母亲、护士或保姆等角色来伤害儿童。她表现出明显的高度精神失常,且非常危险,一开始人们不相信她的罪行,后来又有严重的道德恐慌,因为她作为照顾儿童的护士,破坏了公众心目中神圣的女性形象。
在少数情形下,女性参与连环杀人案时,充当的是侍女的角色,比如沼泽谋杀案和曼森谋杀案。她们与受到家暴的妻子不一样,后者由于无法承受暴力而屈服,或与丈夫串通。而前者被意志强大的男人掌控,这些男人以杀人来表达对人性的蔑视,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迫使别人付出终极代价而获得权力感。有些女人被这样的男人选中后反以为荣,好像她们是从普通女人中脱颖而出。
有些人的性角色似乎要求其放弃个人意志,这意味着永远不必为性的不检点承担道德责任,如果你的越轨行为构成犯罪,你也不必承担罪责。也许亨德利在那个生命阶段,需要布雷迪的性控制,正如他需要一个见证自己暴行的证人,然后他们因彼此了解而结合在一起。亨德利重塑了过去,这没什么可吃惊的。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她那巨大的耻辱感一定需要某种幻想。然而她每一次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都只会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狡诈的、善于操纵别人的女人,同性对她的罪行尤其厌恶。
杀人的女性会激起一种特别的反感,尤其是如果她们没有表现出令人同情的样子。亨德利没有哭。真正的女人会哭。然而,即使她们哭了,也会遭到怀疑。2003年,伊恩·亨特利(Ian Huntley)因杀害两名10岁女孩霍莉·威尔斯(Holly Wells)和杰西卡·查普曼(Jessica Chapman)而受审,他的女友马克辛·卡尔(Maxine Carr)也在被告席上,被控为他提供了假的不在场证明。卡尔之前对警方说,小女孩们来家里找她,当时她在楼上的洗手间。她声称听到亨特利在外面和她们说话,随后她们就离开了,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事实上,那时她在100英里外的格里姆斯比(Grimsby)。被捕前的那个礼拜,她帮亨特利彻底打扫了房子,也许毁掉了很多法医证据。
在审判中,卡尔承认说了谎,但是她把俩人的关系描述为,亨特利控制欲强、嫉妒,有时很暴力。她说,她是在亨特利的坚持下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因为他过去曾被诬告强奸,可能会因为那件事再次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她还说,她不能让自己相信是他杀了那两个女孩。
然而,侦查组的副队长、总督察安迪·赫布(Andy Hebb)对卡尔在证人席上泪流满面的表现不为所动,他坚信她一定曾对亨特利的所作所为有所怀疑。2003年12月,他对《观察家》表示:“我对此相当怀疑。”他如此公开地表达观点,助长了媒体对卡尔的普遍诋毁。公众的抨击使得她在出狱后不得不更换身份,并被安置在安全屋里。
另一个造就女恶魔形象的案件是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案,她最初于2007年11月在意大利佩鲁贾被判谋杀梅雷迪思·克尔彻(Meredith Kercher)。2015年,意大利最高法院最终撤销了对她的定罪,但是在此之前,她的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通过互联网和小报公之于众了。
克尔彻是利兹大学的一名英国学生,为了获得学位,她在意大利进行为期一年的海外学习。她被残忍地杀害了。喉咙被割,头部几乎与身体断开。发现时,她半裸躺在和诺克斯合住的房子里。
诺克斯是美国人,她和意大利男友拉菲尔·索勒西托(Raffaele Sollecito)受到审讯,并被控谋杀。一名名叫鲁迪·盖德(Rudy Guede)的男子也被控谋杀,并单独接受审判。
然而,吸引了媒体注意的,是诺克斯。有人把她的日记从监狱泄露给一名记者,披露出各种耸人听闻的细节。她说,她之所以记录亲密关系,是因为意大利狱方错误地通知她,说她有艾滋病毒阳性,所以她才列出跟她发生过性关系的人。意大利检察官宣称,诺克斯杀死她的室友,是因为她“缺乏道德感”。她心中充满了“不惜一切代价寻欢作乐”的欲望,而克尔彻身上的伤痕表明,那把刀是被人“戏耍般地”挥舞着,刺穿了脖子,最后捅进了这名年轻女子的体内。
最后,盖德被判谋杀,以及性侵克尔彻。他是一个有名的窃贼,警方在克尔彻的物品上发现了他血迹斑斑的指纹。
诺克斯被释放之后,在纪录片《阿曼达·诺克斯》中谈到自己是如何被人看待的:“(他们觉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荡妇——野蛮,变态,沉迷于性。”她指出她跟7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不是什么世界纪录。毫无疑问,这个年轻女人的性欲被用来暗示她杀了人。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她被问及是否喜欢变态的性行为。在整个案件中,对诺克斯的判断基于我们如何看待女性的性,以及如果一个女人有数个情人,那意味着什么。正是这些无关的因素使得女性在面对司法程序时充满了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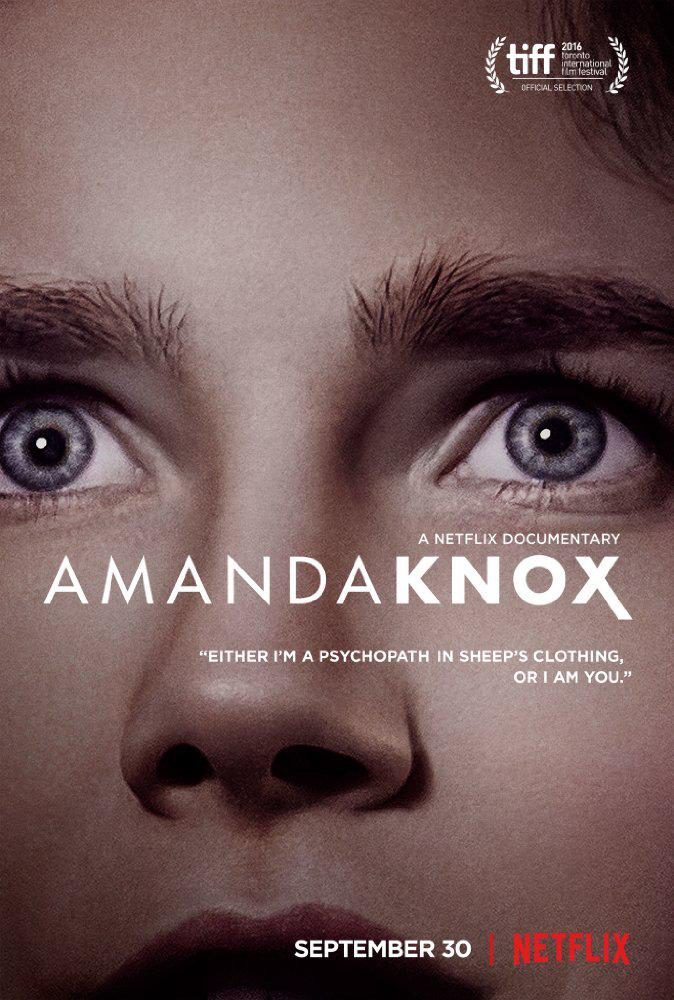


4
安·琼斯(Ann Jones)在其权威著作《杀人的女人》(Women Who Kill)中指出,对女性与犯罪的道德恐慌,正好与女性朝着平等迈进的时期相吻合,这种恐慌可能是在粗暴、甚至是无意识地抑制这些进步。
1955年,露丝·埃利斯(Ruth Ellis)案进行审判,她因谋杀情人而被判有罪,从而成为英国最后一名被绞死的女性。当时,由于战争结束,女性正被迫重返家庭。安·琼斯的理论中,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指出了,司法系统是如何回应那些参与政治运动或为平等而战的女性的。最严重地挑战法院的男性权威的女性,是那些为了践行其政治信仰而不惜犯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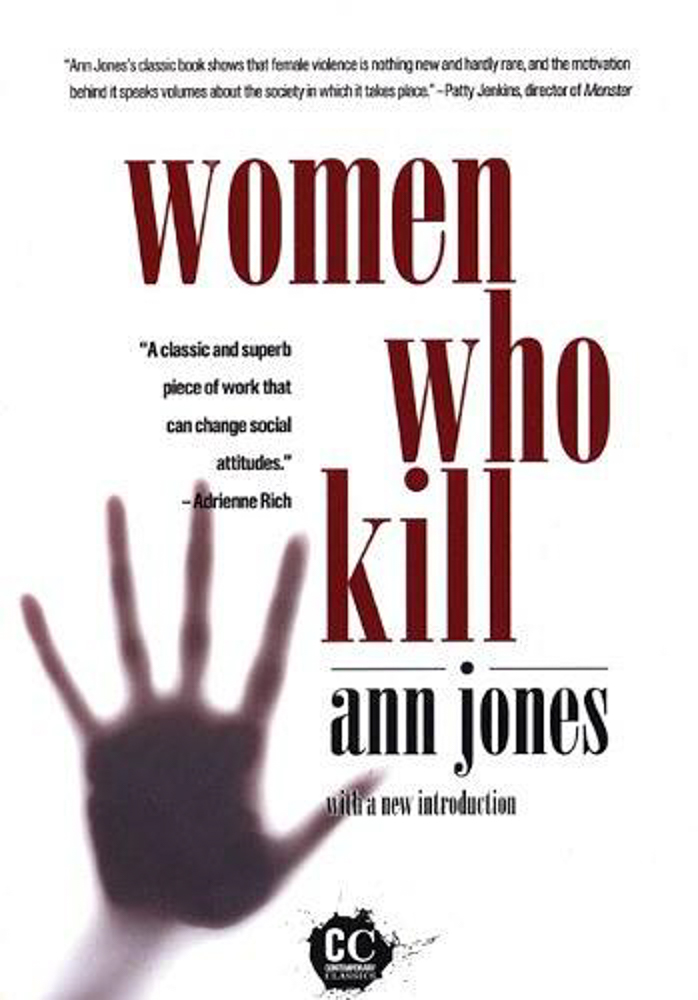
1970年代和1980年代,许多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性出庭受审,因为她们参加了反核运动,如格林汉姆·科门的妇女和平营(women 's peace camp at Greenham Common),或是女权主义示威,如“夺回夜晚”(Reclaim The Night)和“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Women’s Right to Choose on abortion)。这些公众运动是本世纪初妇女参政运动的延续。但是法院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很多女性批评该体系居高临下的家长式作风,与妇女参政运动时的司法体系非常相似。
处理公共秩序案件时,司法体系往往会引发愤怒情绪。由于大量涉及的案件都是因政治自由的实践而引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公正感。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两性在法院的遭遇并无差别,但是当女性组织为女性权益的游行时,情况不一样了。
在纽伯里(Newbury)格林汉姆审判的前期,女性聚在一起、要求和平的欢庆气氛渗透到了法庭。地方法官对面前形形色色的女性感到困惑不安:不同阶级、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女性,女同性恋,修女,母亲。当时我受委托为一群女性辩护。一次法律辩论没有成功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我退出,这样她们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声明。我坐在一边,亲眼目睹向来严格的法庭程序被改变了——这太了不起了。这些女性一个接一个,有力地解释了她们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被告席上人数众多,她们没有被吓倒,在通常仅限于男性的舞台上自由表达自己,并互相鼓励和支持。
然而,这场女性的叛乱必须遏制,于是这些女性被分开,一次只审判一两人。这些多样的女性很快被媒体描写成1970年代的刻板样貌:工装裤、刺猬头、不相配的耳环、没有口红的痕迹。传言中,这个或那个女人是厌男者,离经叛道者,放弃了对家庭、炉灶和孩子的责任,在男性领地边上转悠。法庭上很快表现出了对格林汉姆女性的敌意,即使是最轻微的妨害案件,也会询问这些女性有没有子女,她们被捕时谁一直在照顾她们的子女。而站在纠察线上的矿工永远不会被问到这些问题。
在媒体的报道中,格林汉姆案从一场合法的和平运动,变成了一场滑稽表演,最终沦为一场变态秀。这一过程就是在法庭上完成的。
当代政治已经抛出了另一种政治女恶魔。女性恐怖分子很特殊,因为她挑战了众多女性犯罪的悲情色彩。她对国家的攻击是双重的:一是直接的方式,用炸弹袭击国家机构;二是间接的方式,对抗女性作为社会基础的传统角色。
年轻女性与权力相结合,似乎很性感,“冷酷”、“精于算计”和“无情”等词常常与“迷人”、“活泼”和“漂亮”并列在一起。爱尔兰共和军中有很多活跃的女性,男性警察、律师、法官和记者都被女性手持阿玛莱特(Armalite)步枪的形像迷住了——但他们也害怕其背后隐含的意义。贯穿这些案件的是一种恐惧感:女性竟会利用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来使他们放松警惕。
性与罪、惩罚与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审判参与政治的独立女性时,这些因素主宰了法庭的氛围,其结果是,微妙、潜藏的判断影响了审判的进程。在最终判决时,女性并不会被区别对待——在这点上没理由批评法院不平等——但是一种对她们的担忧和恐惧影响了庭上的辩论。
5
今天,令人心惊胆颤的是那些加入ISIS和其他极端伊斯兰组织的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萨曼莎·卢斯韦特(Samantha Lewthwaite),她是一名退伍军人的女儿,在北爱尔兰唐郡(County Down)出生并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皈依了伊斯兰教。她是杰曼·林赛(Germaine Lindsay)的妻子,林赛是2005年7月7日在伦敦造成多起爆炸、导致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四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一,他在皮卡迪利线(Piccadilly line)列车上引爆了自己。
事件之后,卢斯韦特一家身份暴露,萨曼莎和孩子们遭受了一次报复性的纵火袭击。不久她就失踪了,据信她去了索马里,嫁给了军阀哈桑·马利姆·易卜拉欣(Hassan Maalim Ibrahim),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的高层。她成为全球头号女通缉犯之一,2013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对她的红色通缉令。据说她策划了多次恐怖袭击,包括2012年对肯尼亚蒙巴萨一家酒吧的炸弹袭击,当时游客和当地人正在那里观看足球比赛;她下令暗杀两名穆斯林牧师和两名新教牧师;她还与2013年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Westgate mall)爆炸案和2015年加里萨大学(Garissa University)屠杀事件有关,后者造成148人死亡。
2016年9月,有三名女性圣战分子袭击了蒙巴萨的一个警察局。其中一人持刀袭击一名警察,另一人投掷了一枚汽油弹。三人都被击毙。其中一人还带着一件未爆炸的自杀式背心。这三名女子的笔记本电脑和电子邮件表明,她们一直与卢斯韦特保持联络。安全部门称,卢斯韦特参与了对女性的在线培训,鼓动许多人离开家人,前往叙利亚和索马里等地参与创建伊斯兰国际。青年党一直与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有关联,但最近该地区发生的暴行,却被ISIS认领了。有人推测,卢斯韦特已经死了。


在2017年之前,另一名被通缉的女性恐怖分子是萨莉·琼斯(Sally Jones),也被称为乌姆·侯赛因·布里塔尼(Umm Hussain al-Britani)。她曾住在肯特郡,是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2013年,她开始在网上与一个名叫朱纳德·侯赛因(Junaid Hussain)的年轻穆斯林黑客交流。
他把她拉入了伊斯兰教。当他决定去叙利亚时,劝她也一起去。那年冬天,她带着9岁的儿子乔离开了英国。18岁的大儿子选择留下。她在抵达叙利亚当天就嫁给了侯赛因,并皈依了伊斯兰教。乔改名为哈姆扎。然后他们前往拉卡,侯赛因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琼斯接受伊斯兰教的教导,以及ISIS对教法的极端解读。
不久,侯赛因娶了一位年龄比琼斯小一半的叙利亚年轻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大多数武装分子都有不止一个妻子,但通常都是绑架并奴役雅兹迪人(Yazidi)、基督徒或什叶派妇女。当时,琼斯曾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在哈里发治下的美好生活。
有情报称:琼斯招募了数十名年轻女性,据成为线人的叛逃者说,由于成功鼓动追随者对西方发动攻击,她很快升到了一个显赫的位置。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还未能确认。
侯赛因被怀疑操纵了ISIS的黑客攻击,以及在西方招募同情者,实施独狼攻击。据信,他还向ISIS提供了雷达技术。所以他是美国军方的重点打击对象,2015年8月,他在拉卡(Raqqa)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有报告说,琼斯作为圣战分子的遗孀,成为了高级别的培训者,她训练了一支特别部队,成员都是新招募的欧洲女性,她教她们使用枪支和制造炸弹,并演示如何策划和实施自杀式袭击。法国情报机构认为她与2016年在巴黎逮捕的三名携带毒气罐和其他材料的女性有关。报告说,琼斯和她的儿子去年在美国的另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2017年5月的报告估计,前一年有50名英国女性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一些是与丈夫、甚至孩子一起去的,另一些则是独自前往,或与朋友一起,吸引她们的是浪漫、冒险和虔诚。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低估了。召唤女性前往、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这抓住了许多圣战新娘的想象。2015年2月,闭路电视的录像镜头显示,阿米拉·阿贝斯(Amira Abase)、沙玛·贝谷姆(Shamima Begum)和卡迪扎·苏塔纳(Kadiza Sultana)这三名女学生从伦敦东部的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出发,途经伊斯坦布尔前往叙利亚。她们至今下落不明,人们担心其中有人、或是已全部死去。
毫无疑问,上述女性中,有一些和男性一样,在政治上非常坚定,但也有很多是被洗脑,她们以为自己在创建一个理想的伊斯兰国——也许就包括这三个女孩。她们到达叙利亚之后,肯定被正在等待他们的事情所伤害,她们可能改变了主意,但那时已无路可走了。
在ISIS内部,女性通常被买卖或交易。她们被用作工具,以留住幻想破灭的军人,或是看管当地的妇女,或是被强迫生育小孩,并被迫接受自己作为几个妻子之一。德国难民营和避难所里的雅兹迪妇女报告说,她们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被屠杀,其后她们遭到轮奸。同时,她们也遭到了ISIS的女性的虐待。
随着ISIS逐渐被击退,该组织的许多女性目前被关押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的战俘营里。英国政府的内阁大臣们希望那些离开英国、加入ISIS的武装分子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希望他们在被捕的国家被起诉。然而,人们不太相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能进行公平的审判。

重返英国的女圣战分子不可能获得多少同情,但是整个体制应该超越本能,超越情绪。前往加入恐怖主义组织是一种罪行,但也不宜放大。一些女孩在机场被政府拦住,进而谨慎决定,是否有必要提出起诉——往往没有必要。但是,当她们返回,如有证据表明她们参与恐怖活动、招募人员、虐待被奴役妇女或其他犯罪行为,就必须面对审判,如果定罪,理应受到长期监禁。
然而,我的经验是,当法律标准降低,就会出现错判,有人会因此付出生命代价,因此保持高标准是必要的。ISIS本身就有极度的厌女症,这意味着其中的一些女性可能受到了严重的虐待,并可能遭受威逼和胁迫。司法系统很难通过未经证实的叙述、脆弱的证据和强烈的公众敌意来辨别是非。这是一个复杂的司法领域,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 完——
本文节选自海伦娜·肯尼迪(Helena Kennedy)的《被羞辱的夏娃:英国司法如何辜负女性》(Eve Was Shamed: How British Justice is failing Women)。该书于10月11日由Chatto & Windus出版。本文曾于2018年10月2日发表在《卫报》,中文版已获授权,谢绝转载。
Copyright©Guardian News & Media Ltd 2017
版权顾问:群岛图书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