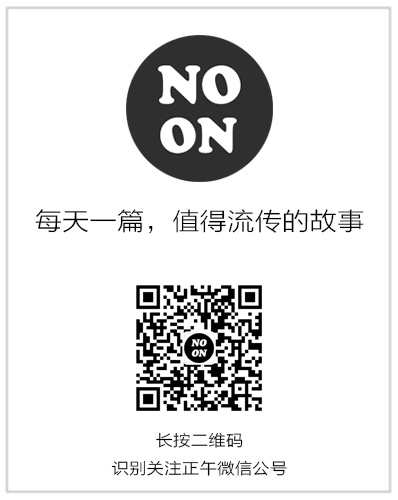一
霍大为(David Hogge)在华盛顿有一份干了快十五年的工作:美国弗利尔与赛克勒艺术博物馆(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合称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部主任。他两鬓斑白,发际线也急急地奔向脑后,高挺的鼻梁在狭长的面颊上更为凸显。与湿热严肃的华府相比,霍大为更喜欢西海岸的家乡西雅图,那儿终年下着温和多情的雨。在家乡的华盛顿大学,他读完了艺术史硕士,成了一名精通日语的日本艺术专家。但在大学时,他便对中国画产生了兴趣,因此又学了中文。
在博物馆迷宫般的办公区一角,档案室像一座无声的矿,埋藏着无数仍待开掘的亚洲艺术学者、考古学家、收藏家和古董商的手稿和摄影收藏。有访客的日子,霍大为会拿出他最爱的馆藏给你一通展示,像个口述人一样娓娓道来背后的故事。多数时候,他都躲在档案室里一排排贴满标签的铁皮储藏柜背后,埋头打理那些尚未启封的历史。
2008年,霍大为整理出了一批玻璃底片,共44张,底片的主人公是慈禧。这批主要摄于1903年和1904 年间的照片,大多出自慈禧当时的御用摄影师裕勋龄之手,后被勋龄的妹妹裕德龄(做过慈禧身边的女官)带到美国,当作插图收录进她的回忆录里。德龄去世(1944年)后,她的丈夫以五百美金的价格将照片卖给了博物馆。虽然馆藏几十年,但照片中依旧逼真的细节让霍大为动了心。他打算以这些底片为基础,筹备一次关于慈禧的影像展。
2009年的某一天,霍大为在搜集资料时,突然留意到一幅作品,由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erine Carl)绘成于1904年的慈禧画像。这是慈禧本人的第一幅肖像油画,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幅,高近三米,宽两米, 接上画框后高度近五米。
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是这幅慈禧肖像的所有者,但霍大为前往该馆拜访时,却没有人知道那幅画的下落。几经搜寻,他找到了一份油画租赁的原始记录——这幅油画在1966 年被租借到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记录上,还有一长串十几年尚未支付的保险费。但无论美国还是台北,双方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幅画的存在。
二
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似乎不太愿意提起这幅慈禧肖像画。虽然它已在台北停留了长达45年,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幅画再也没公开露面过。
“我不认为历史博物馆是故意(不支付保险费)。这幅画在台湾曾经非常受欢迎,也很有名…很多年长的台湾人对它十分熟悉。”霍大为说,“接着,这幅画就不见了。”
根据历史博物馆助理研究员赖贞仪的记录,1965年9月,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包遵彭赴美参加活动时,获悉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收藏了一幅卡尔画的《慈禧太后肖像》,深感其历史意义重大,便有意将该画带回台湾展出。当时的台湾与美国还有邦交,于是史密森尼以长期租借的名义,将这幅画像于次年5月运往台北。
自1966年抵台一直到1990年代,这幅肖像画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了近三十年。台北气候潮湿,再加上博物馆建筑体空间不够,博物馆决定暂时将画收进库房保管,一放就是十几年。
霍大为一心想把画运回美国,作为自己慈禧主题展的一部分,但当时的他对画的尺寸大小以及画面状况都不是很清楚。他向美国艺术博物馆提议收回这幅画,得到的回应却非常冷淡——他们对慈禧画像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严格来说,它和美国艺术没太大关系,而且也不能称得上是一幅杰作。更让霍大为生气的是,博物馆想把画直接送给台湾。
“我告诉他们,这是清廷送给美国的官方礼物。(如果)我们拱手送给了台湾,中国大陆的媒体会怎么想?”霍大为说。
在台湾,历史博物馆获悉美国有意收回这幅慈禧画像后,一时也很紧张。当时正值世博年(2010),美国国务院也在考虑要不要把这幅画像运到上海,在世博会的美国馆展出,但这一计划后来没有成行。而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为这幅画像举办了短期的重新公开展览。据霍大为回忆,历史博物馆曾多次接洽美国艺术馆,希望能对画像做一些修复性处理,争取把画留在台湾,但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既然美国艺术馆并不想收回这幅慈禧肖像,霍大为想,能否让自己工作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将其运回呢? “我们应该把画拿回来。”他开始反复游说自己的领导,“虽然它不是一幅杰作,但从历史意义上看,这是中国人给美国的第一份重要的官方礼物。”
经过来回近一年的沟通,2011年年初,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终于同意自费将这幅慈禧画像运回美国。博物馆不仅动用了一架货机托运油画,还于2011年5月和9月两次派馆内会说中文的中国画修复师格蕾丝.简(Grace Jan)去台湾查看画面状况并监督画的运输。
据简回忆,在最后一次抵台前,她委任了一位台湾当地的修复师对油画做了一些保护性处理,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整幅画的拆卸和装运在一天内完成,共动用历史博物馆以及外聘的家具师、研究人员、木匠等十余人。
2011年10月,漂流了四十多年的慈禧油画终于回到美国。此前,除了派去监督油画运输的格蕾丝.简,博物馆里还没有人亲眼见过画像。霍大为和其他人一样满心期待地前去一睹慈禧尊容。但看到拆封后的画像后,大家都沉默了。他清楚地记得,“馆长的肩膀都耷拉了下来。”
油画表面很黑,布满了裂纹,而且掉色严重。画面中的慈禧端坐在一团黑影中间,面色蜡黄,嘴角两边有两块剥落的油彩,像是掉了两块肉。

三
1904年,油画完成前,六十九岁高龄的慈禧究竟长什么样,在世界上仍是一个谜。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在清廷的默许下,大批义和团拳民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进入北京,大肆烧毁教堂,屠杀基督徒。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宣战”,并悬赏捕杀洋人。清军和义和团开始大举围攻北京的外交使馆。事件很快演变成国际冲突。7月中旬,历经一个月的混战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8月,北京沦陷。仓皇中,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在列强眼里,那时的慈禧既是一个神秘人物,又是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两者相叠加的后果就是外媒刻画的慈禧多是妖魔化的形象。1900年6月出版的美国杂志《Atlanta Constitution》,索性把慈禧拟画成当年纽约的一个著名女谋杀犯,身披凤冠霞帔。而同年7月4日出版的法国《Le Rire》杂志封面,则把慈禧打扮成一个太监,左手紧握匕首,右手攥着扇子,手指似爪,背后的一根柱子上插满血淋淋的基督徒的头颅。
慈禧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外界怎么描绘她,但她意识到改变自己一落千丈的国际形象刻不容缓。一张摄于1902年的照片(摄影师不详,照片收录在1908年11月出版的法国周刊L’Illustration里)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一群在北京的外国人获悉慈禧太后即将回京,就站在城墙上等着一窥其真容。进城门时,慈禧先去旁边的观音庙上了香。从庙里出来时,看到城墙上有人举起相机,她非但没有忽略,而是朝镜头挥了挥她的手巾。
回到北京的慈禧为扭转自己的形象,开始逐渐修复和各国外交使团的关系。为此,她在宫中接见招待了很多外交使团中的女性,因为她觉得女性对联谊兴趣更大。其中,和慈禧关系最好,同时也是帮助慈禧改善形象的功臣之一,是当时美国驻京公使爱德温.康格(Edwin Conger)的夫人莎拉.康格(Sarah Conger)。康格曾这样评价她和慈禧之间的友谊:“如果你亲眼见过她,并且让她握着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就像她对我做的,你也能感受到她的诚意。”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接见外宾,慈禧在1903年初召见了曾驻巴黎的外交官裕庚一家。裕庚的太太路易莎.皮尔森(Louisa Pearson)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因随父常年驻外,皮尔森的四个孩子精通多种语言并熟悉西方社会的风俗礼仪,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对姐妹花——裕德龄、裕荣玲。进宫后,姐妹俩一直陪在慈禧身边,担任其翻译和顾问,直到1905年因父亲病重离开宫廷。
德龄离宫后,用英文撰写了一系列回忆录。尽管回忆录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是她的第一本书 ——《在紫禁城的两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可信度相对较高,详细记录了她在1903年至1904年期间在慈禧身边的个人经历。在美国大学担任艺术史副教授的彭盈真,仔细对比过德龄的这本书和同时期在紫禁城出入的其他外国人的回忆录,发现虽然书对德龄本人在宫中的重要性有所夸大,但就基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而言,契合度较高,没有太多捏造成分。
1903年6月的一次私人觐见上,康格向慈禧提议,让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卡尔的哥哥当时在天津海关工作)为慈禧画一幅肖像画,代表中国参展来年(1904)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让美国人见识见识慈禧的容貌。而慈禧对此的态度,康格和德龄的记录有出入。康格在她出版于1909年《中国札记》(Letters From China)中提到,慈禧对她的提议很有兴趣,很快答应了。但彭盈真教授更相信德龄的说法。
“皇太后看上去对(肖像画的提议)有点震惊。”德龄在书中写道。毕竟在中国,肖像画一般是在人死后所作,用来纪念死者或后世拜祭祖先。慈禧还有其他顾虑:首先,让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外国画师进驻宫廷,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妥善安排住所,还要确保她不过多接触宫中的人,对皇室留下较好的印象。再次,肖像画需要作画对象长久保持固定的坐姿,而慈禧显然没有那么多耐心摆同样的姿势。德龄因为在巴黎就与卡尔相识(卡尔曾在巴黎学画, 并为德龄画过肖像),彼此相互了解,她又拿出了自己的肖像画,供慈禧参考,并尽量模糊解释作画的时间长短,才最终说服慈禧接受康格的提议。
慈禧对这幅油画,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从6月康格正式发出提议,到8月底卡尔进宫作画这段时间,她突然对摄影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仍要归功于德龄。为打消慈禧对肖像画的顾虑,德龄之前并没有给慈禧看自己在巴黎时拍的照片,因为她担心慈禧会因此决定用照片来替代画像,毕竟拍照所需的时间要比为画像摆姿势少得多。但在一次偶然的探访中,慈禧在德龄的寝室看到了这些照片,一下被吸引住了。当得知德龄的弟弟裕勋龄是业余摄影师时,慈禧立即召见了他。
在德龄的笔下,慈禧对照相的兴趣似乎远大于画像,但在彭盈真看来,慈禧让勋龄照相最开始的动机其实是为油画做准备 --“她是透过勋龄的照相来决定什么样的背景,摆什么样的姿势。她其实做了很多演绎,要正面,还是模仿西画,(用)半侧面的角度。”
从1903年9月到1904年8月,卡尔在宫中待了近一年。据她自己于1905年出版的畅销书回忆录《和慈禧皇太后在一起的日子》(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记载,她总共画了四幅慈禧的肖像,但现今为人所知的只有两幅。另一幅目前仅知收藏在北京,且因长年曝露在不理想的环境损毁严重,没有公开展览。尽管卡尔在回忆录里对慈禧的容貌仪态和审美品位大为褒奖,但在实际作画过程中,她明显有点“水土不服”。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细节,忌讳“阴阳脸”,和卡尔在巴黎学习的十九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讲究阴影和透视的画法相冲突。此外,画面的内容,大到布景,小到一个配饰,都是由慈禧来决定的,卡尔完全没有发言权。创作自由一再地受限制,很快浇灭了卡尔刚来时的那股热情和期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不得不遵从(中国传统画法)之前,我内心有过很多挣扎和反抗。”
其次,卡尔也没有太多时间仔细琢磨怎么画慈禧。裕家姐妹受委派照顾卡尔,一方面带她四处游玩,另一方面又充当慈禧的耳目,除了不时向太后汇报卡尔的近况,还要在慈禧累了的时候,充当她的替身,为画像摆姿势。据德龄在回忆录中记载,作画期间,慈禧大多只在卡尔画脸部时出现,而德龄则每天需要假办四个小时的“慈禧”,直到画像完成。事实上,在卡尔为慈禧画的第一张画像里(也称试手画,用来考核新晋画家的能力)就能看出不少端倪:画像中的慈禧一手捏着一朵花,一手卧在榻上,脸部微侧且圆润,很年轻。如果比对同时期慈禧和德龄在一起的照片,就不难发现,画中的慈禧有德龄的影子。
但这并不表示,慈禧不重视这幅即将送往美国的画像。相反,“慈禧很重视这张画。她把这张画当作某种形式的祖宗像来制作。”彭盈真说。中国的传统里,最正式的画像角度就是祖宗像——正面端坐,面部无表情。最后的成品画里,慈禧的坐姿延续了祖宗像的姿势。
1903年的冬天,卡尔开始着手画这幅最终参展的慈禧油画,直到1904年四月底完成。期间,慈禧亲自设计,以镜框的造型,让宫廷的造办厂赶制了一个巨型画框,顶座刻双龙逐“寿”图,四周雕刻“万寿”字样。



四
2011年秋,正当霍大为在为这幅破损严重的油画一筹莫展时,谭家珊(Jia-sun Tsang)成了他的救星。
年近中旬的谭家珊,个子不高,一米五的样子,有一头齐耳的灰白短发。我在她的工作室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粉色T恤和棕色卡其裤,戴着红色镶边的圆眼镜,看起来神似老年版的樱桃小丸子。谭家珊的头衔是史密森尼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高级油画修复师。今年是她在中心工作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修复现当代油画是她的强项。
谭家珊说,她快忘记了四年前第一次看见这幅慈禧画像的情形,但她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兴奋。“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幅画能被修复。”她告诉我。“画的状况其实不错,尽管它看上去很糟。”
霍大为工作的艺术博物馆和谭家珊所在的修复中心,是史密森尼旗下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很少会有交集。艺术博物馆的画也不属于谭家珊的工作范畴,但由于馆内的中国画修复师没有修复油画的经验,卡尔的这幅慈禧画像提供了一个契机。更让霍大为感动的是,谭家珊主动向修复中心的领导要求,由她来组织修复这幅看起来似乎修复无望的画。
大型油画修复往往需要团队配合。谭家珊迅速组织起了一个包括科学家、工艺师、家具修复师等五十六人的团队,开始向卡尔画笔下的慈禧“动刀”。
在对画面损耗做技术分析时,谭家珊借助红外线反射图像,发现了卡尔的“初稿”——画家在作画过程中所作的修改。这些修改往往隐藏在后补的油彩层下。
比如,慈禧左手的摆放姿势是改动过的。原来的两只手捏在一起,揪着一条手巾, 交叠在腹部,但卡尔不喜欢,认为慈禧的手部被遮盖太多。据卡尔的回忆录记载,慈禧一开始很坚持,但最终被说服,让她改成了试手画中左手卧榻的姿势。此外,卡尔还曾上移过慈禧的眼睛、眉毛和发线的位置。
这些反复修改的位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纹。画像最明显的损耗就是其表面大量的干裂纹,有的发如细丝,有的较宽且突边呈小岛状,最严重的出现在慈禧的脸部。谭家珊说,造成裂纹的主因是画家在底层颜料未干时,就覆盖上新的颜料,顶层油彩干凝收缩时裂开成缝。这说明卡尔修改得很仓促。
另一幅摄于画像完成前一个月的照片显示,慈禧的脸部在当时仍然是草稿状态。谭家珊推测,卡尔在最后时刻仍试图用西方写实主义的风格更生动地捕捉慈禧的面部表情,但最终的呈现效果,却是中国传统肖像画法的平面且无表情。
仓促作画,再加上清廷的压力,卡尔被迫作出反复修改,可以佐证为何画面上的干裂纹如此之多。霍大为认为,虽然台湾潮湿的环境会加快油彩掉落,但画家的技术以及画的质量才是造成画面破损严重的主因。
根据谭家珊的记录,光是除去画面上的污垢就花了三个月(在台湾展出时,由于整幅油画被钉在墙上,画布表面沾上了不少油漆)。此外,由于画布已经变形,无法支撑油画。谭家珊的团队需把画布加湿并在重力和真空中压平,再用另一块帆布托底,增加布面的稳定性。
完成这一切后,真正的修复才开始。
首先,要清除导致画布表面发黑发黄的老化光油。画家在油画完成后,往往会上一层光油来保护画面的色泽。光油发黑是自然现象,时间一长,画面中的细节就不可见了。清除前,谭家珊对画像测试了不同的化学试剂,确保画面中的色彩不会被一并抹去。
“油画修复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所以,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有指导。作为油画修复师,我们知道哪些事我们能安全地做,哪些事不能。”谭家珊说,“比如,画面中有些绿色对某些试剂很敏感,如果上面有很脏的光油,我们只会对其弱化处理。”
虽然修复无法去除画像中的干裂纹,但填上颜料可以减少对观赏的影响。谭家珊能用肉眼分辨出150种绿色,她用色粉和黏合剂调制出一种可逆性的颜料,经过数月的描点(肉眼看不到的点),重现了卡尔原作中鲜亮的色彩。
“我们想要(裂纹)被看见。有时,画的真实性很重要。所以我们只把(裂纹的效果)最小化,让你能够识别。”谭家删告诉我。“可逆性是油画修复的重要原则。如果你不喜欢我的修复,只要通过少量的试剂就可以将其抹去。”
画框部分,由于很重,需要很多人力配合来修复。整个框架由四十余块木料粘合而成,搬运时需要把每块拆开,等展出时再重新组装,因此不少木料已经破损无法使用。
卡尔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整个框架由樟木制成,但修复中心的家具修复人员经过分析发现,原材料很可能是毛泡桐,木身柔软易雕琢(考虑到当时的制作工期很短,清廷的工匠们很可能偷偷替换了木料)。修复人员用类似毛泡桐的木材制作替代木料,更换榫舌,并在框架顶部加以固定。整个画框的清理花费数月,最后再涂上清漆恢复木材的光泽。
2013年秋,长达两年多的油画修复完成。修复期间,霍大为几乎每周都要来仓库观看修复进度,拍摄照片和视频做记录。在他办公室的电脑上,霍大为给我展示了一张油画修复完成后,画布与画框首次对接时他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异常兴奋的谭家珊在画前跳起了舞。
“这大概是我在这世上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了。”他说。


五
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卡尔的慈禧画像被陈列在美国厅的东北角,一同展出的大都是半身像或侧面像。据当时的报道记载,慈禧画像的确吸引了不少注目,但很可能是因为它大而显得特殊。同期展出的其他作品里,最著名的是美国画家、自然主义画派的先驱Gari Melchers画的Doctor Harper。世博会结束后,慈禧决定将自己的第一幅官方画像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并在白宫举办了正式的馈赠仪式。随后,该画被转移到史密森尼学会收藏。
“(这幅画)代表的多是那个特定时空氛围的一个写真。”彭盈真评价说,“如果没有庚子拳乱,不会有这张画。因为这张画是慈禧为了扭转自己的国际形象,跟美国在外交关系上的妥协。它毕竟是美国这一方提出的相对柔性的诉求,而慈禧当时也很想跟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那个特定时空,与欧洲列强崇拜军事主义扩张不同,美国似乎更重视商业与文化的交流。早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第一个外交协定《中美望厦条约》里,当时的美国驻华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极力促成添加了著名的第十八条《文化条款》,允许美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并雇佣中国人教习中国的语言。顾盛通过该条约收集了约230多种中文和满文书籍,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首批中文馆藏。
半个多世纪后,顾盛的接班人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是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利益均沾,实际上是在为美国争取更多在华的商业和贸易机会。
1900年10月,李鸿章赴京和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在最后签订的《辛丑条约》里,中国作为战败国需支付其他十一国共4.5亿两白银,折合当时的3.3亿美金,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赔付一两。德国获赔最多,占到总赔款额的一半多。美国分到了约2440万美金的赔款。 但《辛丑条约》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认为赔款数过重,曾考虑通过退还部分赔款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压力。1908年,也是慈禧去世的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咨文(当时中国已经赔付了约一半)。“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办学,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年成立的肄业馆(清华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前身)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其他列强后来纷纷仿效美国,将部分赔款用来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
说卡尔的慈禧画像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主因多少有点牵强,但霍大为和彭盈真都认为,这其中或多或少有慈禧肖像外交的功劳。
2010年,正愁着如何将慈禧画像从台湾运回美国的霍大为,无意中在美国国务院布莱尔宫(Blair House)的阁楼上找到了一张肖像照,那是慈禧在1904年以私人礼物送给罗斯福总统的。由于当时的摄影技术有限,为弥补细节失真,慈禧派人在印出的照片上填上了涂料和镀金进行修饰。1905年,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访华时,慈禧又送了一幅尺寸较小的肖像照。这些照片以及卡尔的慈禧画像共同构成了慈禧肖像外交的一部分。
2011年秋天,霍大为策划的“权力/剧场:慈禧太后”在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展。44张关于慈禧的玻璃底片构成了这次展览的主体。在介绍文中,霍大为写道:“当美国有意向放弃庚子赔款时,罗斯福(以及他的家庭成员)自然成为了慈禧私人馈赠的对象。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影像都是经过战略性考量、通过建立私人纽带来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之一。”
但卡尔的慈禧肖像由于仍在修复中,并未展出。不过,就像霍大为说的,这样一幅由美国人提议、美国人创作的肖像画本身就是“美国在艺术上与中国相逢的极好见证。”重新返美,已成为百年前那段难得的相逢与友谊的一个完美注脚。
某种意义上,如今这副画像早已不是画家一个人的作品。卡尔是创作者,霍大为是发掘人,谭家珊是修复师。三个美国人,在不同时空与慈禧太后“见面”,擦亮了她当年本无心插柳的一段中美外交史。他们共同组成了慈禧修护人。
彭盈真认为,卡尔当初能为慈禧画像,完全是沾了性别和国籍的光。论技巧,卡尔比不上另一位慈禧画像的创作者——来自荷兰的男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华士于1905年为慈禧画了两幅肖像,一幅现藏于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另一幅则被颐和园收藏,在2008年由荷兰团队修复完成并展出。华士于1906年在巴黎展出的慈禧肖像明显比卡尔的这幅更生动,也更接近慈禧的真实年龄。但那幅画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主要原因还是慈禧的容貌得益于卡尔的画像,在那时已不再成迷。
历史是吊诡的,艺术价值也是相对的。画家和艺术史家眼里的三流作品,在谭家珊眼里却是一流的。在她看来,卡尔和华士的作品没有高低之分,只有问题大小之别。
“(修复师)感兴趣的是(画的)问题,而不是艺术家。”谭家珊说。
2015年4月,当我走进修复中心常年保持21摄氏度和50%湿度的仓库,在属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那一间看到这幅修复完毕的慈禧画像时,它正侧卧在一个带有滑轮的支架上。塑料遮盖的背后是百年前的油彩,在谭家珊团队的努力下,最大程度地恢复了鲜艳的光泽。
画像中的慈禧端坐在雕刻精美的椅子上,身穿绣了水仙花和“寿”字的黄色长袍,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背后的屏风上装饰着喙中含着八个佛教象征符号的凤凰。画面中的慈禧,实际已六十九岁,但看起来至少年轻二十岁。

————————
参考材料:
1、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De Ling, 1911
2、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Katherine Carl, 1905
3、Letters From China, Sarah Conger, 1909
4、《慈禧太后画像》驻台始末小记,赖贞仪,《历史文物》,2011.11
5、“Conservation of an oil portrait of the Empress Tze His of China,”Jia-Sun Tsang
6、Freer and Sackler Gallery, David Hogge
7、促成“庚子赔款”办学的五位关键人物,《文史博览》,2008.10
————————
冷书杰,自由撰稿人。
除了注明来源者,其他所有图片都来自于: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