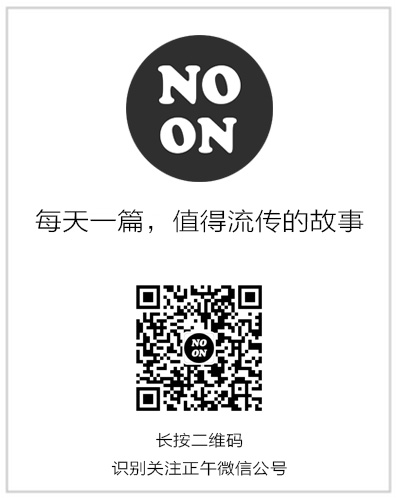一
清晨五点,方廷荣起床了。这天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一年一度的上海电影节开票,他要赶上五点半的地铁,到14公里以外的上海影城排队买票。
这阵子正是上海多雨的时节,已经入夏,但天气并不很热,潮湿的空气里有一丝凉意。方廷荣换上红色格子的长袖衬衫,米其色粗布长裤,黑色单皮鞋已经擦了干净放在门口。他喝了一杯豆浆,吃了一个水煮蛋,然后把热好的鸡蛋饼揣进皮包里。通常,他是以这副装扮出现在虹口区曲阳路一家六楼的舞厅。跳上两个小时的快步华尔兹,每天的生活就此展开。自从2004年他从南京路的永安百货退休以后,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超过10年。
他看了看时间,地铁迟了六分钟,直到六点半,他才到达。上海影城排队买票的队伍像一条龙似的沿着走廊拐了个弯,他站在队伍里,拿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上海电影节《市民手册》。 按照惯例,他首先关注的是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电影。今年,他的功课没有做足,有些吃不准看哪部电影,他把目光移向队伍的前方,搜寻了一会儿,他跳过年轻时髦的小女生——一般这些小女生是为了追日本影星来的,继续搜寻,有个男生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觉得这个人和他气质相仿,应该对电影很有些观点的。于是他走上前,和男生主动交流了起来,他问:“你买了哪几部,给我看看?”
排队是件拼体力的事情。来排队的多是年轻人,有的前一天夜里就在门口守着了。一串年轻面孔把方廷荣衬托得很显眼。他身材干瘦,衣服像飘在身上一样,他的头发已经泛白稀疏,朝后梳拢,露出光亮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金属边框眼镜。这样的形象招揽了不少搭讪聊天的记者,当被人问起“高寿”的时候,他便委婉地回答道:“高寿谈不上,我是小弟弟,刚刚拿老年卡。”他乐于和人交谈,以此排遣等票的时间。站累了,他便跑到影城大厅的星巴克坐一会儿,看队伍走动了,又插进队伍里继续排。
影城大厅里人流来来往往,不时有人认出他来。从1993年上海第一届电影节开始,方廷荣就没有缺席过。那时,他还在永安百货,担任了工会组织的影评小组组长,电影节的票都是单位买好的。退休后,每年六月他就自己起早排队买票,而且一定要去上海影城——就像看足球赛一定得看主场。他的退休金不多,维持正常生活不成问题,其他开支就得省着点,“讲分寸”地花。早年,电影节上午的票最便宜,20块钱,他就专挑早上八点半场次的电影。现在票价提升,再也找不到20块的电影。他得综合影片价值、可看性、排片时间等各方面,进行衡量。
将近10点钟,方廷荣终于排进了大厅。他看到一个熟人,是上海影城以前的影院经理王佳彦,人称“老王”。他向老王打了个招呼:“老王,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铁杆影迷哦。”老王回答:“我们是老朋友了。”老王比方廷荣小7岁,从90年代末开始负责上海电影节的排片工作。今年,300多部影展影片、1000多场放映的排片工作全靠他一个人完成。他阅片量大得惊人,干了多年影城经理,早年还做过电影发行,对电影市场有着敏锐而准确的判断。排片是一种需要经验和时间积累的艺术,直到今天,老王的位置仍无人能取代。
直到电影节开票,老王的排片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和方廷荣一样,每年开票的那个早上,老王必定出现在影城大厅,像赴一场早已确定的约会。
二
方廷荣和电影的缘分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就注定的。1944年,他出生在上海百乐门舞厅对面一个狭窄的弄堂里,父亲是香港海关警署署长,家庭条件属于中上阶层。7岁那年,姨妈带他去百乐门红都戏院看了人生中第一场电影《劳来与哈代》,是部美国喜剧片。当看到劳来一口吞下一个蛋的时候,他被逗得哈哈大笑。
1959年,方廷荣进入沪西中学读书,家里已经没落。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属于黑六类。那时,有句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家庭出身高过一切,他连团员都入不了。即便如此,电影倒从来没断过。班里组织学习小组,八个同学组成一组,平时放学一起做功课交流学习,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组里一个同学是解放军家属,凭军属证能去学校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看内部电影。方廷荣因此跟着同学看了很多在外面看不到的片子,他最喜欢《百万英镑》、《科伦上尉》和《好兵帅克》,看完电影他们几个就跑到某个同学的家里,在客厅长长的西餐桌上,扮演电影里面的角色,他喜欢扮结巴,“电影里面有个人喝醉了有点结巴,就像这样,啵啵啵......”
由于出身不好,他高考没被录取,正巧,永安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聘高中生,他应聘去永安公司做起了“练习生”。1949年前,永安是上海有名的百货公司,由郭氏家族创办。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很有商业头脑,在他的管理下,永安经营着全世界的百货,英国的毛料、法国的香水……是当时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货大楼的装修讲究,电风扇、木地板,柜台材料统一进口英国,连一面镜子都是从英国运来。1956年,全中国的资本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永安变成“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郭琳爽成为了红色资本家、全国人大代表。
1962年,方廷荣进入永安公司。他在二楼的纺织品柜台卖呢绒,全羊毛,布料上标着两个硕大的英文单词“ALL WOOL”。他是买不起这些的,做练习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7块8毛4,挨上两年,工资才能升到36块,这个水平就差不多到顶了,“我们有句口号叫36块万岁,就是年年都是36块,从来没变过。”
他是家里的男丁,肩负着补贴家用的义务,每个月只留了5块钱零花,看电影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花销。他按照票价给附近的电影院分类:大光明、和平、大上海、新华电影院属于头轮电影院,新片在这几家首轮放映,票价也贵,一张票3毛5;江宁电影院属于二轮电影院,票价便宜一些,2毛一张;三轮电影院是他的心头好,一家位于商场旮旯角、只有一个厅的大武电影院,放的片子比较旧,比头轮影院晚一个多月,因此票价也最便宜,一张只需8分钱。大武的条件非常简陋,人走在地板上,地板嘎吱嘎吱直响,板凳是可以翻转的硬木板凳,但他并不介意。在那儿他看过《三毛流浪记》,也看过《复活》。
不久,“文革”爆发。戏院里,除了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但有一类电影他十分中意。红旗电影院经常放五分钱一张票的“世界见闻”,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尽管地域经过了选择,大多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古巴这类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第三世界国家。那时,他非常失落,他是“反革命”的子女,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生怕被人揪辫子。电影成了他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他觉得“世界见闻”蛮好看。
“文革”期间,永安公司改名为东方红商厦,后来又改为第十百货商店。计划经济时代,公私合营的永安迅速被国营的百货公司甩到了身后,每年的销售量只能做到国营百货的三分之一。老板郭琳爽被红卫兵批斗抄家。有一天,方廷荣在食堂吃饭,看见郭琳爽正在哆哆嗦嗦地擦桌子,他悄悄走过去,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老板。他没敢叫他“郭老板”——他家也是遭迫害的对象,父亲正关在监牢里,他走近郭琳爽,低声唤了一声:“侬好呀。”

三
老王的父亲也是“文革”中被迫害死的。
老王爱电影并不偶然,他父亲叫王光彦,解放前就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曾担任电影《白毛女》的副导演,电影《赵一曼》的制片主任。1952年,王光彦导演了一部批判封建迷信思想的电影《一贯害人道》。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要在上海发展科教电影,把老王的父亲调到上海从事科教电影工作。“文革”中,王光彦的作品被贬为毒草,他是所谓的黑线人物,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老王免不了受到牵连。1969年,老王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北大荒,当了八年农民。老王去了就没指望回去。农村里放露天电影,他站在雪地里看《地道战》、《地雷战》。对他来说,电影都是好看的。他想,那就扎根一辈子,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文革”接近尾声,老王作为知青病退回到上海。日子并没有好起来,他在上海人造板厂做缝纫机桌面的木板,搬木头烤木头,工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抗过来。80年代,“文革”中的受害者一一平冤昭雪,老王终于被落实政策,调到电影系统工作。
老王曾经也有过导演梦,像他父亲那样。1978年,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报考北影的还有陈凯歌、张艺谋,不料学校通知他年龄不符合标准——他岁数超过了,老王导演梦就此破碎。他痛苦了好几天,老王回头想,“否则的话我就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了。”
“文革”结束后,方廷荣也被落实政策,终于从二楼的柜台升到了六楼的办公室,干起了行政工作。他的生活像从石子路驶入了柏油路,一切变得平稳又顺畅。80年代,商业部要在全国12个沿海城市各搞一个华联商厦,条件是承办的百货大楼必须可供顾客“吃、住、玩”。永安百货底子硬,六层大楼里老早就有了餐厅部、旅社和舞厅,甚至还有一间可容纳五六百人看电影的剧场。1988年,永安百货翻修。这栋大楼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永安百货改建为华联商厦。
那是方廷荣一生中“最好的时候”。他头脑灵活,长袖善舞,除了干些行政工作,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做了华联商厦工会影评小组的组长。他文字功力一般,但嘴皮子功夫好,公关能力强,很快和黄浦区的各家影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春风得意——全中国电影院最多的是上海,全上海电影院最多的是黄浦区,黄浦区电影院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南京路。大光明、和平、大上海、黄埔剧场、浙江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业务组组长都和他“熟得不得了”。很快,人脉资源给他的电影事业带来了另一个小高潮。
华联商厦开张没多久,淮海路的妇女用品商店并到方廷荣的单位。正值妇女用品商店开张十周年,商店搞了一个“美在妇女”的电影填字比赛。参赛者要在给定的字形表格里填50个电影名称,这些电影相互衔接,最后刚好能嵌入到“美在妇女”这个字形表格中。大多数影迷填到40个左右之后,就填不下去了。有的影片实在生僻,非专业人士很难想到,方廷荣跑到各个电影院的业务组那去,让业务组的组长帮他查片名。填完以后,他不急着交,等到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他托熟人把表格直接递交到评委的桌面上。比赛结果公布,他果然拿了一等奖。奖金很可观,一千块。
199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正式举办。美国导演奥立弗·斯通作为电影节的国际评委来到上海,他还带来了电影《刺杀肯尼迪》。影片一共放了两场,第一场在上海影城,放完以后引起很大轰动。第二场排在和平影院的上午,黄牛票已经炒到了45块的高价。方廷荣要上班,没办法去看。但他非常激动,托和平影院的业务组组长帮他争取一个斯通的签名。后来,这个签名是他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四
退休以后,方廷荣的生活非常忙碌。他早上五点起床,去舞厅跳舞,之后一般去看一场电影,电影看完以后他要在12点之前赶到上海音乐厅听“音乐午餐”:从12点到1点,10块钱一张票,大多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或者学生演奏。音乐会结束后,他一般看下午场的电影,或是听苏州评弹。等到了五点钟,外孙女放学,他去接她回家,一天的行程结束。
我陪他看过一场上午场的电影。他看电影几乎不花钱,都是些稀奇古怪、十块钱就能看一场电影的放映厅,有的干脆就是免费。那天,他领我去静安区文化中心的一个放映厅。走在路上,方廷荣不停地称赞文化中心的放映员选片水平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他选片基本上自己也看过,他是一个gentleman。”
很快,我在放映厅见到了方廷荣口中的“gentleman”。放映厅面积不大,但是只布置了24个座位,显得很宽敞,墙壁上挂了一台液晶电视,用来播放影片。电视旁边站立着一位中年男子,正在调适电视,他趿着拖鞋,穿着T恤短裤,戴了一副眼镜。他非常低调,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叫老陆吧。”
老陆看上去有些年纪,但是做放映员,才是最近的事。几年前,为了照应年迈的父母,他从法国回到上海,一开始从事公益行业,服务残疾人。他觉得国内的公益不够纯粹,让他很疲倦。两个月前,他来到静安文化中心放电影——电影是他一直热爱的艺术,也算老本行了。
之前文化中心也搞放映,但放得随意,文化局给的IPTV片库里随便挑一部就放了。老陆来了以后,他一个一个问来看电影的人:“你们喜欢看什么?”了解观众的需求以后,他把影展分成了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主要是新电影展播,下午场则是百年奥斯卡回眸,按照年份、或者影片获奖时间一部一部开始放,那天下午他放的是马龙白兰度主演的《欲望号街车》。
这部片子在放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故,由于片源年代久远,放到一半字幕跳掉了,一位老人跑出去找老陆,很着急:“字幕跳掉了调得出来伐?”老陆把影片停掉重新设置,中间这个过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所有人静静等待字幕,他们告诉老陆:“太好看了。”那一刹那,老陆非常感动:“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你用一千句一万句也没法表达的。”
老陆年轻时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在80年代,在美影厂工作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上影厂、美影厂被外界归类为文艺单位,老陆被称作”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最大的特权就是有“过路片”看。每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会在某个时段搞一次电影巡演,许多好的电影路过上海,被称为“过路片”。位于黄浦区宁波路的新光影院就是指定播放“过路片”的地方,只有电影厂的职工才有资格进去看。有一次,《出租车司机》“路过”上海,当时这部片被划定为色情片。老陆进影厅要过两道门,先出示工作证进第一道,再出示电影票,才能进影厅。
老陆看了很多片子。那时候电影资源紧俏,他不懂得挑片,一部片子过来不管喜不喜欢看,先看了再说,“有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他曾经看了一部苏联片子《托尔斯泰》,几乎没有情节,打了一个暗灯光,紧跟着一个逆光,托尔斯泰坐着开始讲故事,全片接近三个小时,他看到最后快崩溃了。
和老王一样,老陆也曾有过一个导演梦。他和当时同在美影厂工作的娄烨是好朋友,俩人一起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每天清晨,他们抱着大部头的电影理论书籍到静安公园复习。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加速,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气息从深圳飘到了上海。那时美影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过100块,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动画产业劳动力的廉价,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太平洋动画公司,并用几十倍的薪酬把美影厂的职工挖到了深圳。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一个月数千元的工资几乎是不可拒绝的诱惑。老陆没抵挡住,他放弃了导演系的考试,奔赴南方。在深圳的那段时间,他像疯了一样,没日没夜地画,画得猛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三四万。在深圳,他觉得离西方世界更近了,居民楼的房顶上竖立着一根根鱼骨头形状的天线,这些天线用来接收香港的卫星信号。虽然隔着海关,但是深圳人很容易看到国外的资讯。老陆就在HBO上看了许多美国大片。
在深圳呆了几年,老陆出国了。再回国后,老陆成为了电影放映员,方廷荣口中的gentleman。

五
电影节上,方廷荣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放映厅的人。他有自己的礼节。
他觉得电影一定要看到最后一个字幕结束,才算看完。有的电影放完,会放一些拍摄花絮,“幕后戏才是好看的东西,走掉的,不懂,不会看电影。”还有,他认为电影放完是应该鼓掌的,尤其是看完好电影。可是他很少看到人鼓掌,这让他很泄气,”国际上的电影节放映观众都是鼓掌鼓到最后才走的。”
在上海电影节开票的那个上午,方廷荣向老王炫耀:“我最了不起的就是第一届,奥立弗·斯通来上海放《刺杀肯尼迪》,他在台本上的亲笔签名我有的,全中国全上海就我这一家的。”老王在旁呵呵笑:“我也有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方廷荣。他打开书桌下面的第二层抽屉,取出一把钥匙,再打开第一层抽屉,然后取出一本黑色皮套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我凑近看,原来是他的看片记录。
我翻到去年上海电影节的看片记录,他这样记录:“6/14 ,纯真年代,美,可,70;6/16,窈窕舞妓,日,好,80;6/18,教父2,美,可,70。”他解释说,每看一部片子,他都要记上一笔,注明国家,再打分数。最高100分,65分算差劲,70分尚可,75算好,偶尔能到80分的,那是少之又少。
方廷荣说:“怎么评价一部电影?第一要素是可看性,包括音乐、画面、对白。《教父》是好片子吧?我为什么给第二部给得低,因为我看过第一部,第一部绝对好,应该是80分,第二部我给它分数就低下去了。哪部电影你一提到,脑子里马上有个镜头出来了,那一定是好电影。比如说,《简爱》,有镜头伐?两个人坐在树林里的凳子上讲话,马上有了吧?《简爱》肯定有85分。”
电影节开票的早上,方廷荣没有告诉老王,其实,他不仅仅有奥立弗·斯通的签名。去年奥立弗·斯通再次来到上海电影节——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拿到奖以后,斯通前往刚刚开张的上海电影博物馆参观,当时,方廷荣正巧也在。奥立弗·斯通身边环绕着人高马大的保安,但方廷荣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随手抓了一个男青年,把手上的相机递给他:“这是奥立弗·斯通,我待会跟他说话,你帮我照相。”他的身手顿时变得异常敏捷,完全不像一个退休已久的老人。保安还没发觉,他已经站在斯通面前,对他说:“奥立弗·斯通,我是你的铁杆粉丝。”他知道,这位美国导演根本听不懂他说些什么,重要的是,男青年在旁边“咔擦”,按下了快门。
“就像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一样,历史的瞬间被记录了下来。”方廷荣说。
————————————
文中“老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