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小宽 顾禾
编辑|董文璐
不同族群对重口味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对中国人最匪夷所思的重口味偏见是吃狗肉,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吃像大虫子似的海参;中国人也不理解西方人吃牛排,“切开一刀,里面还血淋淋的,怎么吃!”在张大卫拍摄的美食纪录片《Ugly Delicious》中,他们来到北京,街边有一家驴肉火烧,张大卫转头就跑,为什么会有人吃驴肉!
跟这个重口味的人间相比,吃什么都算不得重口味。无非是 “尝试” 二字,不能接受的,就一别两宽,能接受的,就上去走两步。人间孤独中,吃着一些有点儿怪异的食物,步履有点儿蹒跚,喝一口酒,再假装坚强着往前走。
广州,入海口处的重口盛宴
“广州人什么都吃”,这大抵已经是全国人民给这个地域贴的标签。都说广州人喜爱食物的原汁原味,在无辣不欢的人眼里,粤菜的口味着实算“小清新”。然而,广州人的“重口”,不在于浓烈之味,而在于取食—上天下地入海,还真没什么是广州人不敢拿进厨房的,如此一来,确实算对得上“什么都吃” 的名号。
有趣的是,广州地处入海口,更如同一个“大胃王”,开放性的地域特征更使得其源源不断地接纳多种多样的食材,而你若想一探究竟,跟闫涛去广州的南番顺地区觅食,瞧瞧广州人日常餐桌上的重口盛宴。

不食虫,不做“老广”
说起吃昆虫这件事,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云南或东南亚地区,但怎么能落下广州,不过虽然他们也喜爱虫子,不同的是,他们更喜欢往水里找。
很多 “老广” 都有着这样的童年回忆: 儿时跟爸妈逛菜市场,总能看到白白的水箱里,一群黑黑的 “蟑螂” 游得正欢。小孩子当然视它们为 “童年噩梦”,懂吃的大人们却“门清儿”,这些“水蟑螂”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水蟑螂”即龙虱,是经典的粤式昆虫饮食中的一员。龙虱当中,金边的尤为珍贵,不仅肉质肥美,独特的蛋白质香味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和龙虱不同,桂花蝉从名字上就沾上了点风雅的情调,由于它体内的香腺能释放类似薄荷和桂皮的味道,桂花蝉还经常被用来炼制精油。“吃完桂花蝉,手上好一阵都是香的”,这形容不仅指桂花蝉给人味觉上的美味,也代表了它身上的独特香气。
龙虱和桂花蝉,一个在夏天,一个在秋天,正是它们的最佳品尝季节。掰掉腿,撕去翅膀,露出饱满的 “肉体”,用嘴一吸,便是满嘴喷香。除去它们略显“重口” 的外表,其中的风味让所有老广折服,不愧是“我很丑,但我很美味”。

越是美味,越是藏在肮脏处
动物内脏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吃惯河鲜与海鲜的广州人,自然是不会放过鱼内脏的,鱼肠就是其中之一。
与猪下水类似,鱼肠自然也干净不到哪里去。“鱼肠我老婆是会做,但她一般都不乐意做,清洗起来太麻烦啦”,闫涛打趣道。即便是这样,鱼肠那独特的油脂甘甜还是让无数人魂牵梦绕,再麻烦也要吃。
热锅中放入鱼肠,丰富的油脂瞬间在锅内迸发,发出诱人的滋滋声响。鱼肠染上诱人的焦黄色泽后,加入吸油的瘦物,既中和了大部分之时,正是取马鲚鱼春的最佳时期。趁新鲜取下的油腻,又让鱼肠的滋味变得更加饱满。其实,“鱼春”并晒干,用炭火微微炙烤,便是一道完美越是脏的食材,越是考验人。细心地清洗,精心地搭配,才能让食材完美蜕变。

除了鱼肠,“鱼春”也是极品。其实 “鱼春” 就是粤语中 “鱼卵” 的说法。说到鱼卵,就避不开因其鱼肚中一年都有鱼子而得名的“多春鱼”。很多人爱吃酥炸多春鱼,爱那香脆的鱼肉和绵软的鱼春结合时的奇妙口感与香气。
即便 “鱼春” 本身就已经足够美味,挑剔的广州人更绝,不仅吃鱼春,更要吃鱼身上更鲜美的部分—鱼子。像马鲚鱼,虽肉质鲜美,但它在上岸脱水后便会迅速死去,于是,深谙其道的广州食客便懂得: 每年春天,马鲚鱼回游产卵的下酒菜。
还有一种,就是鲫鱼春了。相比之下,鲫鱼倒是广州人平日里也常能吃到的河鲜之一。鲫鱼肉质十分鲜甜软嫩,然而尾部处的鱼刺多且细长,让很多人苦不堪言。清蒸鲫鱼的旁边,往往会伴上一条嫩黄色的鱼春,让人眼前一亮。鲫鱼春同样适合清蒸,简单地蘸上酱油,便能把它的鲜甜发挥到极致。怕挑鱼刺的朋友,肯定会转而爱上鲫鱼春这一“精华所在”。

世事无绝对,游水黄眉头
要吃点好的,有时候是要费点力气的,广州人对吃,可以说有足够的耐心,如费工夫地清洗鱼肠,或者油炸已经很细的鱼骨,又或者为一口极鲜的“黄眉头”,跑到河边。
闫涛就是一个对 “黄眉头” 的新鲜度尤其执着的人,市里当然也能吃到,但味道是远不能比的。
黄眉头,鲜到能让人 “掉眉毛” 的极品,同时也极其脆弱,上水后很快就会死去。因此,只有在广州海边地区,尤其珠江入海口处,才能吃到最新鲜的。新鲜黄眉头如此珍贵,由此也延伸出了一鱼三吃的做法,可谓把它的 “鱼生” 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世事无绝对,游水黄眉头”,闫涛的一句感慨,虽说饱含对黄眉头也能远吃的希望,但要吃到最美味的它,还是到河边去吧!
其实,在闫涛和一众 “老广” 的眼中,口味重不重,其实并不等同于特定的味道或食材,它更像是一个人在饮食上的价值选择。

“在我们广州,重口味也算是一种情趣吧。”如闫涛所言,小小的一条鱼,在广州人的烹饪下,变成了全身都是 “宝” 的佳肴,这种对食材极致的发掘和利用,其实也是对 “吃” 这件事的追求和情趣。但万事都有原则,即使广州人,对重口味这件事也是有原则的——不碰珍稀保护动物,保持对所获之物的感恩,不浪费可用资源,让好食材碰到好手艺,得到的才是真美食。
厦门,偏爱惊世“臭、怪、奇”
素冠以小清新头衔的厦门,在饮食文化上,如果翻开 “黑暗料理” 的篇章,定令人大跌眼镜—竟还有这番重口和说不出滋味的偏好! 他们对 “臭” 万般着迷: 开辟出将鱿鱼搅碎了腌制成咸腥酱料,用以拌饭的吃法;他们对 “怪” 情有独钟: 生长于滩涂,扭曲黝黑的一种蠕虫,是地方传统小吃的原料;你以为你吃的海鲜够多,在吃 “龟足” 的厦门人眼里,根本排不上号...... 厦门用其 “犯规” 一般惊人的食材挖掘能力,倒也呈现给人独树一帜的美味视角。

爱吃“臭味儿”,流淌在厦门人骨髓里
如果说在厦门有一条地道饮食文化链,那么,了解 “蚵仔煎” 和“沙茶面”等小食,只能处于入了门,只有当你说出“土笋冻”“墨鱼膏”“鬼爪螺”...... 此类令外人摸不着头脑的食物,才算真正走进了厦门饮食文化的骨髓。
区别一个人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人员,仅仅看他如何 “挑嘴” 就行。吃什么这件事,是经过一座城市中世代祖辈千锤百炼,不怪不食,越丑越贵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在厦门也是如此。就像“海鲜大叔”,陈葆谦这位“老江湖”,祖辈渔民,骨子里就继承着对海底生物的热爱,在吃口上尤其追究本土历史,就连《风味人间》节目组都知道,去厦门吃,得跟着这位懂行人。
陈葆谦告诉我们,厦门人很有意思,大抵是看过尝过太多海鲜,味觉上的 “鲜” 已不足为奇,非得捣鼓些非本地居民不轻易接受的当地风味儿,比如“臭”。

墨鱼膏
从味觉下手,他们对自己就够狠,如 “墨鱼膏” 这道特色小食,就足以诠释这一怪癖,光是操作起来就相当“浓墨重彩”: 将鱿鱼的内脏掏出,洗净剁碎,用盐腌制,常温发酵几天,待味道渐渐酝酿成熟,便用油炒,熬制成酱。
黑乎乎的墨鱼膏,品相上类似鱼露、虾油,闻起来又腥又臭,据说制作它的人别人远远见到就要躲,气味熏人,一米之内都无法让人近身。但墨鱼膏这东西,越臭则意味着品质越佳,厦门本地人都爱到不行,大街小巷,寻常人家的饭桌上,只见大家捧一碗鸡公碗,打一碗米饭,拌上几筷墨鱼膏,大口吃饭,满嘴臭,一脸香。
所以说,谁说爱吃臭味儿可是一座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脉络,外行人可看不懂,但吃的人沉醉其中。

不怪不食,越丑越贵
爱吃臭味这种事儿,其实放在全国也不算太稀奇,以海鲜数量和品类见长的厦门,历代发展渔业,祖辈都是渔民的陈葆谦就尤爱海鲜市场。厦门的海鲜市场,渔港码头,总有一位举着相机拍摄鱼类、海鲜的大叔,那便是陈葆谦本人了,但即便是他,如果在海鲜市场看到 “一种长相奇特、“似手又似足” 的海鲜,乍一看好像不能吃,“想吃又不知该如何烹饪”的食材,他也是要一顿猛按快门,忍不住跟老板询问攀谈几句的。

那便是“龟足”,即便在厦门,它也是无比珍贵的稀有食材,价格更是能上二百元左右一斤。龟足,俗名佛手贝、观音掌。或许只有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才曾听闻,人们喜欢吃龟足,倒也不是全吃,吃的是龟足的柄部,一般是白灼或爆炒,当作下酒小菜,把外面的硬皮剥掉,里面是一块白肉。“这块肉口感紧实,有点像蟹肉味,吃时就像嗑瓜子一样。”
你说这厦门饮食怪不怪? 人人都说海鲜海鲜讲究 “不鲜不食”,以及“不时不食”,而在陈葆谦口中的厦门,则多了一份“不怪不食,越丑越贵” 的怪相。

此笋非彼笋,“小肉丁”显本土味儿
从陈葆谦儿时记事起,家乡就有一种著名的风味小吃 “土笋冻”,过了重阳节,天气渐凉,传统做法中“土笋” 中的胶质自然凝结,人们就开始制作这一种玲珑剔透,味道甘冽鲜的吃食。
不就是笋吗? 如何和重口味搭边? 但许多人拿到一碗有着 15~18 条 “土笋” 的“小肉丁”,硬是下不了口。“土笋”学名叫可口革囊星虫,是一种蠕虫,它们一般生长在江河入海处,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过熬煮,虫体带有的胶质溶入水中,冷却后可凝固。
只能说厦门人能挖掘这样食材,真是绝。作为地方传统小吃,甚至都无从考证是具体从哪一年开始吃,只据《闽小记》载:“予在闽常食土笋冻,味甚鲜异,但闻生于海滨,形似蚯蚓,即沙巽也。” 这便更增加了 “土笋冻” 的神秘色彩。

即使制作土笋冻需要费一番功夫,也无法泯灭福建人民对它的热爱,做 “土笋冻”,传统的做法是先把土笋泡在水里,让它吐出肚里的泥浆,清洗黝黑的“土笋” 变白嫩,再将它们用五六十斤的石碾子,来回碾压暴浆去内脏,洗净。最后,加水在锅里猛火旺烧,只需滚沸两三分钟就成。经过泡、洗、压、洗、煮五道工序,最后,加入模具中冷却成型。
掌握了方法,包括陈葆谦在内的许多厦门人,都自己做自己爱吃的土笋冻,秘诀就是要挑选鲜活肥硕、生长周期满 18 个月的土笋,满满放够 18 条虫子,做完放入冰箱,就可以制造出冰冰凉凉的口感,一口下去,爽嫩脆滑。
海港之城厦门,饮食和文化多元而开放,人们心态开放、生活安逸,你能有多享受一碗土笋冻,就能看出你能有多融入厦门本土饮食。
云滇,异食异味,生食炸虫
据说,当一个汉族人兴致勃勃坐到 “老昆明” 的饭席上,少有能不皱眉的,倒不是对方怠慢你,相反,更多的可能是过于盛情,端上桌的菜色道道“档次”!
如: 拌了蒜汁、花椒、薄荷等作料的白旺 (生羊血),清晨刚从市集上“片” 下来的新鲜生猪皮,价格竟比猪肉贵,再瞧那碟鲜亮、明艳的蘸水,倘若飘着生肉糜你也不必咋舌,那可正是云南最地道的“剁生”。倘若你赶在 3 月底到 4 月初的好时候到访,主人家必然是要端上一盘黑白相间,像芝麻粒一般的当季新鲜佳肴—“蚂蚁蛋”,那可绝对是把你当宾上座的珍馐佳肴。

上天入地都是菜,自然教育就是“吃”
当汉族人的自然启蒙还是小花小草时,云南人从呱呱坠地就开始接触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动植物,而这些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树上爬的,大多数都是能入口的。
刚满 2 岁的小娃娃,就在自家的火塘边吃生皮,时不时再来几口“不见天”,不停咂吧嘴;七八岁的皮大王则会去抓蜂蛹,要不就是成群结队去木柴加工厂,从树皮上找柴虫,用水龙头冲干净,直接就往嘴里送,味道甜甜的,男生女生都吃,仅仅就是嘴馋图好玩。

70 后记忆中的小时候,街边小贩挑着担子卖的谷雀、蚂蚱,2 分钱一碗,还有现在是珍稀动物的抗浪鱼,当年也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食材,如今都绝迹了。
90 年代的傣族村,天刚一亮,村子的姑娘们扛着背篓,拿着小叉子,去田野、河谷附近采青苔,抓泥鳅、鳝鱼,再往树上找找蚂蚁,田间找找蚂蚱、田鸡,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回自家厨房切切煮煮,摆一桌好菜。
对开大卡车的司机来说,最提神的可不是喝咖啡,而是吃“臭屁虫”,学名荔枝椿象,把翅膀撕掉后,再把屁股去掉,炸透之后吃起来特别香!

大千世界,无所不“蘸”
有句俗话这样说:“ 云南第一怪,蘸水人人爱。” 说起香,什么都比不上蘸水让人欲罢不能!
听老一辈说,曾经蘸水的配料可有五六十种之多,现在少了,但三四十种也还是有的。蘸水的配制讲究,什么味型搭配什么样的佐料,该按什么比例、什么数量来放,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秘制做法。

举几个例子: 生皮蘸的酱,通常用梅子醋、梅子酱,低温发酵,提供酸味,另有蒜、香菜、宽叶韭菜根、薄荷、青柠檬。
辣味就更广泛了,煳辣子蘸水无人不晓,把被烤过的辣椒,也叫烧辣椒,用柴火灰焐热,手搓一把木姜子撒下去,舀两勺自家特制的豆油,浇点麻油、撒点葱末和已经炒香的芝麻粒,一起倒入碗里就成了蘸水,那叫一个香辣浓郁。
蘸水又分干的和湿的,有的则都放,撒上新鲜的花椒也是常有的事儿,特别提味儿。香料中,最特别的要数香薷粉,棕色粉末,干了以后磨成粉,味道奇香,特别香,带有薄荷清凉的味道,很是开胃。

吃米线时,最精华的总是那份浓汁,浓汁是把牛苦肠水用锅熬成,然后再把剁成细末的生牛肉加上剁细的韭菜、缅芫荽、香柳、布芽、小米辣搅拌在一起,再把涮涮辣在里面一涮,把米线、熟牛肉片、熟牛肚片在浓汁中蘸过一下就可食用,吃起来十分爽口。
这些不可思议的食物取材和饮食习惯,在我们看来如同天方夜谭,却早已深入云南民间的传统和骨髓,果不其然,食物是可以区分一个族群的,不禁感慨云南地区的游牧民族竟开辟出这番生猛的饮食作风,而民族的大融合,更接地气的一种方式或许是: 打开这本绮丽又真实的美食经,“滇”覆你的味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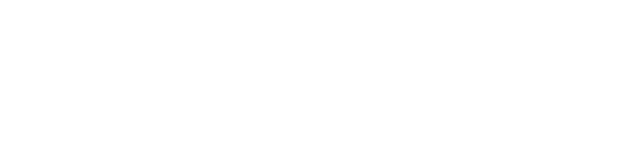
口味轻重,视觉说了并不算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用此形容传统云南菜,恰如其分,据 “敢于胡乱” 回忆,当年在云南拍摄取材《风味人间》,摄影师们将机器瞄准早市上白族人杀猪,现切生皮,就地食用的镜头,五大三粗的汉子竟个个惊得说不出话来。但对当地人来说,这可是好东西,“无生皮不成宴”,日常饭桌上少了它,更是喝不下酒,吃不下饭。
其实,“生皮”不生。“敢于胡乱”曾拿着温度计测量过三四次,往刚切的猪皮底下一验,竟也有 60~65°C 左右的烹饪温度,这番论证,摄影师们也就放心吃起来: 鲜嫩、滑爽,且味美甘甜、不带半点腥味,但凡放开胆儿吃过一次,就会沉迷 “生皮” 所呈现的猪肉最原始的美味。
巡游到大理、保山、德宏这一代,你会发现人们都爱吃生皮,又叫 “火烧猪”,之所以不生,是已经用火“低温慢烤” 过的了。由于早年缺乏丰富物资,锅碗瓢盆等炊具,白族人杀猪,先用稻草点火,将其全身的皮子烧透,去毛,刮洗干净。用稻草烤过后,整头猪呈金黄色,皮子及其以下两三寸的部位,实际上已经被烤熟了。

秉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人们取下猪皮后,又是一番开肚解剖,趁新鲜将火烧猪肉的“不见天”(肚底肉、后腿肉)、肺、肝、肚等部位分切成薄片或丝状,便就又有了腌牛蹄、白菜叶包生猪肝、凉拌猪肺等等汉族人口中的“重口味”,云南人心中的风味佳肴。
如此看来,很多时候,“重口味”来自于视觉冲击,更源自“不了解”,一旦你深入悉知地方的物产体系,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烹饪方法,你便也就能点头接受。
本文内容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摄影:陈超/采访
美术编辑:默菲
场地鸣谢:广州一方渔家 广州四桂堡
厦门上青本港海鲜厦门阿德土笋冻昆明翠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