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8年,我20岁那年,分配到了油田的勘探处,和一百多人集结,从七里镇(甘肃敦煌以西七公里的戈壁滩上的一个石油小镇)出发,经冷湖去花土沟。破旧的客车像毛毛虫一样,在柴达木盆地笔直的公路上蠕动。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不仅人缺氧,连车也跑不动。那是我第一次去花土沟,看到油砂山林立的井架,还真有一番激动,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憧憬。
在距离花土沟50公里的昆仑山下,很多节野营房围成的一个大院子,我们安营扎寨。
我被分配给一位叫李福的师傅当徒弟。第一次见到师傅时,他30来岁,人很好;满脸胡须,刮胡刀刮过后下巴呈铁青色;说话很慢,音调也低;但干起活来很利索,力气很大,憋足劲能抱起一个装满机油的大铁桶。
我对石油勘探一知半解,闲暇时间李福师傅把石油勘探的流程反复给我讲了很多遍。
我从事的钻井是勘探的一个环节,开着背载钻井机的车辆,前往指定的测线井位打井。打井分深井和浅井,深井要二三十米,浅井只有四五米。开始我对一切都好奇,跟着师傅学了一个星期后,慢慢地就能上手操作钻机打井。地层好的地方很好打井,一支烟没抽完就能打完一口井,再挪个地方打第二口。遇到岩石层,就不好打井了,干一天下来,都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测线有长有短,长的几十公里,短的几公里,每隔十米打一口井,多的时候一天要打一千多口井。一个多月后,我渐渐适应了钻井重体力工作,手指骨节开始变粗,饭量也变大了,每天干不了两小时,肚子就饿,盼着炊事班的人送饭来。饿的时候就想,当炊事员多好啊!
业余时间很无聊,队上的师傅们打麻将三缺一,我被叫去凑数,打放炮自摸都5块的推倒和。他们都是麻将精,打过两三次,我就把身上的钱输得一分不剩了。
野外每个月工资加补贴300元,钻工是重体力活定量发粮票52斤,扣除吃饭和喝酒的钱,发到手没多少。没有钱的时候,就到管理员那里赊账,结果有一个月发工资,管理员说我的欠账太多,要倒贴钱给他。一看账单,全是欠酒记录。那会儿身体好,每晚都要喝一斤白酒才罢休,是我酒量最大的时期。




临近收工,队里电台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设备和野营房不得搬迁,原地封存,留人看守,明年将在这个区域继续勘探。队长开始琢磨安排留守看家人员。他先发通知,没人回应;又到各个班组征求了一圈意见,也没人吭声。在野外干了半年,大家都想早点回家。
我很好奇,就从李福师傅那里打听,“看家”是个什么情况?他说看家就是留人在营地守护设备,免得被破坏或丢失。他说他就想看家,可以挣到一大笔钱。可是,他又说,出工前才从老家找了个女人结婚,女人还在基地等着呢。
看家到底能挣多少钱?我开始盘算,在野外每月工资300元,看家定额4人,单位允许一人值守,从当年9月到第二年3月,一共7个月,可以挣到8400元,都快接近万元户了。在这个诱惑下,我找到了队长报名看家,他立马同意了。
我琢磨着,挣到这笔大钱后,就可以买台相机,到南方去旅游。可第二天早上,队长把我叫到队部,东拉西扯地问我,家里什么情况,是不是失恋了,为什么要求看家。我说想挣钱去旅游。他说想了一夜,让我这样的小伙子看家,一个人在野外七八个月,寂寞难熬,实在是太残忍了。谁看家都行,反正不同意我。
我沮丧了两天,后来听说,李福师傅要留下来看家,队上将安排一辆车,把他“新婚”的女人接来陪他。
施工结束了,队里封存所有设备。我用铁板给师傅焊了一个大方罐,用来装七八个月的生活用水。大方罐焊得很漂亮,得到了队长的夸奖。这是我业余学电焊后的第一件作品。食堂把剩余的几袋面粉和一点蔬菜都留给了师傅,我把几本书也留给了他。
临别前,我们互相挥挥手,百十号人就全部撤离了营地。
回到七里镇基地一周后,队上才有车把他“新婚”的女人送上去。送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师傅的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感觉她眼神里还有一丝媚态,怎么也不能将她与那体格粗壮、脸庞丑陋的师傅联系到一起。我们这些单身小伙都很羡慕师傅。
轮休的日子无所事事,天天喝酒打牌,但时不时就会想起师傅。好多天过去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年昆仑山下了很大的雪,不知道他和他的女人在野外过得怎么样?
开春后,接到了集结出工的消息。从七里镇出发,颠簸一整天,傍晚到营地。见到师傅时,几乎认不出他了。他两眼充满血丝,头发胡须长长的,像原始人。在高原上孤独地待了近两百天,语言功能退化了。我问他这七八个月日子怎么过的,他木讷的嘴唇哆嗦一会说:“挺好的!”我问他师娘呢?他扭头不回答。又追问了几遍,他低声说:“来了一个多月,就跑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师娘跑了与我有关。我给师傅焊的那个水罐,罐底是漏的,不到一个月,一罐水就全漏光了。两口子吃水,只能到十几里外的东沟里去背。下雪后,就一直靠化雪水用了。
营地方圆几十里都是无人区。有人说,师傅与他新婚的妻子,在野外第一个星期,干柴烈火,都没有顾上穿衣服。第二个星期开始,两人便大眼瞪小眼,不停地争吵起来。
一个多月后,师娘跑了。听说她一个人从昆仑山下的营地往北走了60里路,到国道上,搭便车,回西宁附近的老家了。之后,师娘再没回来,这些年师傅一直是一个人过。
想起师傅,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2
野外搞勘探,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不过,勘探队员野外经验超级丰富,就没有想不出的办法。他们有句口头禅:“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假如要参加美国电视里的“荒野求生”栏目,一定比他们强得多。
柴达木盆地经过几十年勘探,好找油的地方早已让前辈干完了,剩余的就是啃骨头了,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沼泽,遇到沼泽地区还要分季节去干,只有到冬天,地表结冰硬化才能进得去。但到了花土沟一带的盐湖地区,即使天气再冷,湖水也冻不住,勘探队员就要想出各种办法打井放线放炮。在尕斯库勒湖附近施工,看似平坦的湖面下藏着盐穴,最深的有几十米。制造浮船也不好干,车辆陷进去是常事。后来单位买来部队淘汰的几辆坦克,作为勘探作业用车。在湖边浅滩还行,畅通无阻,肆意横行,往纵深前进,一辆坦克就掉进了盐穴出不来,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在柴达木东部的达布逊湖施工,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辆拉大线的卡车,路过盐湖附近的低洼路,以前天天都从这里经过也没事,但出事这次,车头刚进去就下沉。车厢上的人都迅速跳车逃生。驾驶员努力想把车开出来,加油冲了几次,错过逃生时间,一起沉入盐湖。现场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束手无策。后来勘探队想把人和车打捞出来,尝试多次都没成功。几个月后,油田请了青岛的海军潜水员,才把牺牲的驾驶员遗体弄上来,遗体已经被饱和盐水浸泡成人体标本了。
有些地方,冬季无法施工,夏季也不是没有危险。2005年5月13号,距花土沟东南60公里叫大乌斯的地方,就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野外勘探伤亡事故。当天上午还是晴空万里,气温20摄氏度左右,出工的勘探队员多数衣着单薄。下午6点左右,西边突然出现一片黑云,一场特大暴风雨雪悄然向他们袭来,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0摄氏度,瞬间地面积雪,能见度不到10米。经过全力营救,最终,在这场暴风雪灾害中,还是有15名勘探队员被冻死。
勘探队员献身戈壁,这不是第一次。柴达木西部有个地方叫“南八仙”。1955年,有八位南方来的女勘探队员,在冷湖以东的风蚀残丘中跋涉测量,返回途中,遭遇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迷失方向,长眠于此。后来为了纪念她们,石油人把这里叫作“南八仙”。
我当勘探队员的时期,生产生活条件都比早年改善多了。日常遇到一点困难,爱絮叨的老师傅,总爱拿勘探传统故事来教育我,说我不能吃苦。
有一次,在花土沟西南部,昆仑山下叫阿拉尔的地方施工。那里是一片湿地。进入草滩,一种细小的黑蚊子,多的时候一团一团地围着人转圈。那蚊子别看小,但毒性很大,脸上咬一口,几分钟就会肿一大片。用手拍死蚊子,会闻到一股草腥味,仔细观察,那些蚊子原来是落在芨芨草叶子上,吸附叶子里的汁液。最痛苦的是去拉屎,屁股被咬得全是包。我们一到来,吃素的蚊子便开荤了。后来工友们总结出经验,拉屎的时候要先在旁边点一堆火再脱裤子;要不跑就到一个山头上去拉,那里风大,蚊子都吹跑了。
我同营房的师兄郭月平,是个讲究人,每次拉屎都要去很高的山头上,说那里风更大,太远就开钻机车去。有一次不小心把车开翻了。那可是德国进口的MAN车,73万美元一台买来的,马力巨大,320马力。海湾战争时,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过美国兵用MAN车运输坦克。
西南部的工区任务结束了,勘探队沿昆仑山整体往东搬迁。新工区工作量不大,队上把女工都安排回基地轮休了。
搬迁的时候,发现队上有一间野营房是原来设计的洗澡间,一直当库房使用。向队长提出来,他安排腾空物资,让电工给收拾一番,洗澡间准备好了。
队上清一色的男人,几个月没洗澡了,我们毫无顾忌地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穿越小队大院,到后面去洗澡。淋浴水量大,温度自己调,很舒服。可没洗几分钟,就发现不对头,水里像是有针扎的感觉,一阵有一阵没有。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漏电,突然就严重了,几个人瞬间就被电打得连滚带爬地摔出洗澡间。
过后,再也没人去洗澡了,那间洗澡间又变成了库房。
终于完工,队长要求我们3部钻机车都开回七里镇维修。回家路上有种凯旋的感觉,你追我赶。冲出荒野,眼尖的队友发现,离公路不远的地上有一具穿羊皮大衣的尸体。看他脸的状态,已经死亡多日。怎么会死在这里?也不像凶杀。师傅有经验,说这是昆仑山里的淘金客,可能晚上迷路了,其实就差两公里就走到公路了,可他看不见路。我们报了案,公安来得很快,打开尸体衣服,在胸口找到一个用羊皮缝制的口袋,倒在地上,全是一坨坨不规则的黄金。
公安分析说,这人估计偷了金矿上同伙的金子跑出来的。公安拿着金子走了,叫我们把这个人就地给埋掉。
这事处理完,耽误时间太多,车跑到晚上,过老茫崖后,有一辆车发动机一阵异响,趴窝了。天漆黑漆黑的,怎么也发动不着,都说是白天遇到那个尸体太倒霉了。大家经过讨论,决定留下一人看车,等待救援,其他人挤上别的车先回。大家开始还都争着表态要留下看车,我没有说话;可后来,我刚说了一句“我留下”,有人就说“好”,没人再吭声了。只好认了,谁让我在里面最年轻呢?
我在车上等待了3天,没吃没喝;等见到救援的人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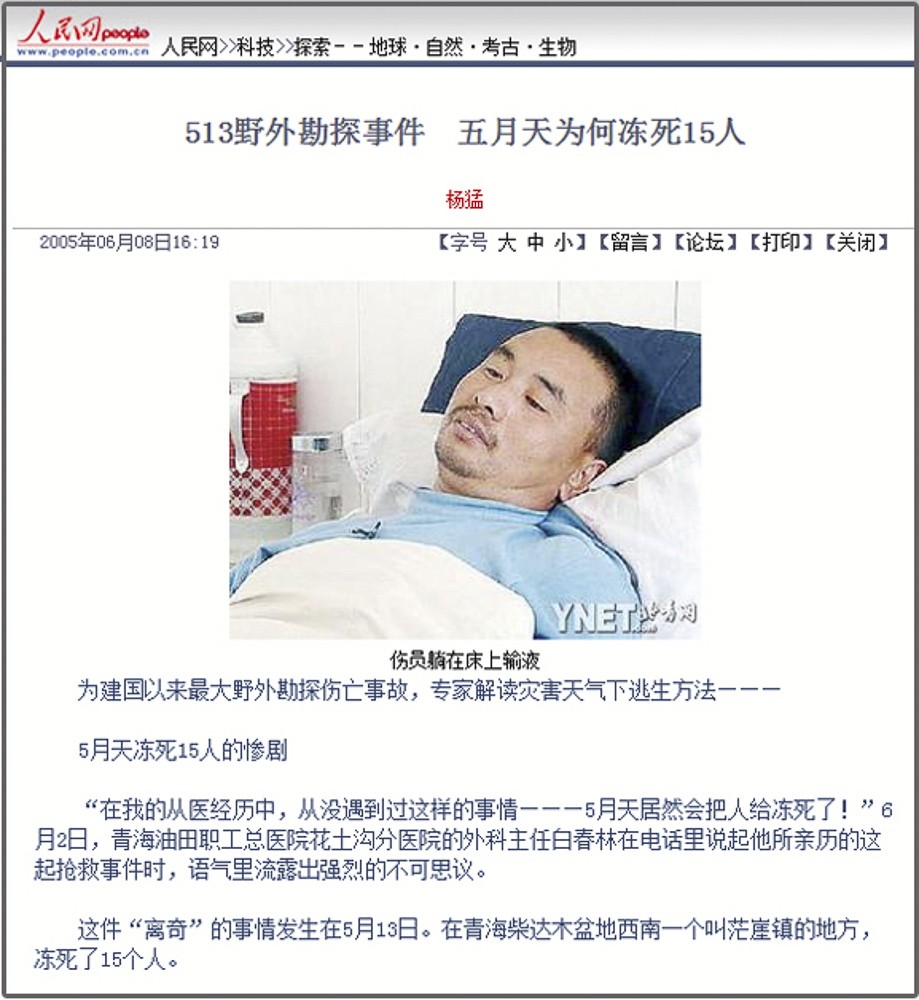



3
昆仑山下,有个叫切克里克的地方,在这里勘探施工最有乐趣。
昆仑山北坡地貌是按海拔变化阶梯分布,顶部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寸草不生的石头荒山,往下有沙丘、戈壁、草场、沼泽。别看这里气候恶劣,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野牦牛、野驴、野马在戈壁奔跑,藏羚羊、黄羊灵巧地跳跃,狼、狐狸在悄悄地追寻猎物,地面上的小型动物也很活跃,荒漠与草地间有旱獭、野兔,更小的有一种跳鼠,像澳大利亚袋鼠的缩微版,非常可爱。我经常捉跳鼠玩,夜间车灯一照,跳鼠就立定不动了。
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切克里克的平缓地带,有一部分是牧场,居住着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叫巴特尔。刚到这片工区时,我出于好奇,去过他的毡房。巴特尔汉语很差,只能做最简单的交流。他从来也没有走出过这片草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记得他用磕磕巴巴的汉语问我:“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我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把毛主席当成了一个领导人职位。
勘探的地震测线要穿越巴特尔家的草场。他家有很多羊、牛、马和骆驼,常看到他骑着马在羊群附近遛跶,胸前挂着望远镜,背上挎着一杆枪,脸庞晒得黝黑。
一天下午,我们打完井返回营地的途中,遇到羊群。四周望去,巴特尔竟然不在。机会难得,想着逮上一只。于是停车去追羊,原本平静的羊群迅速逃离,在凸凹的草滩上跑得飞快。我们追了五六十米,在即将抓到的瞬间,前方土坑里突然冒出一个人,巴特尔站在那里,手里端着枪,对着我们。马上掉头往回跑,生怕他开枪,连滚带爬到车里,一溜烟就跑了。看来巴特尔的枪不仅是防野兽,也防人。
巴特尔比较淳朴,就算头一天我们袭击过他的羊群,第二天去他的毡房,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热情地给我们倒奶茶喝。
有一次去打井途中,发现测线上卧着一匹黑马,一动不动。下车一看,原来这马的一条腿踩到勘探井,卡住了。一定是巴特尔家的马。我们又拉又拽,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决定离开的时候,我看见马在流泪,就坚持要用钢丝绳穿在马身下,再用钻机升降系统拉它出来。师傅却不同意,说这样弄,一下就把马撕裂了,马肉又不好吃,巴特尔不会在乎少一匹马。
我被劝着上车就走了。可从那一刻,脑子里就一直是那匹流着眼泪的马,卧在那里无法动弹。
第二天,去打井的路线变了,想去看那匹马,就得绕很远。
第三天,打井的路线离那匹马就更远了。
第四天,继续央求师傅去看马,软磨硬泡,他同意了。
绕道十几公里,来到马的身旁时,我惊呆了。它还活着,急速地喘着气。它两只眼睛没有了,黑黑的两个窟窿,血迹未干。天空中盘旋着几只秃鹫。
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看马了。
老测线上井打完了,等待新的任务,在营地休息的日子寂寞得要发疯。没事就喝酒。喝多了,满脑子都是那匹身陷困境的马。夜里,我常跑到野营房外的戈壁上,对着天空一会儿放声大喊,一会儿高歌,一会儿狂笑,有人说我精神出了毛病,已经快疯了。队长说这是患了典型的戈壁综合症,“气候干燥,生活枯燥,心情烦躁”,要回到七里镇,看看绿色,看看女人,自然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爆炸班组告急,说测线上连接炸药的雷管线有一百米被拔掉了。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难道是巴特尔发现有一匹马丢了,以为被我们逮住吃了,故意报复我们?
队长安排一些人去巴特尔家交涉一下,要求好好解释,不能发生冲突,只要以后别再破坏就行。我们一伙20多人,在司机小魏师傅的带领下,大小车开了6辆,团团围住了巴特尔的毡房。在毡房里发现了丢失的雷管线。巴特尔的女人和孩子以为废弃了,才拔去准备编织成绳使用。我们人多,把巴特尔给吓唬住了,小魏师傅气势很凶,告诉他破坏石油勘探是犯罪。看巴特尔听不明白,小魏就开始计算破坏测线施工的成本,七算八算,要巴特尔把所有羊、马、牛、骆驼全都赔给我们也不够。巴特尔还是不太明白,小魏师傅说要不就报政府处理,公安要抓人的,接着用手摆出个手枪形状,对着巴特尔的头“啪!啪!”两下,这时巴特尔似乎明白了,用蒙语给女人孩子说了一通,女人孩子都吓傻了。过了一会儿,巴特尔结结巴巴地问我们要怎么办?小魏师傅一副放松的表情,说那就不报政府了,只需要赔20只羊、5头牛就可以了。巴特尔又用蒙语与他的女人叨咕了几句,就同意了。
之后队上伙食改善,吃过一次羊肉。听说队长不同意要巴特尔家的赔偿,只弄来了两只羊就完事了。没几天,发现巴特尔的毡房搬家了,离我们的营地又远了四五公里。
多年过去,想起那个说话不利索的巴特尔,就有一种内疚感。

4
到了1990年代,不论是七里镇还是花土沟,天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最明显是单位的澡堂子、理发室没有了,被桑拿、洗头屋代替了,一间间卡拉OK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街上出没着成群的穿白鞋白裤、画着红红嘴唇的女孩,都是外来的小姐。
这一年出工的路上,我们目睹了一起离奇的车祸。一辆地方单位运石棉的货车跑在我们车的前面,突然撞倒了路边的电线杆,车翻到沟里,从挡风玻璃里竟然飞出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女人的裸体,可惜碰撞得很惨,肚子被划开,肠子都出来了,奄奄一息。我们立即组织营救。队医只能进行简单包扎,由事故方的其他车辆,将裸体女孩和货车司机送往就近的冷湖医院抢救,后来就不知死活了。
营救完,才知道,这辆车的司机长期跑长途,在大戈壁上实在寂寞,就包养了一个小姐陪着跑车。夏天车里太热,两人索性就脱光了衣服,走走停停,忙忙碌碌。可能是司机太累了,撞上电线杆出了事故。车报废了,但车上的录音机没有碰坏。我们离开时,录音机里面还在用很大的音量,反复地播放着齐秦的歌曲:“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这大概是我在公路上遇到的最浪漫的司机,其实很羡慕他。
油田要提高产能,加大勘探的投入。我们的任务也加重了,队上调来很多人,也有分来实习的大学生、技校生。女人也增加了不少,她们主要干放线、收线的工作,看似劳动强度不高,但一天在测线上来来去去,少的要走十几公里,多的时候要走几十公里。
单身汉们天天都惦记着那些女人,打听谁没结婚,谁没对象。长相好的,一定出野外之前早就有主了。在那个缺少女人的野外环境,真是“车过当金山,母猪赛貂蝉”。单身汉每个人心里,都暗暗有了自己相中的目标。
钻井班的年轻人没多久就与几个女技校生混熟了,总邀请小英(化名)和晓丽(化名)来我们营房。晓丽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甘肃人,鹅蛋脸,长辫子,性格开朗。她爱笑,也爱讲笑话,还能表演独角戏。她还有个本事,各路方言都能说,特别是上海普通话说得非常地道,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
有一次晓丽讲了一段上海话后,我问她怎么学来的,她说母亲是上海崇明人。我追问,上海人怎么跑到西北来了?她扭头岔开话题,不说这事了。
没过几天,我们营房有人从基地弄来一台放像机和十几盘录像带,都是一些三级片,每天都扎一大堆人看录像。小英和晓丽过来一看是这些录像,很不好意思,就再也不来串门了。
我们通常看到晚上12点左右,队上的发电机关闭停电,录像带卡在放像机里取不出来,便不再管它。早上6点营地发电,我们还在睡觉,电视机来电了,屏幕里面的角色就开始劳作了。那些录像带没有看完,队长就知道了,怕影响不好,就把放像机没收了。
录像看不了啦,大家又想起那俩女孩。一打听才知道,晓丽被一个老工人搞定,谈上恋爱了。
夜里,睡不着觉,我把暗自喜欢小英的想法,告诉了同屋工友。他给我分析了一下,说小英长得太差,配不上我。而且她有严重的心脏病,这种病就不能结婚,不然新婚之夜圆房的时候,她会“嗝”地一下死掉。假如不死,生孩子的时候一定会死。我真相信了。
可过了几年,我听说同屋的工友与小英结婚了,娃也生出来了。
女人在野外工作,想方便的时候最不方便。遇到这种情况,几个姐妹会事先说好,几个人围成一个圈,轮流在圈里方便。后来我们教会她们开钻机车,开到两三百米外去解决。
这年的野外施工,还发生了一件女工受伤的事件。测线经过一大片盐碱地,到了中午,烈日当头,气温很高。放线车的水箱开锅了,冒着很大的白烟。遇到这种情况,车不能熄火,熄火发动机就会报废,只能低转速,及时补水。
由于距离太远,车载电台联系不上救援,只能自己想办法,携带的饮用水剩余不多,全加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采用土办法,以尿代水。男人们轮流往水箱里撒尿。在高温环境下,人都快脱水了,没多少尿。于是动员女工来撒尿,开始她们不同意,后来有个女工带头爬上车,脱下裤子对着水箱口就尿。接下来,女工们只好全都排队上去尿。可就在一个女工尿的时候,突然意外出现了,发动机转速提高,水循环加速,水箱口冲出一股滚烫的热流,直刺向撒尿的女工。一声惨叫,摔了下来,女人的下面被烫了,据说烫得很严重,全部被烫烂掉,而且那个部位不好痊愈。这个女工叫葛青梅,老家在西宁郊区的农村,1984年招工来到勘探队当放线工,到被烫伤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很长一段时间,队上都有人时不时地责骂那个驾驶员,说是他故意脚踩了油门,还有人想揍他。他却辩解说,是发动机不稳定,自动加油的。
烫伤的女工被送到西宁治疗,就再也没有回来。想起她,都心痛。



好不容易熬到施工结束,回到七里镇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那一年的冬休季,过得最无聊。
我整天与青海籍的工友幺蛋混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他大我很多,听说他与一个重庆的女人有过短暂婚史,他有个恶习,喝多了总爱打老婆。重庆女人是出名的厉害,反倒把他一顿暴打,然后就离婚了。
每天中午在家吃完饭,就会听到口哨声,那是幺蛋在呼唤我,天天如此。出勘探处大院的西门,我们通常是先进入右手的一家台球室,打三局斯诺克,赌注就是谁输下午喝酒谁买单。
决出胜负,便去北面的一条商业街。跟着幺蛋逛那些小店,什么东西也不买,没有目的地瞎逛。时间长了,发现幺蛋逛小店的规律。他带我进的小店,大多都是有姿色的女人开的。
老贸易公司左侧有一家非常小的凉皮店。一个脸上永远没有表情的老太太忙碌着,别看她没有表情,但做的芥末凉皮特别好吃。不知道哪一天,店里来了一个端盘子的长辫子姑娘。幺蛋判断,这姑娘不像是本地的,本地就没有这样的肤色,白白嫩嫩的脸上泛着微微的腮红,五官极为精致,特别是那双眼睛,会说话。
自从发现长辫子姑娘后,我们每天都要光顾凉皮店,总是直钩钩地盯着她看,找借口搭讪。她总是转头莞尔一笑,便躲藏在面无表情的老太太身后。
我们总以最慢的速度吃完凉皮,才把位子让给别人。
之后便去商业街东头,是维吾尔族人买买提卖烤羊肉的摊子。在这里会遇到很多勘探队的工友,一毛钱一串烤羊肉,八毛钱一瓶啤酒,总喝得没完没了。
到了傍晚,我与幺蛋告别还在喝酒的工友,按原路返回,路过凉皮店要看一眼长辫子姑娘,再进入老贸易公司。幺蛋每次都要到日用品的柜台,买一支牙膏、一块香皂才离开。
我问幺蛋,你家吃牙膏香皂呀,天天都买?其实我明白,他想泡日用品柜台的营业员。那女人总穿一身红底黑格子上衣,齐耳短发(当地俗称剪发头),脸庞清秀,嘴角微微上翘,上嘴唇右侧有一颗美人痣,是老贸易公司里最漂亮的女人。
记不清这样的日子过了多少天,幺蛋到底买了多少牙膏香皂。
突然有几天,幺蛋不再来找我了。我在家也憋得慌,就按老路线出去。到了买买提烤羊肉摊,一打听才知道,几天前的晚上幺蛋喝多后,拿刀捅伤了人,被公安抓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一个人在街上遛跶,也去吃芥末凉皮,挑逗长辫子姑娘,但她从不与我说话,只是一笑。我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爱上她了,她从不理我;我甚至怀疑自己长相太丑,配不上她。
老贸易公司也每天都去,学着幺蛋买牙膏香皂,只不过与那剪发头没有说过多余的一句话。有一次她把牙膏香皂递给我,手碰触到她指尖的时候,感觉一阵发麻,出了商场就兴奋得跑起来。
我妈看到家里一堆牙膏香皂,问我买这些到底想干啥?
元旦的前一天,我还是挂念着长辫子,去了凉皮店,她却不在。憋不住,向没有表情的老太太打听,她没有吭声。我问长辫子为什么不理我,老太太冷冷地嘣出两个字:“哑巴!”
走在大街上,第一次体验到失恋的味道。
5
在荒原上一天到晚找石油,时间久了,没了开始的新鲜和激情,有了麻木。也为自己的前途发愁,重体力的钻井工作又脏又累,看不到希望,度日如年。我曾在营房里每天都写下一笔,写了很多的正字来记录日子,就像在坐牢。
我发现队上的拉水车司机岗位最好,不仅不累,还可以出入小队,每天去花土沟拉一次水,比其他人自由多了,让我羡慕不已。
我们队水罐车司机何桂新,外号“何大癞子”。他脸黑,光头,一米八的个头,从来没见他笑过。他酷似电影《少林寺》里的秃鹰,比秃鹰还要生猛,我第一次见到他,都不敢与他直视。他平时衣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天天抽的都是好烟,有酒喝有肉吃,打起麻将,兜里摸出来的全是一沓沓的“大团结”,大家都弄不清楚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找理由向队长请过几次假,才在休息的时候搭上“何大癞子”的水车去花土沟。路上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一看竟然扔出了车窗外,兜里摸出一包好烟扔给我。我问他,怎么这么有钱,怎么挣来的?是卖车油箱里的柴油吗?他却一本正经地教育我:“公家的柴油能卖吗?再说就两个油箱,也装不了多少,能卖多少钱啊?想挣钱要靠动脑子。”接着问我想挣钱吗,我说当然想啊。“何大癞子”说,今天就给你找个挣钱机会。
没多久就到了花土沟,车七拐八拐来到北山下的水站。十来分钟,我们把一罐水就装满了。接下来他把车开出水站停在一边,拿出一个红色的记录本给我,他解释说,一会儿看到有油田以外的社会车辆来拉水,装水的时候,就去罚款。先要来行车证、驾驶证,进行登记,然后一辆车罚款1000元,500也行,多少都行,看你的了。
这时正好来了一辆外来施工队的车,我壮着胆子上前,问司机要来行车证、驾驶证,一一登记,问他有油田的装水水票吗,没有就罚款1000元!那个司机马上哀求我高抬贵手,说干了几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领到,穷得饭都快吃不上了。我说那就罚200。他翻出兜给我看,的确没有钱。我只好绷着脸,批评教育了一下,就把证件还给人家。
施工队的车装满水走了,“何大癞子”笑我不行,面太软,不心狠手辣怎么能挣钱。接下来看他的。又来了一辆烧砖场的车。他果然厉害,成功罚款人家600块,还算给了人家面子,那司机走的时候还不停地感谢他。
有了钱,“何大癞子”带着我去逛花土沟的商场。买了烟酒后,他请我去自由市场吃手抓羊肉。我一个劲地吹捧他有勇有谋。他说这是他来拉水第一次就发现的商机,罚过一次后,每次来都要罚两三个车才走。我问就不怕违法吗?他说外来花土沟油田搞建筑的、烧砖的、承包施工的队伍有百十来家,罚他们款,黑吃黑,永远不会有事。不过他不让我把这件事说出去,这个事我一直保密到现在。
我们队上的老工人,多数没什么文化,但他们有智慧,解决问题各有高招。另一位司机,小魏师傅,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反应灵敏,口才极好。几年前,地震队在盆地东部施工,离最近的城镇有200公里,小魏每天要开罐车去那里拉水。
有一天返程,天色已晚。路过盐湖,湖水涨潮把路淹了,车越走水越深,最后熄火走不动了。湖水涨势最严重时,小魏只能爬到车顶待着,饿了就喝罐里的水。挨过一夜,湖水退下一些,但仍然无法脱身。又饿又冷,小魏开始害怕,队上怎么就没人来救他呢?就这样又等了一天,小魏绝望了,估计自己难逃此劫。于是,他用记号笔在车身上写下遗言。遗言很多,车上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写满了。
然后,小魏弃车逃命。
经过层层汇报,各级领导知道了小魏失踪的事情,已经派出了很多人,分多路去找,但就是没有找到。最后,都惊动了省委书记,联系了空军,准备出动飞机找。
油田的电视台、报社也行动起来,报道寻找小魏的过程,还打算要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宣传部也在准备事迹材料,要是活着找到就树立成劳模,要是死了就追认为烈士。
第五天,水性好又年轻的小魏幸运地逃出被淹区域,走到了国道上,又幸运地遇到过路车,被拉到了医院。检查身体,什么事都没有。消息传开,领导放下心来,各路人马皆大欢喜。
湖水彻底下去了。小魏被安排和各级领导、电视台、报社、宣传部等一起去遇险现场,准备拍照、录像,要他在现场讲述如何保护国家财产并自救成功的惊险过程。
找到孤零零的水罐车,看到小魏在车身上写下的遗言,所有人都傻了。
小魏的“临终遗言”大致内容是:他要死了,一定要变成厉鬼,不放过对他见死不救的人,要先杀处长,再杀科长,最后杀队长,要把当官的全杀了,把这些人的老婆全部强奸。这些内容不但文字下流,而且配有低劣的图画,就像长途车站公共厕所里的那些留言一样。
小魏的事弄得各级领导哭笑不得。组织上也没有什么条例来处理他,不让他在开水罐车,换油罐车开了。

6
后来,工作调动,我离开了野外小队,最终辗转到了北京工作。有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开车走在繁灯闪烁、车水马龙的北三环上,收音机里传来汪峰的歌声:“我们在这欢笑/也在这儿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儿死去……”30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在昆仑山下朝夕相处的工友们,如今在哪里活着?你们还好吗?李福师傅是否在七里镇安度晚年?葛青梅的伤治好了吗?巴特尔和儿子还在切克里克放牧着牛羊吗?
—— 完——
题图为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的昆仑山尕斯湖 。摄影:姜鸿。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炯,1960年代末生于甘肃戈壁石油小镇,辗转于青海柴达木、上海、北京工作,学过绘画、电影,当过石油钻工,扛过摄像机,拍过纪录片,结交三教九流,能饮善讲,装着一肚子故事。现居北京,在一家行业媒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