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赛莱柯(Reinhart Koselleck)在审视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于1529年绘制的油画《亚历山大之战》(Alexanderschlacht)——又名《亚历山大大帝的伊苏斯战役》(The Battle of Alexander at Issus)——时写道,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时间意味着“期望”(expectations),因此这幅画作也被世人认为内含多种预兆。
而当德国诗人兼评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在卢浮宫看见这幅画时,这幅画已经问世接近三个世纪。施莱格尔被画中庞大的战斗场面和细致的人物描绘所打动,不过,在他看来,这幅油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只不过是一幅产生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艺术作品。正如科赛莱柯所言,三个世纪以来,“时间”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阿尔特多费尔绘制这幅战争场景油画的时代,普通人喧嚣忙乱的日常生活中交织着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希伯来文圣经中称之为“末世”[eschaton])的深深恐惧。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造成当时这种社会不安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而反基督者的存在,则是宗教方面无处不在的忧患。到了19世纪初,时间一词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不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日渐迫近,相反,它表示人类已经开始踏上从艾萨克·牛顿的“绝对、真实和数学的时间观”向今天的铯原子钟进化的漫长旅程。
自此,“时间”变成了一个线性的概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展示出的乌托邦前景也令整个社会为之振奋。为了促成这一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前景,大革命后的法国郑重其事地宣布:1792年将是新纪元的第一年,而且每个月份将被划分为3段时期或是以10天为一组;每一天的时间将被减少为10个小时,每小时则由100分钟组成……到了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曾经废除了一周七天制,代之以一周五天制,而且将一周中的五天命名为紫色日、蓝色日、黄色日、红色日和橙色日。2002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宣布,参考他自己的官方头衔“土库曼人的领袖”,那一年的一月将被命名为“土库曼巴希”(Turkmenbashi)。就这样,时间,以及我们的时钟和日历一次又一次屈从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的著作《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所指出,时间的民主化改变了十九世纪北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对与齐次性时间(homogeneous time)激增的关系的理解,而这种时间的民主化是通过各地城镇广场钟楼上的时钟以及后来普及的手表得以实现的。不过这一转变也为每个地区带来了挑战。仅在当时的德国就存在着五种时间标准,然后,普鲁士陆军元帅老海尔姆斯·冯·默尔克(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英勇地站了出来,说服议会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参照所设定的单一时间。正如历史学家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在她的著作《时间的全球变化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中所写,“废除因固守五种不同的时间标准而形成的地方主义(regionalism),既是一种建设国家的行为,也是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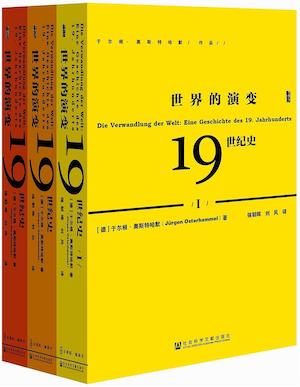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刘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1
除欧洲以外,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时间的设置上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对时间的含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在印度,形形色色的印度教天文历对时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划分方法,而且一种划分方法又会隐藏于另一种划分方法之中 ——这些时间单位包括从举行仪式时需要使用的微秒,到用于描述广阔无垠的宇宙和空间本身的宇宙时代纪元。对于美洲的拉科塔印第安人(Lakota Indians)来说,时间单位包含有根据月球运动制定的小时,而十月对于他们则是“落叶之月”(the Moon of the Falling Leaves),就像作家杰伊·格里菲思(Jay Griffiths)在她的《哔哔:换个角度看时间》(Pip Pip: A Sidewanys Look at Time)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在非洲国家布隆迪(Burundi),那些无法辨认人的面孔的漆黑夜晚被称为“你是谁?”之夜。在伊斯兰世界,人们一天中的第一次祷告总是开始于“当黎明的白线(光)与黑线(夜的黑色)明显区分开来的时候”。

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现在仍然保留有“牛儿踏尘时刻”(cow dust hour)这样的词,专指傍晚牛群结束放牧后,踏起漫天泥尘归来的那个令人惆怅的时分。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兼诗人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们微微移动的时刻/在最后可能出现的光亮中。”在日本人的传统中,一年被分为他们称作‘kō’的72个微季节(microseasons,对应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编注),每一个微季节由5天组成(三月的第16至第20天是“毛毛虫变身为美丽蝴蝶”的日子)。时间的渐变过程漫长得足以令我们难以忘记,但同时也短暂得足以提醒我们当下是多么的稍纵即逝——这是一种从人类的直觉、大自然的规律、圣经的训诫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之中诞生出来的时间概念。
到19世纪中叶,铁路这一革命性的成功使欧洲以及美国的各个距离遥远的地区连接了起来,这时情况也因此变得非常清楚:各地的城市和乡镇都遵循自己的一套时间标准。一个国家的地理面积越大,时间上的混乱程度就越严重。仅在当时的北美,就有至少75种时间标准。1884年,在苏格兰裔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的努力下,国际子午线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目的是尝试将当时世界各地混乱的时间标准合理化。会议确定了一个含有24个时区的“世界时间”,但是当时来自各国内部的政治阻力强大得令人震惊,人们反对在计时上做出任何改变,哪怕只是一些机械方面的改变。
在殖民主义时代,使时间标准化的努力与反殖民情绪以及联合新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挑战密不可分。1881年12月1日,孟买的英国总督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通告全体市民,自当日起,“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所有办公室将开始使用马德拉斯(Madras)时间,而且这一时间将作为以后在一切场合使用的官方时间。”众所周知的是,位于印度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德拉斯的时间比孟买的当地时间要早40分钟。通告发出后人们在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到底应该遵循哪一个地区的时间。孟买商会为此发起了一场运动,号召人们就当地大学的钟楼应该显示马德拉斯时间还是孟买时间举行一场公投。结果完全可以预见:孟买居民全都赞成让钟楼显示孟买时间。为了让当地人明白藐视政府命令的后果,弗格森政府以显示“非官方时间”为罪名,切断了钟楼夜间照明的资金来源。历史学家奥格尔在书中记录了这一段史实:1906年印度标准时间(Indian Standard Time)确立以后,又过了将近44年,孟买市政公司(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才最终同意放弃他们一直坚持使用的孟买当地时间,从而结束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记得的那场“时钟之战”。
到了20世纪中叶,时间的标准化成为后殖民时代国家建设的关键因素。以朝鲜为例,在过去的10年,该国曾将时间往前和往后调整过半个小时,以此显示其与韩国的或疏远或和解的关系变化。相比之下,国土疆域绵延超过3千公里的印度则一直坚定地抗拒在国内设定一个以上的时区,即使该国不同地区的日出时间相差已达到近两小时。经济学家毛利克·贾格纳尼(Maulik Jagnani)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睡眠不足和提早到校等原因,平均日落时间每延迟一个小时,儿童受教育的时间就会减少0.8年。他估计,如果从设定一个时区改为设定两个时区,人力资本收益(human capital gains)可以达到42亿美元左右。
在所有这些经由理性、历史和国家行为斡旋调和形成的混合的时间制中,人类对当下时刻的体验不断证明了对时间的过于简单的分类是错误的。正如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醒我们的:“你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千多年后,圣奥古斯丁用一种更加个性化、甚至接近忏悔的方式试图理解时间这一概念:他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当他试图去描述它时,他却发现时间无法描述。又一个千年过去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写道:“时间,它并不会流逝,它是慢慢滤透出去的。”在塞雷斯眼里,时间不再是一条自由流淌的涓涓细流,而是一种促凝剂,它的一部分渗透了人类头脑中的缝隙,成为了我们并不稳定的自我定位的一个见证,它使我们确信此刻并不同于其他时刻。同时时间也成为了我们内心恐惧的最大起因,它使我们认为自己注定要重复经历当下这一时刻。
为了重新找回不易捉摸的自我,偶尔我们也会追寻自由,而这种追寻仍然是证明我们依然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唯一途径。在内心深处,我们清楚知道,其余的一切最后都终将屈服于时间。
本文作者Keerthik Sasidharan是一位作家,现居纽约,作品曾在《印度教徒报》《商队报》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他的新书《达摩丛林》(The Dharma Forest)将于2019年出版。
(翻译:郑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