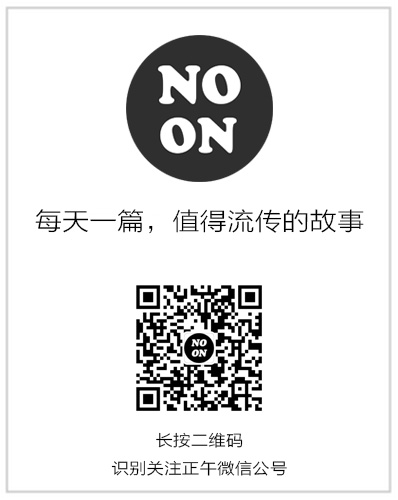时代的晚上
文|叶三
当一名慈祥的老交警告诉我,他可以把我六年没年检的驾照复活时,我心头涌上四个大字:“感谢祖国”。
那是2008年的七月,北京奥运的前夕。赶在各国友人和运动健将之前,我回到了北京。在这个我出生并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我发现,六年的分离让我手足无措。
这感觉有点像穿越千山万水回到久别的爱人身边,而对方已变心。熟悉的书店拆了,常去的小饭馆翻修成酒楼,大学附近暴土扬烟的大北窑现在是CBD,我离开那年爆红的肥皂剧里的小丫鬟,已成了一线明星。朋友们用很长时间向我解释轻轨和地铁的不同,而每一个聚会的地点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吃饭、买书、理发、打发时间……在故乡,我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外来者。
热闹非凡的街头,我经常盯着鲜红的交通灯,迈不出第一步。
那个夏天,我无所事事。父母的家狭小杂乱喧闹,外地的亲戚赶来北京“看奥运”,占据了我以前的房间。朋友们忙着自己的事,更多的朋友已失散。我长时间地蜷在沙发上,看那部啰嗦至极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在虚构的八十年代里寻找童年。看一会儿,睡了过去,又热醒——节俭的父母总是在我睡着时关掉空调。于是我便一次一次地在满头大汗中醒来,窗外蝉声一波波如敌人的强攻,黄昏永远不来。
似乎唯一熟悉的是北京夏天的触感,皮肤上一层刺痛的盐,又粘又咸,让人不耐。
然后我决定去买一辆车,来对付北京的交通和即将实行的单双号限行。当我将几摞人民币现金摆在4S店的收银台上时,迎面遇到收银员含义丰富的目光。而我该怎么开口解释,我目前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固定地址,没有工作,没有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去参观鸟巢的表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下了公交车走了四十分钟,“还没看到鸟巢啥样”,我笑了一会儿。那个时候,我正在平安大道上,听左小祖咒那首《平安大道的延伸》,“一个人感到悲伤就去平安大道;一个人感到失落就不要去平安大道。”这个坏蛋十分认真地唱道。车厢里的空气散发着崭新的皮革味道,车窗紧闭,空调运行良好。我从四惠出发,开到花园桥,再掉头开回来,在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人和强行并线的司机之间手忙脚乱——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与北京谋求一点亲近。
在平安大道还不叫平安大道的时候,这是我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的暑假,我每个下午走半个小时的路到后海去游泳。后海的水是碧绿的,伸直腿探下去能触到柔嫩的水草和淤泥。我出生在后海对面的北大医院。现在,九十多岁的祖母住在那里——没有什么病,只是老,各种器官心平气和地衰竭着。她在我出生的地方躺着等死。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很兴奋地问我期末是不是又考了双百,有没有评上三好学生。
平安大道和北京其他主干道一样,将一条车道画上了橘红分割线,这是“奥运专用线”,私家车开上去是会被罚款的。我被堵在官园桥的东侧,左边是空荡荡的专用线,右边是新修的灰砖墙街景,据说只修了临街的这一面。我摇下车窗,点燃一支烟,铺天盖地而来灼热的空气。我想着现在的后海叫荷花市场,晚上路过时,会看到水面上游船成群。我下意识地伸直腿,寻找柔嫩的触感。然后我踩到了油门。车轰鸣了一下,将我吓了一大跳。
那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来看奥运的亲戚们每天早出晚归。赶上傍晚下起雷阵雨,她们就把客厅的茶几搬开,将床上的竹凉席铺到地板上,团团围坐其上,每人持一汤勺,围攻中间切开的半个西瓜。房间里充满西瓜清甜的香味,和亲人们刚洗过澡的皮肤的味道,我有一点熏熏然的幸福感。雨水带着泥土气从窗口扫进来,将桌上放着的书打湿。那是我很早以前买的《基督山恩仇记》,已经被亲戚们带来的小孩撕掉了封皮,成了一篇没头没尾的故事。我坐在窗口读着,让雨打在身上。直到有人发现,将我赶开,把窗户关上。于是房间又闷热起来。亲人们睡去后,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分辨着不同的呼吸和呼噜声,无来由地觉得四面楚歌。
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我终于在北京的三环边租下了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只有房东留下的简单家具,非常之空。房东是一对公务员夫妇,他们在那个算得上不错的小区有好几套房子。“因为奥运”,他们说,“给你打了折扣啦。”房子在九层,他们还说,晚上也许能看到开幕式上的烟花。我谢过他们,关上门,把电脑放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将空调开到最大。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但最终没有成功。我只是想,这一年,我三十岁了。
那天签完租房合同,我慢慢地开车回家。天正在黑下来,北京在那个晚上很像我小时候的样子。车很少,人也很少,路上走着的人步履缓慢。那正是盛夏,我却有着雪就要降下的错觉,好像小时候睡眼惺忪地出门,被祖母拉着手,在清晨去取一瓶牛奶。我觉得很饿。
我走访了好几家灯火通明的饭馆。除了我,没有其他客人上门。饭馆都出奇地干净,散发着消毒水味儿,这让我想起我离开北京的那个冬天——那正是“非典”来袭的时候,饭馆里也没人。
带着红袖箍的老太太和老爷爷和厨师服务员坐在一起,盯着挂在墙上的大电视,看奥运会开幕。没有人肯做饭给我吃。我想起那天早些时候看过的一篇外媒的奥运报道,是刻薄的英国人写的,他说在奥运村上厕所,撒完尿,发现热情的志愿者在他身后为他扶着厕所的门。
后来我将车停在二环路辅路上,一座公共厕所的旁边。一个老大爷走过来端详了我一会儿,又走开了。我想着要不要去九层的空房子里看烟花,或者去父母家,和亲人们在一起。最终我哪里都没有去,就在那个公共厕所的旁边,我在车里吃买来的麦当劳,听着崔健,度过了那个举国欢庆的夜晚。我想起在远离北京的岁月中,我无数次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并不失落也没有悲伤。时隔多年再看,那种落落寡欢似乎也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矫情,一种无以名状、“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现在,故乡、家、亲人、祖国,这些词不再重要。那个夜晚对我而言也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只是我非常肯定,在那个夜晚,在北京,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听《时代的晚上》的人。

远离北京
文|谢丁
2008年7月25日,一辆装载磷肥的货船在瞿塘峡沉入长江。几秒钟内,它翻了个底朝天。近在咫尺的老关庙信号台,听到一声巨响。台长肖凤林站起来,从窗户往江上望去,只看见一面黑漆漆的船底,浮在江面上。
通过内线电话,肖凤林急忙通知附近的夔峡航道站。快艇赶到出事地点时,货船已经没影了,余下几个在江面漂浮的船员。他们救起了3个人,但还有3个人至今失踪。
没有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获救者自己也不清楚。在长江航道局内部,没有任何通告,也没有媒体报道。那艘有可能属于重庆云阳县的货船,瞬间在长江消失。
对于世代生活在长江三峡的人来说,翻船事故并不陌生。危险,就像江面上的水位一样起伏不定。在中国政府决定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从奉节至宜昌的航道,浅滩和急流随处可见。运输游客的客轮,因船体庞大,翻船的可能性很小。货船才是航道事故的主角。由于死伤人数不大,它们甚至不为外界所知。只有在当地,人们可以平静地讨论某起翻船事故,就像讨论谁家又死了一个年轻人。
政府想尽办法对付这条危险的航道。自1954年长江航道改革以来,航标站、信号台和绞滩站,是这条航道的守护者。父辈退休后,他们的子女接了班。根据体力和危险程度的分工不同,男人一般都去了绞滩站和航标站,女人最好的去处是信号台。
但三峡大坝正在改变这条航道。水位攀升,江面越来越宽阔和平静。以前的天然航道消失不见,人们现在称之为“库区航道”。满载着集装箱的货轮和庞大的滚装船径直穿越三峡,直抵重庆。政府撤掉了所有的绞滩站——现在不用机器绞滩,货船照样可以逆流而上。他们还撤掉了大部分信号台,留下的也已很少发布信号,大多只用来记录船舶流量。但老关庙信号台的职责和功能没有变化,它是长江三峡最后的真正信号台。
这个信号台是个八角亭式小洋楼,红白相间,地处悬崖峭壁,正对面就是雄伟壮观的夔门。站在信号台,往西望去,是宽阔的江面和崭新的奉节县城。往东,是狭窄的瞿塘峡入口。最远可以看见风箱峡,刚刚翻掉的货船就在那里出事。
“那艘船,不在信号台的控制范围之内。它不足够大,船上也没有配备高频对讲机。”肖凤林惋惜地对我说,“它一定是自己操作出了问题。”
老关庙信号台有一个男人,三个女人。台长肖凤林是其中最年轻的,工龄最短,拿钱最少,薪水700余元。
库区水位抬升之后, 原本在夔门斜对面的白帝城,成为一座孤岛。一条长江支流,将白帝城和老关庙信号台隔开。政府曾经修了一座大桥连接两地。可修好没多久,因为水位上升,又给炸了。现在,肖凤林要想上下班,都得坐船。每次上班,她至少得在这座无路可走的孤山停留10天。
那年八月,沉船事故不久,老关庙又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有只发了疯的猴子,咬伤了一名女游客。此后它经常显露出这种凶性,但从未被人抓到。
起初,肖凤林并不怕猴子,它们以前常从树上直接跳到信号台的阳台上,求点吃的。但咬人事件之后,她在办公室准备了一口袋石头,随时准备自卫。有一次,她在信号台门口碰见了那只发疯的猴子,他们互相盯了几秒钟。她大喊一声,猴子转瞬消失在丛林中。
无论在船上,还是水码头,女人都少得可怜。由于燃料上涨,时间又宝贵,每艘船都想赶紧通过。上下船舶有时为此在对讲机里吵来吵去,但他们很少会骂到信号台的女人。几年下来,声音听熟悉了。肖凤林经常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就知道是哪一艘货船又到了夔门。
依靠长江生存的人,仿佛自动构成一个大系统。肖凤林的哥哥是个开船的,每当他经过夔门,就想在这里多“罚站”一会儿。他们俩一年到头很少见面,哥哥的船从信号台下的长江驶过,妹妹仅能在对讲机里多问候几句。
在信号台工作,肖凤林最怕的是没有人说话。她把四个人分成两组,半月一轮换,每次值班都是两个人一起,有个说话的伴。信号台是24小时工作,缺不了人。但每到深夜,总得有人独自值完夜班,一个人去面对窗外黑漆漆的夔门和凛冽的江风。
在老关庙的第一年,她们仍然是手动挂信号。每次拉完绳子,她得跑到远处看看那个大铁皮箭头,是否正确地指明了航向。后来,政府装备了自动升降机。随着库区形成,政府在信号台旁边的悬崖竖立了一个超大液晶显示屏,希望能随时显示水位信息。但在三峡,现代化的设备看起来有点柔弱——由于缺乏电力,显示屏至今没动用。单位给信号台配备的柜式空调,如今也成了摆设。那年夏天,屋子里那个庞大的空调套着花边布料,无法启动。每个月,她们都收紧腰包,节省电费。
在信号台工作,嘴皮子不厉害,容易受人欺负。肖凤林那年30岁,虽然常年看不到其他人,但每天却在对讲机里和无数个开船的男人对话。稍不留神,也许就被那些男人开了玩笑。
每当水位变迁,夔门附近只容许一条船通过。信号台的职责就是控制来往船舶,有点类似城市里的交通警察。当她们在信号台挂上“上水信号”——一个朝上的铁皮大箭头,等候在峡内的船舶就赶紧逆流而上。如果箭头朝下,来自上流的船舶就可以进入瞿塘峡。
夔门是一个弯道,船舶往往只有走近了才能互相看到,而此时调头已经很困难,事故就容易发生。肖凤林常在对讲机里叫道:“你们就多等一会嘛,上面还有船没有入峡呢!”那船上的男人就调笑到:“还要等多久嘛?我们已经被罚站一个多小时了!”
有时,男人会突然在对讲机里笑道:“你的声音好甜噢!”
“好甜?那你就多听一会儿嘛!”
开船的男人,和信号台的女人一样,都是寂寞的人群。在高频对讲机里,大家能听到每个人说的话,吵的架,开的玩笑。
但这些都是偶尔得来的乐子。在无线电话台的工作日志上,肖凤林的生活看起来千篇一律,日子重复得像生了锈。她常写的段落是:
“轮船:老关庙信号台,我是上水xx918号,已到镜子岩,请问发什么信号?”
“信号台:上水xx918号,我台现在发的是上水信号。”
“轮船:好的,谢谢!”
“信号台:不用客气,慢慢走。”
当上下水都没有船舶等候时,信号台就突然空了下来。江风偶尔透过四面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听见夏日的蝉鸣,猴子在树丛中跳来跳去。平缓的江水不再有奔腾的咆哮声,夔门千年不变。
多年前,几乎每个暑假,我都会往返于奉节和宜昌之间这条危险的航道,每次途径夔门都很紧张。但奥运降临的那个夏天,当我登上老关庙信号台,却感到很平静。大约是因为人少,也可能是没有北京和电视的喧嚣。有好些时刻,我就倚在信号台的阳台上,肖凤林坐在桌前。对讲机也终于平静下来,天楼上没有挂出任何信号。屋子很安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阳台下,江面平稳如镜,我盯着货船沉没的方向,不知道水底下到底藏着什么。我只希望,下一场江风赶紧把这闷热吹散。

北京欢迎你
文|阿乙
2008年,天慢慢好起来了。这是我在帝京待的第四年。有时空气浮现出让人难受的颜色,灰茫茫的,和午睡后起来没有刷牙的感觉比较匹配。那时候人比较郁闷。租的房子也破破烂烂。有一天我下出租车时,不慎让车门碰到路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大姐。她歪倒在地,抚摸着膝盖,那里破了皮。我感到很懊丧,其一是我闯了这样的祸,其二是我需要去办的事只能停止。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将她的自行车推到附近的小卖部那里,和司机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她做了很多检查,最重要的是拍了片子。我不能说这就是抹点碘酒的事(虽然最后就是这样),检查就检查吧。只是后来她越来越多的亲友出主意,说是她本来要去南昌出差,火车票都买了,这下去不成了。我就给她报了。我说火车票给我吧,我看能不能在火车站退点钱,他们又不肯。我没再说什么。那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赌气,他们不知道我将自己许为傻逼,供他们宰割。
这件事使我难过了半年。我想到一位熟人对我的耻笑,你为什么不走掉,你不知道这后果么。
人类为什么喜欢尽情放大自己的损失呢。或者说,人类你为什么不小心小心再小心一点,为什么非得制造出这样一个害人害己的前因呢。你不能看看后视镜再开车门吗。这一年,有一日,我又坐出租车,忽然看见像撒满金币的路面上,有鸟的飞影。我不知道是它在追逐车,还是车在追逐它。我看见了小说里才有的蓝天:辉煌得就要碎裂,就像一枚宝贵瓷器。我差不多要失声痛哭(那是不可能的,也许从14岁起我就没好好哭过)。我跟司机说过瘾啊。他说是啊。
我当时租在大望路地铁附近,周围都是高贵的楼宇,奢侈的场所,譬如新光天地,传说王菲在这里购物。而我所租住的那个小区,破烂不堪,底商有三个门面左右是做垃圾中转站用的。当时装的还是玻璃窗户,每天要摇着铁把手开窗,透气。有一天来了一个工队,敲门,要对此窗户大动干戈。我打电话给房东,房东很吃惊,但是一听说这样的改造是免费的后,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工队就将玻璃窗改造为铝合金窗。以前是推开窗,现在是拉开铝合金窗,我在这简陋的一间房内看着外边哗哗作响的马路,想象着奥运会来到之时,国外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官员以及旅游者会看向我这里。啧啧,那里是铝合金窗户了,这一路上咱们就不曾看见有什么玻璃窗户的人家呀。我想到他们放下照相机这样说。
很多大爷很多奶奶在电视新闻里学英语,四处是北京欢迎你的友好气氛。这种友好是十分真挚的。这种真挚和一种久以积存无法抒发的自豪感有关。我记得当初申奥败给悉尼时,我还惦记着两件事,一是澳大利亚当地的华裔游行庆祝悉尼申办成功,二是有传说悉尼的准备工作让国际奥委会不太满意,因此北京顺理成章地成为接办城市。我想这是因为失败,人才会产生的幻觉。失恋也是这样。明明是一个姑娘不爱自己,然而我们总是去做很多关于奇迹的梦。不过随着2008奥运会终于到来,我一下过30岁了,忽然没有当初那样振奋了,是什么原因就不讲了。其中可能有一条是我懒了。但是人都是有仪式感的。在奥运会结束后,我还没有去一趟,因此我就应约和一位同样错过奥运会的海归朋友,一起去看了残奥会。我们坐在鸟巢里,感受着这人类史上的伟大建筑之一。鸟巢很好看。央视新大楼其实也好看(它一直被罩上大裤衩的污名,但是据建筑艺术家欧宁说,设计者的用意是表达出对摩天大楼文化的反抗,设计者是个左派,他设计出扭断摩天大楼的样子)。有时夜晚路过鸟巢,我会请师傅开慢点,好让我看一眼那灯火闪耀,像是红色济公帽的建筑物。旁边的水立方则丑得让人惊悚。颜色尤其丑陋。
我记得,在奥运会结束后很久,鸟巢都在开放,供游客参观。起先我以为这是场馆方在弥补经济方面的缺口,后来我想到,一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神迹毕竟好奇,愿意付费来这里拍一张照片,以炫于亲友。今天,距离里约奥运会也就一年工夫了。刘翔也退役了。有些人认为他是骗子,可能不应该这样说,他个人是可以承受失败的,但是很多人,或者说,一整个集体都不可以。虽然失败到来后,我们发现也没什么。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在一家体育杂志担任编辑。这家杂志是美国一本销量巨大的名刊(《SportsIllustrated》)的中文版,创刊于2006年。我加盟之时并不知道SI办公地就在纽约。1997年从警校毕业时,我去了一个叫洪一乡的山区,在那里,天亮得早,又黑得早,天黑后,人们缺乏开灯的理由,就那样睁着眼,看着化成无数个分子的黑夜。就像忍受一种刮刑。也就是在那,在我21岁之时,我立志愿,要沿着洪一、县城、省会、直辖市、沿海、首都的轨迹去纽约。这是一项报复性的志愿。立下就是为着不可完成。然而我在加盟这家体育杂志后,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在北京待了几年,在郑州、广州、上海也待过。现在,我离纽约那么近。不少同事都去纽约培训了,也许有天会轮到我。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理论上的机会一般让人耻笑。
我在这家杂志待得并不好。有时半个月我只能做1页到2页。我很难战胜自己在这里领工资的羞惭,因此只能用写作来打发那不可能不用掉的时间。也许有一天写作会让人们对我侧目一点呢,我这样做着梦。这是一个极其意外的开始。我在2015年5月,也就是前几个月,随团去了纽约书展,并在那里闹出门可罗雀的笑话,让单纯的老乡好一顿笑话。在那里我看见纽约和我想象的一样,直升机在水面上飞行,机场公路边上是狗尾巴草。就像来到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想象也极为准确一样。我喜欢大城市。
————————
题图:2008年8月2日,奥运会开幕式排演现场之外。Feng Li/Getty Images
图二:一艘运煤的货船,正穿过三峡。Tim Graham/Getty Images
图三:在北京CBD核心区的大望路过街桥上,远眺央视新大楼。楼富稼/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