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潘文捷
编辑 | 姜妍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代对前辈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距1900年整整30年后,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一篇:《90年代之摇滚乐——是黄金岁月还是转瞬即逝的春天?》。

“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
1994年12月17日晚上,当穿着条纹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何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晃着、蹦跳着、嘶吼着朝在场的近万名观众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整个场馆的气氛被带到了最高点,乐声和人声构成巨大的声浪,令人心魂震荡。
这场名为“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演唱会,主角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的三位签约艺人——窦唯、张楚和何勇,他们被合称为“魔岩三杰”。
彼时,摇滚乐正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努力悄悄“突围”,为自己争取一小块“阵地”。在大众视野里,谭咏麟、叶倩文、黎明等港台巨星正密集地来到中国大陆演出;而本土歌星中,大街小巷响起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和杨钰莹的《我不想说》,这些柔风细雨的婉约风格与看起来野蛮放肆的摇滚乐颇为格格不入。
经历了十年的初期发展,摇滚乐开始突破原有的地下探索和小圈子,开始受到国内新闻界空前的热情,摇滚乐手的演出机会也变多了,崔健还完成了他的全国巡演。
但由于大陆的摇滚乐市场此时还不够成熟,魔岩唱片(魔岩文化成立于1992年,1995年品牌更名为魔岩唱片)选择香港红磡作为演出舞台,并期待可以在香港获得商业的成功进而促进的内地市场。
可是当时,在见多了偶像明星的香港人眼里,摇滚乐还是“牛鬼蛇神”,何勇在演出前炮轰四大天王的言论——“四大天王就是小丑,张学友还可以吧”,更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不少涉及演出的灯箱、地铁广告都被石头砸碎,让主办方不免担心演出能否顺利进行。但与此同时,这番言论也让“魔岩三杰”得到了香港媒体的再三报道。
或许炮轰言论的“炒作”起到了部分作用,演唱会当天,红磡体育馆坐满了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当晚,窦唯首先出场,“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好强、无奈、孤独、脆弱……”,他以《高级动物》开场,一身黑色西服,冷冷清清的少年模样。随后登场的张楚则一身格子衬衫,坐在舞台中央,唱出他的悲悯。最后登台的何勇则带动了整个场馆的气氛,乐声和人声构成巨大的声浪,令人心魂震荡。
在此之前,香港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萤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这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演出。在魔岩唱片推出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现场CD的文案里,魔岩文化的创始人张培仁描述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尽管场地有严格的规定,但是上万名观众都跟随着音乐咆哮、摇摆、撕扯衣服、纵情跳跃。第二天,港台报纸则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道了演出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红磡,很中国》……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大家都对演出当天的热烈反应做出高度评价,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是山里边来了一帮人,在花花世界里闹得天翻地覆。”当时隔28年后,乐评人郝舫回忆起这场史诗般的演出时,他认为,“中国摇滚乐势力”用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证明了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能诞生什么样的音乐。正如张培仁后来所说,在香港带给人们冲击热潮并不是大陆音乐人的创作目的,他们公开告诉媒体,北京才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中国才是他们创作的根。
北京的新音乐乐手们带给港台的冲击正是来自于此,他们首次证明偶像不是一成不变的神话。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抛开了惯有的矜持,呐喊疯狂。而带给港台唱片业与媒体的冲击也是来自于此,他们开始相信,商业应该只是一种流程,一种制度,商业不是一种音乐形式。
80年代后期:中国摇滚乐的源头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
中国大陆的摇滚乐热潮,比欧美晚了二三十年。在猫王、披头士、鲍勃·迪伦横扫欧美乐坛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依然刻板且模糊,对摇滚乐更是一无所知。即便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这个概念,在大多数国人眼里还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象征。
当时光迈入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大陆终于开始进入了大众视野。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成为了第一支来华演出的西方摇滚乐队,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是5块钱,在当时可是普通人平均半个星期的工资。而在开演前,门票更是被黄牛炒到了25块钱。演出当晚,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吸引了一万五千名观众到场,有不少乐迷从外地赶来一睹盛况。
对于30多年前的现场观众来说,如何与台上的乐队互动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情。演出开始后,现场十分安静,当主唱乔治·迈克尔想要调动气氛示意大家和他一起打拍子时,不明所以的中国观众鼓起了掌。但随着演出的推进,人们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在观众席里坐着的成方圆后来回忆说,“到场的外国人都很激动,一起跟着唱啊跳的,但是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坐在那看,有人想站起来跟着一块唱,就有警察过去维持秩序,让他们坐下。”
除了成方圆,观众席里的来自音乐圈的还有郭峰、崔健、窦唯等等,郭峰后来回忆说:“这个场景我永远都忘不了,中国观众全都看傻了。”
受到震惊的中国音乐人很快就缓过神来。1986年5月9日。这一天在为庆祝世界和平年举办的“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为郭峰创作)的演唱会上,崔健第一次唱出了《一无所有》,正是这首歌让中国的摇滚乐不再一无所有。1989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表,这张专辑成为了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也让全中国的音乐爱好者普及了一个新词:摇滚。崔健还第一次把“我”这个概念提了出来,在他以前,中国歌曲很少有“我”,只有“我们”,即便有也是“我是一个兵”“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是,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我”,出现了150多次。

崔健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1989
在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摇滚乐队在北京生长发芽,他们针对特定社会现象,创作出大量具有批判性的音乐作品。
接着,90年代到来了。当“90现代音乐会”即将在1990年2月17日和18日举办的消息一传开,北京首都体育馆的售票厅前就排起了一里多长的队伍,尽管是寒冬腊月,风雪不断,等待买票的年轻人依然络绎不绝,一张售价5元的票在黑市上可以炒到50元。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比起5年前威猛乐队的那次演出的现场反应,这次,观众的反映已是截然不同了——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后来回忆时说,演出从头到尾,现场观众就像球迷在进球时那样的疯狂呐喊,以至于在台上的他根本听不见自己弹琴和演唱的声音。最后,这场演出跺坏了两千多把椅子。
90年代初,打口带的出现传播和专业乐评人的出现,对中国摇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2年,郝舫成为了打口带最早的购买者之一。同一年,一本名为《世界摇滚乐大观》的书由媒体人黄燎原、韩一夫编写出版。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摇滚乐与流行乐。依然是在这一年,《音像世界》杂志推出了《对话摇滚乐》栏目,由乐评人章雷和王小峰主持。在1993年,DJ张有待开始在北京音乐台主持他的第一个节目《摇滚杂志》,过了一个月,由于电台要求不能提及“摇滚”二字,张有待把节目名称改为了《新音乐杂志》。就这样,在媒介的催生下,相对稳定的中国摇滚乐迷群体形成了。
90年代的中国,急速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在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开始式微之时,张扬个性、彰显叛逆的摇滚乐成为了这个年代复杂情绪的代言,受到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但也有人表现出了对这一新兴事物的担忧。1993年,一位领导找到张有待,这位领导称,自己看过前苏联的外长的一本回忆录,里面说苏联开始变色就是苏联的年轻人开始听西方摇滚乐的那一天。张有待告诉他,摇滚乐其实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的环境下,摇滚乐就不会那么政治化,不会那么危险。
商业的大潮会冲淡政治的浓度,今天看来,这句话正可以概括90年代摇滚乐的发展历程。
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大陆:商业化的开始
对于许多听惯港台音乐的人,他们的歌不一定能被理解和接受。我们只是希望你知道,正有一群和你血脉同源的年轻人,想爱过音乐,传递他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挣扎,在歌声中传达渴望和梦想,不管他们的名字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位置,他们尝试在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
——张培仁《唐朝》文案,1991年
在崔健以外,北京有潜力的摇滚音乐人并不少,有和崔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第一个获得国际奖项的常宽,有掌握外语并可以接触外国音乐资料的曹平、曹军两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高旗、何勇……港台唱片公司也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1991年,时任滚石唱片副总经理的张培仁征得母公司同意,创立了魔岩文化公司,并在魔岩旗下成立“中国火”品牌,致力于在没有音乐产业的内地发掘摇滚乐人才。
魔岩第一个签约的音乐人是唐朝乐队。据张培仁接受深圳电台专访时的回忆,1989年的冬天,他第一次来北京,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在王府井的咖啡厅里与唐朝乐队见了面,“他们几个长发彪形大汉走过来,个儿也高,看见了以后就突然从心里有一种仰慕之意,觉得大伙儿真的可以变朋友。”无独有偶,1992年,beyond乐队经纪人陈健添在挖掘了王菲,为黑豹在港台发行了首张专辑《黑豹》之后,发现内地人才济济,他在北京一家小宾馆里租下两间房,成立红星生产社。魔岩和红星后来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厂牌。
在魔岩之前,大陆歌手出名的途径大多是通过电视台,对于大陆的摇滚乐人来说,魔岩的到来才让他们意识到可以不用一直做晚会歌手:原来乐队的工作是可以策划的!而另一方面,当时在港台,人们常见的华语流行音乐只有抒情和偶像这两种形式,连专业的摇滚乐制作人也没有几位。在为唐朝乐队打造第一张唱片时,张培仁找的很多制作人都放弃了,要么是嫌预算低,要么是觉得北京苦,要么是对北京的摇滚乐没有信心,只有来自台湾的制作人贾敏恕愿意进棚。
于是,在1991年的冬天,唐朝乐队第一次进入录音室,他们的首张专辑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2棚,在巨大的毛主席像下面,在一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死磕”式的录制,贾敏恕整整工作了45天,出来之后宣传文案说他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次年,名为《唐朝》的这张专辑问世了。专辑首发10万张,很快宣布售罄。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超级经典。

唐朝乐队
魔岩唱片 1992
签下张楚是张培仁的第二个决定。1990年1月某一天,张培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用随身听听着小样,当听到《姐姐》这首歌的时候,张培仁在冰天雪地里几乎听到流泪。于是,在1992年,贾敏恕操刀的拼盘专辑《中国火1》问世,其中就收录了张楚的第一首作品《姐姐》。在张楚之后,张培仁又签下了离开了黑豹的窦唯,还有看到唐朝乐队做得不错而离开港资大地唱片“投奔魔岩”的何勇。

后来成为太合麦田CEO的詹华当时初入唱片业,起点正是红星生产社,在2016年9月的视频节目《海豹观点》中,他谈到当时大陆的娱乐产业一片荒芜,直到1994年都没有通告这个概念,“去各地做宣传这个模式,现在叫通告。那个模式之前都没有任何公司做过,我们是第一个出去做通告的。”他也谈到魔岩张培仁的商业操作令人惊叹,“他用文案把整个中国摇滚乐最精华的一些东西整合成一个概念,推向市场,把摇滚乐包装成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文化底蕴的系列”。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的文案正是这种包装的案例,文案里这样写道:“如果你听见了一种中国人的自信,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到的事。那是因为你同样也有对中国人的渴望。”它把这支乐队与民族自豪感结合起来,让许多音乐爱好者心潮澎湃。后来成立汉唐文化的黄燎原也曾在采访中回忆,同一个宣传文案,内地做就是用复印纸打印,而魔岩则是做成信纸、套封、硬壳包装,极为精致,让他感觉十分新鲜。
中国大陆摇滚音乐人并没有立刻欣然接受港台独立唱片公司以及他们代表的商业化进程。郝舫告诉界面文化,港台唱片公司刚刚来到北京时吃了不少苦头。“你(港台人士)要是来饭馆请客,他们(摇滚音乐人)就捡贵的点,叫做打牙祭。”当年的音乐人普遍穷困潦倒,以致太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好的,可是,乐队把制作人当作提款机的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穷”字能够解释的。在《摇滚危机》的作者王黔看来,港台独立唱片与大陆摇滚音乐人之间弥漫着一种不信任。一方面,很多音乐人觉得摇滚是艺术,唱片公司却把它当作了赚钱的工具。港台独立唱片公司则认为大陆的摇滚人太懒惰,不遵守协议,合作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一些音乐人追求内地摇滚的本地身份,对港台和海外的唱片公司持有一种阴谋论的观点。这种情绪之下,不仅何勇曾带着两把斧头从大地唱片公司抢回母带,甚至还有乐队在北京三环路劫走台湾制作人的汽车,押送制作人去其家中,将值钱物品洗劫一空。
1994年,昙花一现的新音乐春天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象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象虫子一样
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何勇《垃圾场》,1994年
1994年的春天,魔岩唱片同时推出了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的音乐风格截然不同。窦唯借助古典文学的写作技巧,含蓄内敛,仿佛在梦境中起舞;张楚带着一种现代文学的诗意,注视着平凡而卑微的人们;何勇则常常无视规则、破坏秩序,如同流氓无产者一般。他们三人在1994年推出三张专辑,后来被证明是中国摇滚经典之作,这也让1994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同年,红星生产社为该公司旗下第一名艺人郑钧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赤裸裸》,詹华形容当时郑钧长得帅,口才好,歌又好听,一出通告就赢得了各路电台DJ的喜爱,在全国的排行榜上都是冠军,迅速走红。也是在1994年,清醒乐队的沈黎晖为了实现自己的摇滚明星梦,用几万块钱为清醒、石头、天堂等六支名不见经传的新乐队录了一张摇滚合集《摇滚94》,当年就有了销量15万张的不俗成绩。
这时候,一边是港台歌星开始风一般地吹进大陆,潘安邦、凤飞飞、潘美辰等开始在大陆频繁演出,造成了轰动效应。另一边,“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也给香港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张有待对界面文化分析称,红磡演唱会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当时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摇滚乐的市场非常小,魔岩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才在最短的时间让全社会来关注中国大陆的摇滚乐,这显示出魔岩商业运作和推广的力量,让摇滚乐实现了一次人为的拔高。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为红磡的成功欢呼多久,“新音乐的春天”转眼就变成了寒冬。在乐评人李皖看来,这场寒冬在1994年下半年崔健《红旗下的蛋》问世就初露端倪。这张专辑引来了听众的失望和乐评人的批评,而且刚上市就被停止销售了。李皖形容这张唱片“将中西各类音乐进行高密度的拼贴涂抹,正像此时改革开放时的中国,五色纷陈,各国文化穿插交汇。”除了崔健的新作让人失望,红磡带来的摇滚热潮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张有待回忆,在红磡演出之前,他做了几场魔岩三杰的演出。无论是在长春、南京、长沙,全部都遭遇了滑铁卢。“门票都没卖出去,我们去了以后再只能待两天再坐飞机回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魔岩三杰在红磡掀起的热度不真实吗?在郝舫看来,虽然人们都觉得90年代摇滚在内地特别火爆,可现实情况是,当时正在求学阶段的他发现,本科和读研的7年时间里,同学中听摇滚乐的只有他一人,买过打口带的更是只有他一人。即使在当时打口带最繁荣的五道口,他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店一天的客人超过五十。据他估算,张有待在北京音乐台的《新音乐杂志》节目可能听众只有以流行音乐为主的节目伍洲彤《零点乐话》听众的百分之一。真相是,整个90年代,主宰中国主流音乐市场的毫无疑问是商业流行音乐。摇滚乐卖得再好也卖不过那英、蔡国庆、杭天琪。另一方面,盗版的猖獗使得正版的实际购买量少得可怜。国际唱片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中国音像产品的盗版率仍然高达90%,唱片公司损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也是后来港台和海外唱片公司撤出大陆摇滚音乐市场或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
除了市场因素以外,“中国火”厂牌下的音乐人本身的创作力似乎也在逐渐衰竭。1995年,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世,这之后,唐朝很长时间没有推出更加震撼人心的作品。同一年,滚石由于经济原因将魔岩唱片的重心从大陆后撤,张培仁等人被召回台湾,贾敏恕成为了中国火的品牌经理,最终,魔岩在2001年结束营业。在那以后,“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何勇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语),“魔岩三杰”成为了“魔岩三病人”。魔岩三杰带来的“春天”转瞬即逝。据詹华分析,一方面,这与音乐创作的规律有关:创作型艺人常常第一张专辑积累了十年的创作,表达力量很强,可以给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而在做完第一张石破天惊的专辑之后,就后继乏力。另一方面,在唱片工业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摇滚乐手看到市场反映很强烈,却没有体现在版税上,因此感到不满:在2009年盛志民导演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中,何勇还在问张有待是否和张培仁有联络:何勇看到四处有自己音乐的彩铃在卖,却从来没分到一分钱。
红磡之后:摇滚进入都市夜生活
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 心在徘徊
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
别误会我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完美
有时我也会放纵一次让自己喝醉
——零点乐队《别误会》,1995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红磡是一个标志。本身,香港代表着亚洲商业流行文化的制高点,红磡演出的成功对两岸三地的摇滚乐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李皖看到:1989年至1994年的大陆摇滚“充满了时代大变局的混沌元气,如西北吹来的红色风暴”,锋线所及,刺激了港台的敏感神经,使这两地在这一时期也爆发了摇滚的激流。张培仁则认为红磡演出是大陆、香港、台湾的年轻人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去完成共同的理想,让香港人见识到了内地的文化,甚至“对香港回归都是有一份功劳的”。
郝舫并不认为红磡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摇滚达到了顶峰,接下去就是衰退。他指出,红磡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证明中国摇滚乐确实存在价值,可是它说到底就只是一场演出。“如果我们说那就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那不是在羞辱红磡以后所有玩摇滚的吗?”在他看来,中国摇滚乐的价值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热爱摇滚乐,有多少新的摇滚乐队产生出来。
在1994年之后,窦唯发了《艳阳天》(1995)《山河水》(1999)《幻听》(1999),张楚发了《造飞机的工厂》(1998),除此之外,魔岩还推出了《中国火2》《中国火3》等拼盘,并为刘元、王勇、ADO乐队等推出专辑,但整体来说不复1994年的盛况。与之相对的,1996年则成为了红星生产社的天下。1996年,在这一年当中,红星生产社就前后发了八张唱片,堪称当时内地最活跃的唱片公司。
1995年,三里屯北街上开设了第一个酒吧Jazz.ya。随后,三里屯酒吧街的形成给了中国摇滚音乐人一个稳定的舞台。在2001年出版的《自由风格》一书中,作家周国平与崔健谈及酒吧的出现时指出,摇滚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现在却来自都市夜生活。”他们质疑的是,在消费主义的环境当中,摇滚是否还能够坚持自己原有的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颠覆。

著有《红色摇滚:中国摇滚乐的奇怪长征》(Red Rock: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 & Roll)一书的加拿大音乐人、作家乔纳森·坎贝尔认为,典型的中国摇滚人认为摇滚的任务不仅是做音乐。他们把艺术家视为重要的革命工作者:他们有责任向国人授课,告诉他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因为革命永无止境。
而在王黔看来,中国摇滚音乐人“英雄”和“斗士”的角色不过是被媒体作家和学者幻想和期待的戏剧模型。在与摇滚音乐人接触的过程中,王黔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崔健这样的音乐人是一个例外。实际上,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并不认为自己在90年代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
中国摇滚的影响力最初确实建立在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批评之上。对于李皖来说,摇滚乐的泛政治化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精神解放、艺术探索和启蒙主义的气息。可是当时代逐渐变化,当90年代的深化改革和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经济收入提高,整个社会氛围改善,人们炒股的炒股,买房的买房,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摇滚人再也说不出什么震动社会的话语。即使试图揭示新的现实,面对的也是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的大众。中国摇滚从一种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音乐,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音乐。
在过去,崔健唱一首歌就能击中所有人的痛点,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关注。张有待告诉界面文化,“过去(80年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社会,很适合摇滚的生活环境。后来(90年代)没有黑和白了,全部是灰色地带。没有正确和错误,没有某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的对立,都是多角度的。”李皖也在《新周刊》的一篇《娱乐时代,当摇滚不再咆哮》的采访中称,摇滚乐的强大,本来应该“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也就是说,摇滚乐不孤立于社会之外,而恰恰是主流文化的倒影。当国家全面开放,人们投向享乐主义的怀抱,摇滚失去了对立面,失去了力量。于是,这个曾经在大变局中显得最为大声的载体,逐渐不再产生强烈的社会信息,而是开始大量生产感性。
在90年代初期,摇滚音乐人似乎陷入了政治关注和内容的怪圈。当1996年,零点乐队唱着爱情主题的《别误会》把中国摇滚带进了主流音乐市场,摇滚圈子的第一反应是对零点和他们的音乐反复否定,因为歌唱爱情是向商业妥协的信号。反而是在90年代末朴树成名的时候,对爱情主题的轻视已经不复存在了。
北京新声:向上一辈挑战
我不知道历史
我不懂得规矩
我不知道羞耻
这跟你没关系
——地下婴儿《拒绝》,1998年
而在更新一代的摇滚人看来,崔健等人的摇滚已经丧失了精英启蒙立场的有效性;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臧天朔则与商业合谋,使得摇滚沦为了文化商品;窦唯等人则开始流于学院趣味的自我玩赏。因此,他们就像世纪末文坛“断裂”事件中的新作家(1998年,《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设计者和部分答卷的回答人,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提出质疑)一样,对上一辈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当时,北京的业内人士正“要求摇滚乐在卖身与局部卖身之间作出选择”,可是这时候,文化上的外省却“奔忙着最具实验精神也不乏盲目热情的纵容者。一直以来,外地摇滚始终没有能够撼动北京摇滚的地位。1994、1995年,太平洋公司出版了两盘名为《南方大摇滚》的磁带,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也不乏有与北京摇滚分庭抗礼之意,出版后却引来了北京摇滚的一片嘘声,甚至认为其只是南方歌舞厅的卡拉OK歌曲。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的乐队都渐渐开始有了成批的作品,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原创乐队和观众群,在现场如果只翻唱黑豹会被视为可耻。从广州“98音乐新势力”开始,河南新乡、河北唐山、山东青岛……各类演出为北京以外的城市带来了摇滚乐,也鼓舞和催生了更多的本地乐队。
在失去了单独代表中国摇滚的特权之后,北京依然是中国摇滚的中心。在此之前,北京摇滚圈从来不限于北京人,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建立,使得北京对外地乐手更具吸引力。大批有志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和这里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音乐人一起,发出了新的声音。广东人欧宁为摇滚音乐界的这一新现象感到着迷,1997年,他找到颜峻等人,到北京采访了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子曰、鲍家街43号、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花儿、秋天的虫子等乐队和张浅潜等音乐人,并在两年后出版了《北京新声》一书,在这本书中,乐评人们用“北京新声”来定义这一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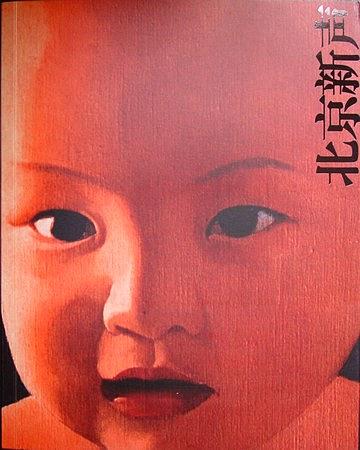
欧宁、颜峻、聂筝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09
《摇滚中国》的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博士孙伊把“魔岩三杰”以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摇滚的这种变化称为“分流”。
孙伊看到,与60年代出生、曾经身处历史激变当中的一代不同,“北京新声”的乐手对历史可谓是一张白纸。正如地下婴儿在《拒绝》中唱道,“我不知道历史,我不懂得规矩,我不知道羞耻,这跟你没关系”,如果说60年代出生的乐手回味着大时代种种风起云涌,新一代音乐人则拒绝历史介入音乐当中,拒绝了崔健式的“红色摇滚”。
李皖则用“城乡结合部”概括6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的精神特质。认为他们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无暇照料的家长、教育要革命的松散学制之下成长的一代,过着“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像是城镇,又像是农村的日子”。与之相对的,“北京新声”一代的摇滚人大多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不会面临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个人体验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断裂感,因此也不会唱出窦唯“又拆了连同过去全部都被拆了”(《拆》)的挽歌。对于变化,他们的态度是麦田守望者乐队唱出的“你倒是来呀,你倒是快呀,你倒是变呀,你倒是快呀”,或者至少也是带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孙伊看到,这一代人崇尚着一种本能的、以快乐原则为标准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特质是“城市化”。
当然,这一代人也并非无忧无虑的一代,孙伊认为,在整个社会的结构方式越来越被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组建起来的时候,这一代人遭遇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压抑和异化。在他们这一代人这里没有“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有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既定人生轨道,有的是“你别无选择”的苦闷。在这个过程中,摇滚也从一种具有时代特征文化逐渐变成了青年亚文化,摇滚的听众扩大到了广大的城市青少年。
至此,中国的摇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迅速吞食了西方半个世纪的摇滚成果,通过听打口、扒带子,乃至学习西方摇滚明星的装扮作派,在90年代实现了与世界摇滚乐的同步。在这段时期,不同的乐队习得了不同的摇滚流派,各占山头。李皖看到,在头五年里,黑豹、唐朝、超载、战斧分别攻下了流行金属、激进金属、鞭笞金属和死亡金属,之后,脑浊、诱导社抢占了朋克,窦唯、陈劲、木马拿下了后朋克……流行爵士、邋遢摇滚、英式摇滚、工业噪音、视觉系等等音乐风格也被一一攻占。
一方面,越来越多新的乐队成立了,越来越多新的音乐风格呈现在中国音乐爱好者面前;另一方面,曾经让整个社会共同倾听的摇滚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却在日益衰退。李皖认为形式主义摇滚在初期颇具轰动效应,中期也不乏新奇效果,但是后劲却不足。到了1998年,《中国火3》拼盘被人们看作是最后一把火,从此以后,“一半出于无奈,一半出于孤傲,摇滚乐强硬派向小众发展,对大众做出我不理你,你也别理我的姿态。”
尾声
妈妈
有些东西永远也不会失去
这样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吗
反正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
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
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
一个人看到的最后一丝亮光
——舌头乐队《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2014
出生于60年代的张有待认为,每一代人都会有由于荷尔蒙而产生的、无因的反抗,可是那种反抗不过是个人的反抗,失去了社会意义。在1997年以后,他就开始发现有趣的乐队越来越少,自己也转而投身于国际的新潮流电子乐。有人开始说“摇滚死了”,张有待也没有否认,他认为摇滚的精神死了,人们觉得一切都是娱乐。
在涅槃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因不看忍受商业化运作的压力而自杀之后,垃圾摇滚(Grunge)让位于英式摇滚(Britpop)风潮,随着绿洲乐队(Oasis)、山羊皮(Suede)等为代表的英式摇滚的退潮,化学兄弟(the Chemical Brothers)、神童(The Prodigy)、 地下世界(Underworld)为代表的电子乐兴起,他们高唱着摇滚乐死了,迎接电子乐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摇滚乐手也像柯本一样质疑着商业化的运作。1997年之前,中国摇滚是摇滚北京、中国火的天下,到1997年以后,拿着做印刷厂的钱,想给清醒乐队出专辑的沈黎晖成立了摩登天空有限公司。摩登天空、嚎叫、新蜂成为了著名的厂牌,国内独立唱片公司取代了港台唱片公司。看起来,相较于地下乐队的狂躁和前卫,摩登天空更时髦、干净,更像是制造流行音乐的地方,但是到最后,只有摩登天空从地下室的小作坊成为了一家唱片帝国。
到了90年代末,中国摇滚已经从早期的思想意识的艺术品,逐步变成了多功能的产品。摇滚音乐人也开始不再觉得和流行音乐明星同台演出令人羞愧,甚至他们的一些人也成为了明星。王黔发现,很多公开表示抵制商业的摇滚音乐人其实也意识到商业并不仅仅带来问题,也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多的时候他们抵制的其实是不公平的商业合约。就连崔健本人后来也公开声明他并不反对商业,而是认为摇滚音乐人在不改变艺术初衷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投入主流音乐市场,与其他流行音乐进行竞争。
在郝舫眼中,摇滚一直在和商业化搏斗,但最终都要被收编。全世界有名的摇滚音乐家都会被唱片公司、被商业体制吸收,否则人们就无法听到他们的音乐。他说,中国摇滚的问题从来不是过度商业化,而恰恰是商业化程度不够。他看到,中国的唱片产业在刚刚有点儿起色的时候,盗版的横行就对商业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早在1992年,黑豹乐队就因为专辑被疯狂盗版而颇受其害,在首张专辑《黑豹》发行了香港版而大陆版尚未发行的时候,其盗版带已经以百万盘以上的发行量洒向人间。主音吉他手李彤愤怒道:“他们这么做是扒我们的皮,喝我们的血”,其经纪人也无可奈何。又如,在红磡之后,魔岩发行了演唱会的录像带和LD,市面上却大量出现了盗版的VCD和DVD。张有待分析,在90年代,盗版的猖獗确实有助于摇滚的普及和推广,可是却造成了投资人、市场和音乐人相互的不信任。魔岩、红星撤离内地就与盗版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投资多少钱,都是填不完的无底洞,可是音乐人则感觉到市场上唱片销量大好,自己却未能从中获取更多利润。
虽然盗版猖獗,市场混乱,但90年代依然是中国摇滚乐产生最多黄金作品的年代。郝舫认为,在2000年以后,摇滚乐在中国真正出现了危机。因为艺术在人生指标中的重要性降低了。他说,90年代的前半段还残留着8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渴求,那时候最聪明的头脑还在钻研文学艺术,到了90年代末,年轻人则一个个都想着当银行家,投资房地产。过去,摇滚乐和其他艺术形式在社会的价值观念当中居于中心位置,但在整个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艺术被边缘化,摇滚乐成为了整个消解运动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要哭摇滚乐吗?诗歌不值得哭吗?文学不值得哭吗?那是更值得哭的事儿。”过去,诗人是真正的明星,北岛和顾城是年轻人心目的偶像,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居于中心的变成了企业家和商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似乎只有电影仍然被人们关注着,或许因为它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但“更是因为它能够赚钱”。郝舫这样认为。
摇滚乐当然也能够赚钱。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音乐教授保罗·弗里德兰德的《摇滚:一部社会史》一书中,“摇滚乐”(rock and roll)被定义为“摇滚流行乐”(rock/pop),这说明,摇滚本来就有流行的一面,有其作为一种商品的本性。在9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朴树、许巍、汪峰这些在主流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摇滚人,知名度已经不亚于偶像明星。在1999年底,颜峻这样记录当年的摇滚圈生存状况:“老炮忙着数钱或解散,新秀在跟公司谈判,群众派媒体来采访,一派热闹景象。摇滚乐似乎就这样发际了”。在新世纪,离开了鲍家街43号的汪峰唱着《我爱你中国》登上央视,之后又以“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春天里》)这样直白的歌词赢得更多听众的喜爱;花儿乐队和新蜂唱片不欢而散,用《我是你的罗密欧》转型成功,创造出更多洗脑式的国民歌曲。一切热热闹闹,风风火火,虽然在2000年代,中国摇滚几乎再没有诞生一位大师。
(本文按语部分写作:黄月)
参考资料
书籍:
《北京新声》,欧宁、颜峻、聂筝,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09
《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李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01
《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01
《摇滚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研究》,王黔,2015-07
《搖滾中國》,孫伊,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06
《自由风格》,崔健、周国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01
影像:
《海豹观点》第06期、08期、09期、11期、16期,丁太升 等,海豹活动,2016-09
《世说新语·艺术传奇》特别巨献 - 摇滚中国30年“怒放”,SMG艺术人文频道
《再见,乌托邦》,盛志民,2009-03
文章:
《beyond御用词人刘卓辉:我很庆幸能陪他们走过那段光辉岁月》,最爱音乐,http://www.sohu.com/a/227746190_203237
《崔健:部队子弟有“特权” 能接触西方文化》,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a/20141010/40832984_0.shtml
《崔健和他的年代》,微杂志,https://site.douban.com/136100/widget/notes/6051842/note/259286597/
《档案解封:台湾音乐人披露北京摇滚圈奇闻逸事》,南方都市报,http://ent.sina.com.cn/y/2006-07-25/10301171357.html
《郝舫:把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经济观察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50827/17001922386.shtml
《魔岩改变中国摇滚内幕:文艺复兴或拔苗助长?》,网易娱乐,http://art.china.cn/music/2010-04/28/content_3486628_3.htm
《深度回顾唱片的辉煌时代:郑钧、许巍与红星生产社》,摇滚客,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66411.html?_k=0hcyad
《香港摇滚和内地摇滚的第一次接触——1988年BEYOND“超越大地”北京演唱会》,大麦网,https://news.damai.cn/rock/c/20110415/364.shtml
《“文革”后首支来中国开演唱会的西方乐队,那个帅气的主唱乔治走了》,奇遇电影, http://www.sohu.com/a/122671635_563955
《摇滚圈凶猛往事:何勇抡斧头抢母带,伍佰为陈升打群架》,果酱音乐,http://www.jammyfm.com/p/19863.html
《野兽档案》,颜峻,http://www.subjam.org/archives/2938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中国摇滚三十五年》,网易,https://music.163.com/web/pctopic?noflash=1&id=69001&black=1
《娱乐时代,当摇滚不再咆哮》《新周刊》杂志2019年第08下期
《张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界面正午,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27034.html?_t=t
《赵牧阳的两张面孔》,南方都市报,http://cul.qq.com/a/20150123/025095.htm
《中国特色摇滚乐难成主流》,参考消息,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0321/20125.shtml
《中国摇滚的江湖传说中,他是中心人物》,正经恶搞,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7950836980949&wfr=spider&for=pc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10首昔日经典》,看理想,http://news.ifeng.com/a/20170513/51087058_0.shtml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