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天我们推荐一本非虚构作品《巨浪下的小学》。这本书写的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特大地震和海啸。在那场灾难中,最著名的是福岛核泄漏事故。作者却把焦点放在了一所小学,大川小学,当时这所小学被海啸覆灭,74个孩子遇难。
英国记者帕里花费6年追踪调查,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井然表象下暗藏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本文摘自书中一个小节,原标题为《解释》。悲伤和愤怒的家长们,在学校的说明会上要求一个解释,为什么学生没有撤到山上,躲避海啸?为什么灾后校长迟迟未能出现?一位父亲问,“你们看见那些肿胀的脸了吗?”有些孩子一个月后才被找到,变成了“一堆发臭的东西”。他说:“要知道那可是一个人啊!一个人!”
校长,你看见那些肿胀的脸了吗?
文|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译|尹楠
海啸过去4周后,大川小学的上级监管单位石卷市教育委员会召集失去孩子的家长开了一次“情况说明会”。说明会在一个周六晚上举行,地点就在重新安置大川小学幸存孩子的那所内陆学校。会场不允许记者进入,但一名家长对会议做了全程视频记录。校长柏叶和其他5名教育局的代表,身着日本公务人员统一配发的蓝色制服坐成一排。他们对面就是家长和亲属,97个遇难学生的家长都收到了通知,在相机视频里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屋子里没有暖气,从视频里可以看到所有人都裹着厚外套,戴着帽子和围巾。
说明会按照常规流程开始,教育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今野先生做开场发言。他以道歉开场:他失声了,因此只能做简短的开场白。“大家晚上好,”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向这次灾难的受害者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我尤为真诚地为死者祈祷。这个月,孩子本应该满怀希望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然而,3月11日一场巨大的灾难突如其来,超级海啸瞬间夺走了平凡生活中如此微小的欢乐。失去如此多不可替代的孩子和老师的宝贵生命,春天也黯然失色。”
在日本,公开会议通常都是一种场面温和的公式化仪式,发言人基本上都是重复一些陈词滥调,不会出现各方对峙或言语冲突的情况。可是,当今野把发言权交给校长柏叶,会议现场气氛迅速发生变化,预示着这不会是一场例行公事。
悲伤和愤怒让在座所有亲属几乎失去理智,很多人无法公正客观地看待柏叶照幸。柏叶今年快60岁,头发灰白,身材矮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紧张或思考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抿一下嘴唇。在其他学校担任十几年副校长后,他在去年4月被任命为大川小学的校长。甚至在灾难发生之前,都没人清楚柏叶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上任一年后,也不是所有家长都了解他的为人。
那天下午不在学校,并不是他的错,没人能想象他内心的恐惧和痛苦。但是他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首先,他在灾后隔了那么长时间才前往现场查看,其次就是他露面之后的种种不当行为。他完全没有参与搜救行动,甚至连象征性的行动都没有,这让大家无法原谅。他第一次前往受灾现场时,只是回答了媒体的一些问题,并用一台昂贵的相机拍了许多照片。另一次到访时,大家只看到他在非常紧张地寻找学校的保险箱。
说明会召开的时候,家长已经积攒了一个月的愤怒和痛苦。那天晚上,他们把怒火烧向了柏叶。
“直到3月11日下午,”轮到柏叶发言时,他含糊其辞地说道,“学校里还回响着孩子的欢声笑语,但我们就这么失去了74个孩子和10位老师,我对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听不清!”听众席中传来一个声音。
“你没有话筒吗?”另一个人说。
柏叶继续说:“当我站在学校教学楼前,我脑子里还浮现出孩子的一张张脸。真是太可怕了。”
“你什么时候去的学校?”有人打断他的发言。
“是啊,你什么时候去的?”另一个人叫道。
“我哪天去的?”这位校长有些气恼地说,“3月17号。”
“我们的女儿11号死的。”柏叶垂下了头。“我道歉,”他说,“为我的反应迟钝,以及其他失误——许多失误——表示深深的歉意。”
就在这时,家长群中传来一阵骚动,大家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男人坐在最左边,穿着一身黑,头和肩膀都深深地低俯向前,让人很难看清他的脸。
“哎呀,啊,啊,”有人叫起来,“那不是远藤纯二吗。”
即使是那些后来非常不信任远藤的人也承认,在海啸发生前,他一直是一名受欢迎的成功老师。他40多岁,戴着一副眼镜,为人谦逊,在学校职员中职位排第三。作为教务主任,他并没有专职带哪个班级,而是教授不同年级的自然和科学课。“孩子跟他非常亲,”今野仁美告诉我,“大辅是自然小组成员,远藤先生曾向他们展示鹿角,教他们制作鱼钩,还给他们讲鳄鱼和食人鱼的故事。他们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以前在渔村相川教书,离海边只有7英里,防灾演习就是他在相川小学的工作内容之一。大多数老师把这当成例行公事,只要求学生做一些常规的疏散演习以及更新家长的电话号码,可是远藤做得更多。相川小学的应急手册上规定,如果收到海啸警报,学生和教职员工应该撤离到三层楼高的教学楼顶层天台。远藤却认为这还不够。他重新编写应急手册,要求大家爬上学校后面陡峭的山坡,撤到山上的神社里去。
相川小学建在平地上,实际海拔高度与海平面齐平,距离大海只有200码。那场巨大的海啸袭来时,浪高50多英尺,彻底摧毁了整所学校。教学楼的天台上灌满了水:当时撤退到天台上只会葬身汪洋之中。但是,在修订过的应急手册的指导下,老师和学生迅速爬上山,结果没有一个人受伤。在他之前任教的学校,远藤纯二可以说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在别的情况下,他可能还能赢得大家的同情和敬佩。但是自从海啸第二天的清晨后,就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消息。他的下落和他所讲的事情已经引得大家议论纷纷—而现在他却出现在这里。
“他救了自己的命,”听众席中传来一个声音,“他还活着,所以让他跟我们说话。”
一个名叫加藤茂实的教育委员会官员这时说:“远藤先生自己也受了伤—脱臼和冻伤,他也去了医院。他现在还有一些精神问题。所以,听他发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别他妈开玩笑了,”一个人说,“哼,我们家长也病着呢。”尽管一副难受和痛苦的样子,远藤还是开始发言了。只见他躬身行礼,头和上半身几乎快与地面平行。他不时因情绪过于激动而哽咽,有时候他看起来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对不起,”他说,“我没有帮上忙,我对此深表歉意。”
原本此起彼伏的质问声戛然而止。
“请允许我讲述那天发生的事情,”他继续说,“我的记忆可能有一些空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见谅。”
* * *
“那是个周五,”远藤开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天的课刚结束,地震就开始了。那时候孩子正准备回家,他们都跟各自的老师在一起开班会。突然就断电了,广播设备也无法正常工作,于是我跑上二楼,挨个通知每个班级:‘躲到课桌下面,抱紧桌子。’孩子有点惊慌失措,但是老师安抚他们说一切都会没事。震动减弱后,我又跑到每个教室让他们出去,尽快疏散。”
远藤自己留了下来,检查教室和厕所,看是否有人落下。当他与其他人会合时,签到工作已经完成,孩子正坐在操场上。“有的孩子被吓吐了,”远藤说,“有的则一直哭个不停。老师设法让他们冷静下来。天又开始下雪了,有的孩子是光着脚逃出来的。我又回到教室去拿外套和鞋子给他们穿上。”
就在这时,釜谷的村民开始出现在学校。他们都是在地震时从自己家里逃出来的,希望能在学校的体育馆避难。远藤向他们解释,体育馆里到处都是碎玻璃,不适合避难。“我正在解释时,家长开始陆续抵达接走自己的孩子,副校长主要负责核对姓名,再把孩子交给家长。”
不久前才失去亲人的家长默默听着远藤的叙述,但听到这里,有人忍不住大声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如果你们开车把所有人带到山上去,他们可能都会得救。”
远藤没有回应,只是继续讲述那天的情况。“这之后我才知道海啸即将到来。当然可以选择上山。但是因为刚才的震动十分剧烈,而且还在继续,我……”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继续。他接下来的话让人很难理解:句子杂乱无章,语法混乱,事情发生的顺序也令人困惑。“海啸来时,”他接着说,“因为我们没有预料到海啸会如此巨大,我们还讨论是应该疏散到学校最安全的地方—体育馆楼上的走廊上,还是教学楼的二楼,而我考虑到教学楼之前损毁严重,就先走回教学楼检查一下情况。虽然很多东西都掉下来了,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躲回来。可是等我回到操场上时,疏散行动已经迅速展开。”
疏散的目的地是大桥附近的交通岛,距离学校400码,就在主路的转角处。孩子排成一列,歪歪扭扭地从学校后门走出去,穿过釜谷村公所的停车场。远藤走在队伍最后面。
当他经过停车场时,感受到一股强劲的气流。他形容道:“那就像一阵狂风,我从没听过那样的声音。一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当我看向学校前方釜谷大街方向时,看见了巨大的海啸。它正沿着那条路涌过来。”而排成一队的孩子正直直地迎向翻涌而来的巨浪。远藤立即大叫:“快上山!快上山!走这边!”他催促孩子朝反方向走,走向学校后方。“但是当我走到山脚下时,”他继续说,“我滑倒在雪地上,没法爬山,孩子都围在我身旁。”
“就在我走到山下时,两棵雪松倒了下来。它们砸到了我的右臂和左肩,让我动弹不得。我感觉海啸正在涌过来,心想完了,可是树突然移开了,可能是水的作用,而当我抬头看向山坡时,只见一个三年级的男孩正在呼救。我的眼镜和鞋都不见了,但我知道必须尽一切可能救这个孩子。‘走,往上走!’我大声叫,‘要活命就往上爬!’……巨浪声越来越近。‘往上爬,往上爬!’我一边推他一边大叫。”
这时候下起了雪。这个男孩已经吞了很多水,他和老师的衣服都已经湿透。“我意识到不可能下山了,”远藤又说,“我要和这个孩子在山上待一晚了。”他们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树洞,于是他们肩并肩地挤在一起,坐在一堆松针上。“水声越来越近,然后—我不知道是否只是我的感觉—每次余震都会有一些树嘎吱嘎吱地倒下。小男孩对我说:‘来了!越来越近了!我害怕!我们走吧,走去更高的地方吧。’”
山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远藤发现自己被树砸伤的手臂动不了了。男孩靠着老师的肩膀睡着了,远藤则开始为这个穿着湿衣服睡觉的小家伙担心起来。“天黑下来,而且非常冷,我想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原地,孩子可能会被冻死。”
因为没有眼镜,他在一片黑暗之中几乎看不见。但是他想,如果他们从山的另一侧下去,最终会在雄胜町的公路上遇到汽车和司机。“我请男孩为我看路,告诉我往下走是否安全。我们一步步往下挪,我依稀能辨认出公路上的车前灯。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我们朝着灯光走,然后看到一栋房子里有人,我们就叫道:‘请帮帮我们吧。’他们也真的帮了我们。”
他们最终到了入釜谷,仁美就是在那儿找到他们的。远藤第二天就被送进入釜谷的医院,然后又从医院直接回了家。
远藤解释道:“有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天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他还补充道:“我每天都会梦见孩子在学校操场快乐地玩耍。我还梦见了各位老师和副校长,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忙碌准备。我真的很抱歉。”
说完这些,他的头和上半身颓然塌下,有那么一瞬间,远藤看起来就要瘫倒在地上,教育委员会的人赶紧跑过去扶住他。他的痛苦就像血淋淋的伤口一般,让人一目了然,在教育委员会那些人看来,他们给予听众的只有形式化的礼貌和陈词滥调,华丽但无关痛痒,而远藤的痛苦给听众提供了他们无法给予的东西。面对远藤先生所遭受的不幸和活下来所承受的折磨,谁还能提出质疑?今野、柏叶和其他在座的官员也许都希望会议能到此结束,甚至希望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能就此结束。会场一片沉默,在座的亲属还沉浸在远藤的发言中。会议处于关键时刻:有可能产生任何结果。这时听众中站起来一个男人。
他叫佐崎敏光,他7岁的儿子彻马和9岁的女儿和美都在学校遇难。“老师,校长,还有教育委员会的各位。”他开口说道——这个开场白听上去似乎要将会议推向可预测的平稳方向。大家听他继续说下去。
“你第二天为什么没有迅速赶到学校?”他质问柏叶,“你为什么直到第7天才出现?你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孩子没找到吗?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吗?你能说出死去的孩子的名字吗?失去孩子的家庭——我们所有人都快疯了。还有10个孩子没有找着。你知道吗?想想我们的感受,想想那些现在每天仍在搜寻的家长的感受。我们每天都一身泥,但如果不去那儿找,我们就会疯掉。”
佐崎就站在教育委员会官员落座的桌子前,而此刻他们的视线都落在地面上。他穿着一件蓝色防风夹克,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在他们低垂的脸庞前挥动。
只听他又提高声音说,“只剩这只鞋了,我们只找到这个。一切都像这样,全毁了。我的女儿——就剩下这个?”说完他把鞋猛地拍到桌上,今野应声瑟缩了一下。“我的女儿!”他尖叫起来,“她就是一只鞋吗?”
说明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但柏叶和其他官员全程发言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几分钟。家长不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得到的却是支支吾吾、不完整的回答——无论是关于接收和发布了什么样的海啸警报,还是关于柏叶何时做了什么以及没能做什么。大多数时间都是家长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咆哮、怒骂、恳求、低语和哭泣,几乎所有怒火都烧向校长一个人。从视频里可以看到他目光低垂地坐在那里。虽然看不到谴责他的人的脸,但可以看到他们声讨时颤抖的背影:
狡猾的老混蛋。滚开,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这个混蛋。
我要用我这一生来为那些孩子报仇,无论你躲到哪儿我都不会放过你。
在日本,人们几乎不会这样说话——不会在公共场合这么说话,也不会对老师和政府官员这么说。但他们的确就是如此粗暴地打断官员的发言,言语中透出遏制不住的激动情绪,毫不夸张。
只见一个女人说:“我们相信他们第二天就能回来,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所有人都相信学校,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安全,因为他们在学校。”
又一个男人说:“每天我都能听见儿子和女儿的哭喊:‘爸爸,救救我!’他们在我的梦里大声哭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梦。”
家长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们看见那些肿胀的脸了吗?”一位父亲问,“才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变了那么多,成了一堆发臭的东西。要知道那可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叠一个地堆在卡车上,身上就盖着一块破布。等到你自己的孩子变成这样之后再来跟我们解释吧,你这个混蛋!”
另一个人问:“你知道每个班失踪孩子的人数吗,校长?不看那张纸。你不知道,不是吗?你必须要看着你那张纸。我们的孩子——他们只是一张纸吗?他们任何一个的脸你都不记得,是不是?”
他们无法抑制悲痛之情,他们的诉求并不难理解——只要坐在他们对面的人更体恤一点,不像这般被形式化的礼节和恐惧所支配,就能扭转屋子里的形势。家长不过希望自己的悲痛能得到一点共鸣,有人能对他们的损失稍微有所认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政府部门,而是跟他们一样活生生的人。家长激动得难以自持,于是他们抛开日本人一贯的含蓄作风,用含糊不清的东北方言更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那些官员不但没有直面家长的质问,反而朝相反的方向退缩,发表更加令人不满、更无情的说辞。
当被问到搜寻失踪孩子的情况时,今野答道:“目前,日本自卫队、中央政府和警察还在尽最大努力搜寻那些至今仍未找到的残骸。未来,我们还将在受灾现场及其他地方继续搜寻。”
家长请求为孩子举行联合葬礼,但校长柏叶回应道:“我认为要在咨询教育委员会的意见,并与失去孩子的家长沟通后,才能决定是否要这么做。”
“别对我们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别拿我们当乡巴佬。”有人大声叫道。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乡下人,所以你们才这样对我们?”另一个人问。
“如果我们是城里人,就不会这样了。”又一个声音响起。
大家一句接一句地质问起来:
校长,你有想过那些孩子等待救援时的心情吗?他们当时该多害怕呀——你想过这些吗?他们该有多冷啊,他们一定都哭喊着找爸爸妈妈。而那里就有一座山,山明明就在那儿!
你们在道路都被清理干净后才去学校,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到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倒下的树,松树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我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我们穿着靴子趟水,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还有淤泥灌进靴子里,你永远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感觉。那些找到了自己孩子的父母仍然返回去寻找其他孩子。你找了什么?混蛋,你在找学校的保险箱。
你还会去学校吗,校长?你还会参与搜救吗?我们可以借你一把铲子,如果你没有的话。如果你没有靴子,你想要多少双我们就给你多少。你只有漂亮的皮鞋,不是吗?
他还有漂亮的相机。
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才怀上这个孩子……我们也是,我们尝试了很久才怀上孩子,可现在他就这么走了。
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把我们的孩子还给我们。
每天晚上,我……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啊。
求求你,求求你,把他还给我。
就是说!
把孩子还给我们!
* * *
说明会一直到晚上9点后才结束。柏叶看起来精疲力竭。在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他们都对校长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觉得那些高声喊叫的人有些令人难为情。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思想斗争。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但至少他们终于听到可怜的远藤发言,了解孩子失踪时在操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刻发生的事情令人无法接受,又让人无法忘记。他的叙述表明,当时确实发布了海啸警报,老师也确实接收到了警报,并且采取了行动——即使太迟了。
与远藤一起爬上山的9岁男孩叫山田圣南,远藤为了让他不受冻,曾跟他紧紧地挤在一起取暖。男孩的妈妈也参加了情况说明会,并且上前向远藤表达谢意。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另一个妈妈也走了过去,她的儿子已经在海啸中不幸遇难。她想问问远藤是否记得任何有关她儿子的事情,与许多家长一样,她渴望知道孩子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况,哪怕只有只言片语,或是他当时是什么表情。可是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告诉她远藤“不舒服”,没有让她与远藤说话。然而,大家很快就知道,远藤那晚说的很多情况根本不是事实。但那晚过后,他就杳无音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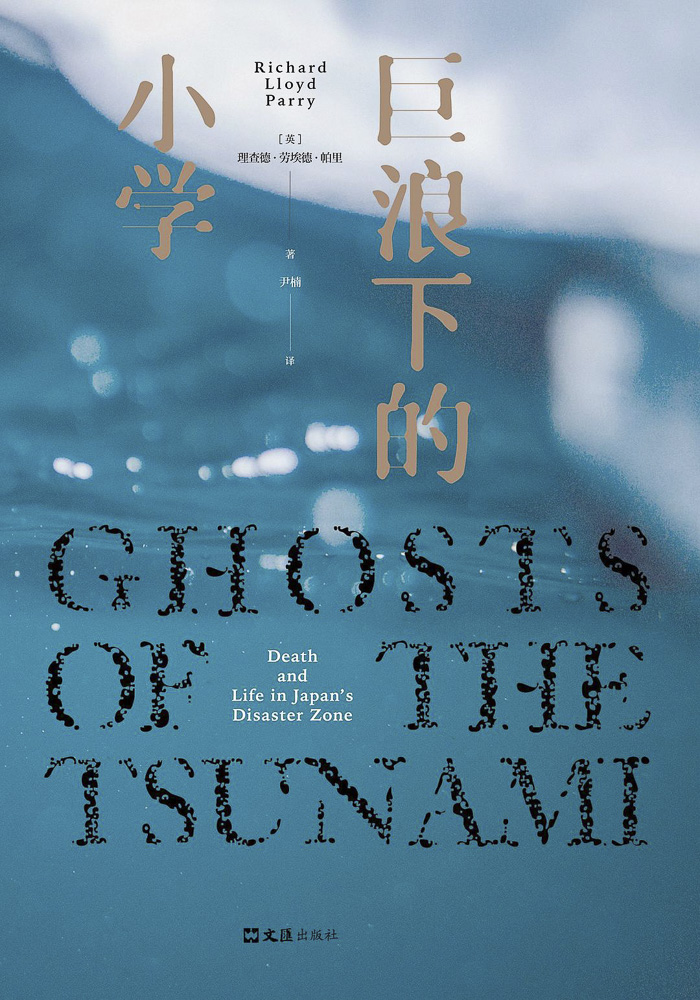
—— 完 ——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英国著名驻外记者、作家,旅居日本20余年,现任《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他长期关注日本社会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其中,《疯狂之时》(In the Time of Madness)被提名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图书奖,《吞噬黑暗的人》(People Who Eat Darkness)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长名单。《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于2018年获福里奥文学奖。
本文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